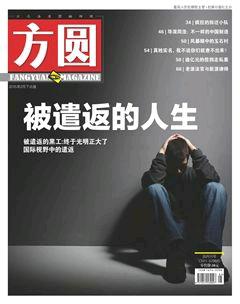北島先生到海南
那位作家每天坐在窗臺上,望著布達佩斯古老的街道,像置身于黑暗的中世紀,孤獨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他
北島比照片上更瘦些,個很高,穿灰色亞麻休閑西服,里面搭件淺草綠羊毛衫和紅色格子襯衫,厚厚的眼鏡片背后目光依然犀利,像拒絕融化的冰。這是一月的海南,離他上次來這座島,已近三十年了。他上次來是1986年,參加《收獲》雜志的一次筆會。1986,那年我剛好出生。我們這代人基本上都是讀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的詩句長大的。
下午和同事專程去了趟新華書店,買走了書店里所有的他的著作。這是一月的海南,遠離文化政治中心的海南,因為北島先生來,這個島今天似乎有了與眾不同的意義。曾經和美國垮掉派作家金斯堡等人坐在一起喝啤酒的這位詩人,今天就坐在騎樓老街某個茶館里,坐在我們身邊,分享過去二十多年來,他在歐洲、北美十余個國家的漂泊經歷。這是屬于文學的時間。
一個旅居布達佩斯的作家朋友曾告訴我他在異鄉的孤獨感受。沒有朋友,沒有鄉音,獨自一人活在缺乏經驗的世界里,周圍的一切都與你無關。你就是這個世界上多余的人。他說每天坐在窗臺上,望著布達佩斯古老的街道,像置身于黑暗的中世紀,孤獨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他。他可以盯著屋頂的鴿子一天也不說話。那段發瘋的經歷讓他內心飽受摧殘。陳染在《私生活》中曾說,“孤獨是一種能力。”“能力”用得很妥當,幸好不是“力量”。孤獨的確不能產生力量,只能消解激情和斗志。但作家最好的狀態也是孤獨賜予的。“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是給孤獨冠冕堂皇的授獎詞。真正的作家都是孤獨的,與孤獨生死相依,像張愛玲一樣悄悄死在洛杉磯的寓所。
誰也無法體嘗到北島的孤獨。20世紀80年代末,他從美國飛往西德之后,便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在不同的國度、高校漂泊。2001年,他的父親病重,得幸于楊振寧先生的幫助,他終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已經陌生的北京。這些回憶,有些已經進入了他的散文集《城門開》、《青燈》等,比起書中被刪節的回憶,我更愿意聆聽他親口訴說的“昨日重現”。“我已經找不到回家的路。”在父親的病榻前,他與父親見了此生最后一面。第二天,他再次回到那片不屬于自己的土地。
2007年,北島先生終于結束了二十余年的周游列國生涯,香港中文大學向他拋出了橄欖枝,這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在他的花甲之年終于回到了他名不副實的“家”——香港,而不是北京。他在香港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經濟方面也沒有了壓力。但常年的羈旅,給他的身體帶來了難以彌補的損害,他已經兩次中風。這位多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熱門候選人,目光依然冷峻,然而已經多了一份寬容。他和我們分享他當年創辦民間刊物《今天》的經歷,講起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幾天他們提著糨糊桶深夜往天安門、中南海、西單民主墻貼《今天》的情景,不疾不徐,不溫不火,當年的兇險,早已靜水深流,了無痕跡。這甚至讓我感覺恍如隔世,心生出不切實的真實感。這是真的嗎?北島來了!
他幾次提到我,提起我們共同相識的朋友阿乙,他還記得我前兩年發在《今天》雜志的小說。他問我,“還寫嗎?”我點了點頭。我懊悔沒敢把出版的小說送給他,書就放在我車里。我沒想到他竟然記得我的小說。在長者面前流露出的羞愧能讓我更清醒,更好地看到自己的差距。我想沒帶上那些習作也是對的。
我為現在所在的雜志自豪,北島先生將在這份雜志上發表他的作品。這是春天的海南,明天海南再無北島,但北島先生在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