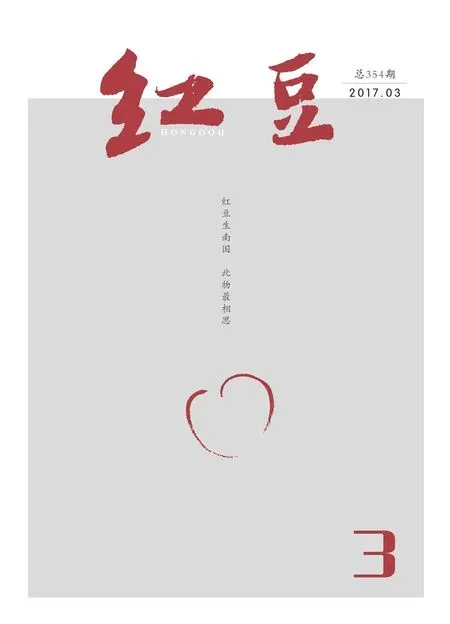女書女人
凌鷹, 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 先后在《湖南文學》《芙蓉》《作品》《山東文學》《廣西文學》等刊發表中短篇小說。在《人民文學》《散文》《中華散文》《北京文學》《四川文學》《美文》《文學界》《鴨綠江》《百花洲》《廣州文藝》《散文百家》等刊發表散文、隨筆300余篇。有散文在《散文選刊》《中華文學選刊》《青年文摘》等選刊選載,并有散文被選入《1996-2004散文精選集》《2006散文年度選》《2010中國散文年選》《21世紀中國經典散文》等權威選本。已出版散文集《放牧流水》《巨輪的遠影》《蔚藍天空上十八朵云彩》《美麗瀟湘·山水卷》《美麗瀟湘·文物卷》。現為湖南永州市作協副主席、《永州文學》雜志執行主編。
一
湛藍天空下的永明縣,一個叫上江圩的鄉村,時斷時續地傳出一種類似于鳥叫的聲音。伴隨著這種聲音,一群穿藍色印花布衣裳的農家女從她們各自的家門走了出來。她們手里或挽著一個竹籃,或提著一只木桶,結伴朝河畔走去。一路上,那種類似鳥叫的聲音就像一粒粒種子,撒在她們行走過的田野上,撒在她們洗衣的碼頭上,撒在她們打豬草的山坡上,撒在她們說悄悄話的樹底下,最終化作一種文字的生靈,留給我們去破譯。
這種文字,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女書,任何男人也無法辨認和書寫,只有極少數女性才能觸摸到它的血肉和靈魂。
二
那個叫做永明的朝代已然遠去,遠得讓我們早就無法看到它的背影,遠得讓我們再也聽不到它的一絲心跳。可是,唯有女書,卻像一種具有特殊繁殖力的水鳥,一代一代依然在上江圩一帶繁殖生長,飛翔鳴叫。
昔日的永明,已經換上了一個更秀氣水靈的名字:江永。這樣的名字,似乎與女書的音色更加吻合,似乎更適合女書的存在和生長,似乎更便于女書的飛舞和流淌。因為她們都共同擁有一種母性的陰柔之美。于是,我們幸運地知道了江永女書的最后一代傳人,知道了高銀仙、義年華、陽煥宜、何艷新這些女書的最后播種者,然后又遺憾地看著這幾個女書最后傳人一個一個永遠告別她們心愛的女書,告別這個她們終生用女書對話的世界。
三
現在的江永女書流傳于僅有兩萬人口的上江圩和銅山嶺農場及周邊的個別村落。可是早在永明時代和更早的時期,瀟浦鎮、千家峒瑤族鄉、允山鎮、黃甲嶺鄉等地也曾流傳過女書。遺憾的是,早在60年前,這些地方的女書就先后消失了,仿佛深冬的樹葉一樣,因經不起寒冷和霜雪,一片一片全部掉光了。
其實,女書最早并不叫女書。
女書是后來的學術界對這種文字符號的雅稱。在女書成為當時那一少部分女性的話語權的那個年代,女書使用者叫它們為“長腳蚊字”或“螞蟻字”。這樣的叫法,其實更形象逼真地呈現了女書的個體造型和女書在書寫中的排列組合特征。因為,它的字形總是呈長菱形,筆畫纖細勻稱有如蚊子或螞蟻腳爪,但又剛勁有力,帶點甲骨文的筆意。這種僅在永明上江圩鎮及其近郊一帶婦女之間傳承使用的表音音節文字,只有400多個字符。其傳承方式都是老傳少、母傳女或親朋相教,代代傳襲, 而且,都是用當地土語發音讀唱的。這樣的鳥叫聲,往往讓那里的男人們停下手中的農活,發呆傻笑而又不知其云。
女書在標記語言的方法上也異常奇特,可以同音借代,用僅有的400多個字符就能寫出千余字的七字韻文來,好像那些字符就是一棵棵莊稼嫩芽,只要種進土地里,就能長出更多的葉子。在那個年代,女書作品一般都書寫在自制的三朝書、扇面或布帕上,那些三朝書、扇面或布帕就是她們心靈的土地和田園,她們就在這塊田土上種植著各自的快樂和苦難。就這樣,由于同處于社會底層的婦女們之間共同的心理和經歷,致使女書在她們之間形成一種強大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也包括她們之間那種與舊制度抗爭的特殊文化力量。一旦她們結婚,便掌握著家庭的財權和子女的婚配權。在某種程度上,她們也算是在特殊時代用一種特殊的文字符號爭取到的特殊女權主義者。
作為那個時代少部分女性的話語空間的女書,就是她們的日月星辰,就是她們的春華秋實。她們經常會在歌堂用女書的發音進行對歌,用女書相互書信往來,用女書記載宗教祭祀活動,用女書結拜姊妹進行日常對話,用女書傾訴各自的心事,用女書記錄各自一生的人生苦樂與悲歡離合。當生命的燈火即將熄滅,就將一生書寫的所有女書或銷毀或帶入墳墓。我們之所以很少見到女書傳人們遺留下來的完整的女書,與她們這種人死書銷的習俗有最直接的關系。
女書還有一個神奇之處,那就是它的書寫工具。現在的女書已經被很多書家當作一種特殊的書法。可是,我至今還沒看到任何一個寫女書的書家會像我們古代的女書婦女那樣,隨意取一根木棍或者竹子,將其削尖當筆使用,也沒見過哪個當代書家從燒柴的鍋底去刮鍋灰加水泡制做墨。而古代的女書前輩們對女書的書寫卻是那么簡陋,隨手找根木棍或竹子,削尖就是筆。隨手從柴灶下刮些鍋灰,蘸水后就是墨,隨手找一張毛邊紙、棉紙或其他的什么紙,鋪開就可書寫。
我這么說,并不是說現在的一些書家用現代舒適美觀的毛筆和宣紙書寫女書就不是女書,我只是覺得,女書的本質已然離我們遠去,今天的書家們所寫的女書,只是對女書的一種緬懷和挽留,這讓我非常感動也非常欣慰。
四
由于女書沒有古代文物為證,且未載于史志,于是,女書到底有多古老,就成了一個謎。
有一種觀點說,女書是古越人文字,很可能是與甲骨文使用區有聯系的另一種文字,因為它有自己的結構體系。而另一種觀點卻認為,女書比甲骨文早,是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女人自己創造出來的自源文字。因為原始社會是母系社會,是人類最早的女權時代,必然會產生女人自己的文字。對這個觀點的認同者也認為,女書的基本字符來源于古夷文,造字方法也基本與古夷文相同,語言上的一些基本詞匯與古夷語,也就是彝語基本相近。從這個角度來考證,女書遠遠早于殷商時期的甲骨文。還有人說,因為南楚自古是百越、南蠻雜居之地,他們被歸入朝廷以后,由于無法忍受殘酷的統治和剝削,歷代都有一些勇士組織起義反抗暴政。為便于起義軍書信往來,又不能讓朝廷知曉,便利用方言土語,將常用漢字加以變形改造,作為他們內部傳遞軍情的特殊符號。這個觀點無疑想告訴我們,女書是漢字的變體變形,或者說,漢字是女書的源頭。也有人認為,女書是清乾隆五年湘南起義失敗后,朝廷明令禁止使用的流傳于寶慶府的“捏造篆字”,由于寶慶瑤遷徙來到了江永,就把那種他們使用過的禁用文字帶了過來。更有人認為,女書借用的漢字是今漢字而非古漢字。女書是當地一個擅長唱歌與女紅并有許多結拜姊妹的女人在遭遇過一次人生的重大災難后創造的。持這個觀點的學者,是源于我們現在看到的女書與女紅圖案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還有女書的產生與當地結拜姊妹的習俗那種不解之緣。
研究女書的學者們所有的觀點,似乎都有道理,但似乎又都沒有找到更確切的證據。這就讓女書變成了蒼天云霞,真實而又縹緲,我們只能看到她妖嬈婉約的面容,卻看不到她行走的路徑。
五
有一部小說叫《雪花秘扇》曾經在文學界鬧得沸沸揚揚。后來,這部小說被改編成同名電影,也在影視圈火過一小陣子。小說和電影中,把女書同伴塑造成女同性戀者,委實是對女書文化歷史莫大的誤讀!
女書姐妹之間的“老同”,在有關女書歷史的記載中確有其事,但在湘南永州,“老同”的含義與《雪花秘扇》中的指向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其本意是指會使用女書的女性之間結拜的一種姐妹關系,一種用女書相互傳遞感情、交流思想、互訴內心苦樂的姐妹情誼。在那個女性沒有社會話語權的時代,她們只能借助這種唯有她們擁有的文字符號相互取暖,相互寄托內心的情思,相互交流各自的隱私。這種苦澀而又純真的情感,正是女書文化內涵的核心和底蘊,可居然被一些并不真正了解女書的人簡單圖解成一種膚淺的情感游戲,這是對女書文化的莫大玷污。
從遺留下來的女書中獲悉,懂女書的女性都喜歡三五個或者更多地結拜成姐妹,但一般都是七個女性相互結拜。一旦準備結拜的姊妹,事先都要寫一份結交書給對方,或者寫給年齡最大的那個姐姐。結拜成姊妹關系后,她們之間便頻繁往來,并常用女書寫信,互通信息,交流各自的生活狀況,訴說各自的內心憂愁。到了女伴的生日或者一些節日,也會寫信前去祝壽賀節。
結拜姐妹中的女子結婚后的第三天為“三朝”。這時候,新娘的每位女友都要寫一本“三朝書”交給她,這就是女書習俗中的“賀三朝”。三朝書內芯一般為十八頁,封面為家織棉布粘糊做成,回形式線裝,上繡圖案。三朝書只寫前三頁,后面的空頁用來夾存刺繡用的針、線、蠶絲片、花樣圖案等物。
女書姐妹之間都有一本歌本。女書歌本多為七字韻文,也有少數五字或三字韻文。歌本里所寫的有童謠、趣事歌、訴苦歌、勸解歌、哭嫁歌、祝壽賀節歌等。這些歌有世代相傳下來的,有同伴創作的,也有自己原創的。那時候,不管是婚嫁坐歌堂,正月十五、二月初一及四月初八的“斗牛”,陰歷五月中、下旬的“吹涼”,七月初七的乞巧節或者廟會等節氣節日,女書姐妹們都會各自用歌本里的歌在那種時刻盡情吟唱。那時候的她們,每個人都成了一只畫眉鳥。
除了書信、歌謠,女書還是她們記錄社會與歷史大小事件的文化檔案。在搜集到的女書遺留物中,有記述太平天國起義部隊過永明的《長毛過永明》,有記敘抗日時期日本飛機轟炸江永和當時政府抽兵情況的《中日戰爭紀實歌》,有記述解放后的反霸斗爭、土地改革、成立互助組以及后來成立人民公社的《解放歌》。當然,也有記述男女愛情婚姻的《白水玉蓮歌》這類既溫情又酸澀故事的。
說女書是當時懂得女書的女人們的人生檔案,一點也不為過。在女書之鄉,一些一生坎坷悲苦的婦女,到年老時都會寫一篇女書傳記,這似乎已成為她們約定俗成的一種生命秩序。在傳記中,她們會詳細記敘自己所經歷的歡喜憂愁,然后在一些婦女活動或結拜姐妹的交往中,或自己或與女友一起盡情唱誦,讓心里的冤屈苦悶悲情化作那些文字與話語的晚風,在生命的蒼茫暮色中隨風而散。
我們今天研究考證女書,一個最大的遺憾就是遺留下來的女書作品實在太少了,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據考證,江永縣城郊的允山鄉的花山上有一座唐朝時期譚氏姊妹在此山坐化成仙的花山廟,每年陰歷初十到十三日,一些婦女都會帶著寫有求子、求福、求財、求平安等女書韻文的巾、紙、帕前來進香,在向花山姑婆頂禮膜拜之后,就將那些女書祭品燒掉。 正是女書女人死后將女書帶進了另一個幽冥的世界,正是這些女書祭品的灰飛煙滅,女書的歷史根源才最終成為我們望洋興嘆的文化啞謎。
一個完全被男權遮蔽的女性世界,就這樣被一少部分女性打開,然后又被這些女性關閉了。而打開這個世界的鑰匙,卻又被她們拋到了時光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