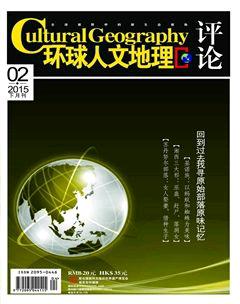仁者之情懷 詩家之史筆
王輔政
摘要:《兵車行》以史家視角入而以詩家之筆成,寄寓了仁者情懷和濟世之意,并通過“七重呼應,八轉雙合”的結構藝術以及師古而不拘泥、更重創新的藝術追求,樹立了“詩史”類詩歌創作的典范。
關鍵詞:仁者情懷;詩家史筆;七重呼應;八轉二合;即事名篇
《兵車行》自問世以來,深得世人推崇,成為各種詩輯教材的上選之備,現當代更是賞析文章如云。該詩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認為,這篇杰作至少有以下幾個看點值得我們去關注和品味:
一,史家視角,詩家之筆
杜甫的詩歌被后世稱為“詩史”,他本人也因此被譽為“詩圣”。在詩壇,這種評價是至高無上的。為什么杜詩會被視為“詩史”?關鍵還是因為杜甫的關注視角大多在家國天下、黎元百姓身上。杜甫雖然不是史家,但他卻始終關注現實、反應現實,并把他所觀察所體味到的現實生活用詩歌的方式記錄下來、展現出來。不必身臨其境,透過杜甫的詩歌就能感受到時代生活和社會變遷。正是這種史家視角,使得這首詩具備了概括性的史料價值和認識價值。這種價值主要體現在它從十二個角度廣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擴邊戰爭給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和對社會造成的巨大破壞:“點行頻”“未休關西卒”道出了兵源短缺、頻繁征兵的事實;“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則從非齡服役和長久服役兩個視角進行了揭露;“邊庭流血成海水”“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則控訴了擴邊戰爭給人民造成的生命損失;“武皇開邊意未已”則直接批判唐玄宗的窮兵黷武;“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描繪出了戰爭給農業生產造成的重大破壞和民生的凋敝;“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則反映了戰爭造成的社會分工的錯亂;“被驅不異犬與雞”控訴了官府施加給士兵的非人待遇;“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道出了民眾敢怒而不敢言的無奈;“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揭露了因戰爭強加在百姓頭上的沉重負擔;“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則以民眾重女輕男的反常心理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耶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二,仁者情懷,濟世之意
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化和影響。以民為本、仁政愛民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和基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1]“憂以天下,樂以天下”[2]則是儒家人生觀、價值觀的核心和主導;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仁者情懷,也是儒家的自覺擔當。杜甫把對國家的憂慮、對民眾的同情、對統治者的勸諭和警示盡寓詩中,這不是仁者的情懷和任者的擔當又是什么?可惜當時的唐玄宗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并沒有把這類善言綸音納入心中,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和大唐的衰敗。不過,這種醒世之言、憂戚之情、濟世之意,終究還是被后人所珍視。大清乾隆皇帝評價《兵車行》時說:“此體創自老杜,諷刺時事而托為征夫問答之詞。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小雅》遺音也。篇首寫得行色匆匆,筆勢洶涌,如風潮驟至,不可逼視。以下出點行之頻,出開邊之非,然后正說時事,末以慘語結之。詞意沉郁,音節悲壯,此天地商聲,不可強為也。”[3]能讓一代帝王發出“此天地商聲”的贊嘆,說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的警醒之語,難道不是大成其功嗎?
三,七重呼應,八轉二合
從層次上看,《兵車行》可分為三個部分:開頭至“哭聲直上干云霄”是第一部分,寫將士出征、親人送別的場面;從“道旁過者問行人”到“生男埋沒隨百草”是第二部分,從十一個角度揭露和控訴擴邊戰爭;其余為第三部分,以虛筆寫戰歿者凄慘悲涼的處境,揭示戰爭的結果和殘酷。層次十分鮮明。從結構手法上看,開頭和結尾兩部分的七重呼應尤其令人叫絕——內容上的“人”與“鬼”、“人哭”與“鬼哭”、“生離”與“死別”以及場面上的“悲愴”與“凄慘”、意境上的“塵埃”與“陰雨”、立意上的“實寫”與“虛寫”和表現手法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描寫相呼應,使這首詩如丹爐契合,嚴密精絕。中間的主體部分則如丹在爐,聚而成金。從行文線索上看,全詩的內容經歷了八次轉承——從第一部分的送別場面到“過者”發問是詩歌的第一轉;“行人但云點行頻”到控訴非齡服役、長久服役是第二轉;從非齡服役、長久服役到批評唐玄宗的窮兵黷武是第三轉;接著寫戰爭造成的經濟破壞、民生凋敝和社會分工錯亂,這是第四轉;隨后士兵傾訴非人待遇和敢怒而不敢言的憤懣則是第五轉;繼而寫官府逼租、民眾無計,進入第六轉;第七轉寫民眾反常的社會心理,揭示人民對戰爭的深惡痛絕;最后轉入對戰死者的描寫,收束全詩,這是第八轉。八個轉承,貫穿起了全部內容,使得全詩有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此外,作者又用雙重關合使全詩結構更顯完整嚴密。第一重關合是首尾呼應的關合。第二重關合是問答關合,即詩歌第二部分的“道旁過者”與士兵之間一問一答所形成的關合(除“道旁過者問行人”一句外,從“點行頻”開始到“生男埋沒隨百草”均為士兵的回答)。這首詩三個層次、七重呼應、八次轉承、二重關合的結構藝術,無一不匠心獨運,無一不令人嘆服。
四,師古不泥,創領非凡
沈德潛說此詩“設為問答,聲音節奏,純從古樂府得來”,乾隆說“此體創自老杜,諷刺時事而托為征夫問答之詞”。二人正好道出了《兵車行》師古與創新的妙諦。從內容上看,該詩與“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詩經·東山》),“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 漢樂府民歌《十五從軍征》)、“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秦始皇時民謠)等古代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精神一脈相承、神氣貫通,體現了杜甫對《詩經》和漢樂府民歌等優秀創作傳統的繼承;從藝術形式上看,雖然歌行體詩歌早已存在并長期流傳,但這首《兵車行》卻感于時事,即事名篇,不拘古制,不泥古名,體現了高度的創造精神。而這種創造精神恰恰是藝術創作和人類文明發展最珍貴的所在。
總之,《兵車行》這首寄寓了仁者情懷、以史家視角入而以詩家之筆成的藝術精品,堪稱“詩史”的典范,讓人捧讀再三而不倦。
參考文獻:
[1]《孟子·盡心上》第九章。
[2]《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四章。
[3]清·愛新覺羅·弘歷《唐宋詩醇》。轉引自徐中玉《大學語文》第32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2012年1月第四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