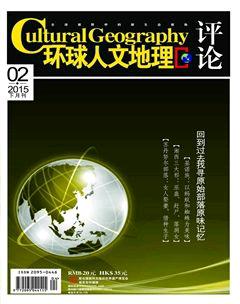龍場悟道和陽明心學的誕生
范同壽
近年來,陽明心學漸次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門選題,王陽明也成了許多地方提升自身知名度,打造特色文化的品牌。但王陽明曾經到過貴州,一直受到偏見和誤解。
一些人習慣地認為:王陽明貶謫到貴州龍場,是他人生經歷中的不幸和坎坷,如果是在水鄉澤國的故土,王陽明會更早提出他的學說,取得更大的成就。不少文章描述王陽明如何在貴州開辦學院,啟迪民智,發展文化教育,這當然是應該宣揚的。但若以“偏僻、荒縈、冷漠”的貴州因為王陽明的到來,便得到了文化,得到了榮譽,得到了許多過去沒有的東西,這就有些不大公允了。
貴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是這片沃土和它的人民滋養了王陽明,孕育了他的陰陽心學,促生了這樣一個驚世駭俗的偉大哲人和他的學術體系。沒有龍場的3年悟道,就不會有王陽明以后的積功和成就,更不會有陽明心學。
王陽明貶謫到貴州龍場以前的官職并不高,盡管他兢兢業業地恪守著一個官員的本分,卻從未受到過重用,在學術上也并無多大建樹。明代讀書人大多信奉宋明理學,青年時代的王陽明也不例外,他對朱熹等人提出的“格物窮理”的道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直到21歲,他對程顥與朱熹的哲學理論仍然十分執著,曾經面對著家里的竹子冥思苦想了七天七夜,想從當中“格”出所希望的“理”來。結果,“理”不但沒有“格”出來,人卻生了一場大病。此后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忙著參加會考。這個時期的王陽明即對程朱理學深信不疑,又一度信佛信道,實際上還沒有屬于自己的思想體系。
為了突出王陽明在貴州處境的艱苦,渲染他在逆境中的奮斗,一些人總是把明代中葉的龍場描述地非常荒涼和破敗。王陽明自己在文章中也將整個黔中的龍場形容成一處不宜人居的恐怖之地,這不僅過于夸大其辭,也與當地的實際情況不符。王陽明貶謫的龍場,即今修文縣治所在地龍岡鎮,雖然相去幾百年,氣候和地貌的變化也不至于像某些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到過修文的人都知道,位于黔中地區的龍場鎮,并不是一座山城。盡管從貴陽前往修文,需要穿越崇山峻嶺,但只要一過三足山,眼前就是一片開闊地勢。而經歷了500年滄桑的龍岡山,也不過是一個小山包。王陽明到來之前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這里便設置了龍場驛,十分繁盛。王陽明來到這里時,昔日昌盛的集市,也絕不可能皮拜倒不堪人居的程度。或許是王陽明從歌舞升平的京城,一下子來到幾千里之外的異域他鄉,覺得極不適應,或許是后人為了襯托這位哲人治學環境的艱苦,便刻意采取可夸張手法,總之,王陽明悟道的龍場,在一些人的筆下成了讓人聞之色變的窮山惡水。
王陽明在貴州的確做了不少事。他創辦龍岡書院,開課授徒,為貴州培養了眾多人才。然而貴州這片土地給予被貶謫的王陽明的回報,也同樣十分豐厚。當他初來乍到,面對陌生環境,感到無所適從的時候,得到了當地人民的熱情幫助。當他身處逆境,萬念俱灰時,是當地各族人民的樸質、善良、助人為樂的精神感動了他,讓他重新煥發出了昂揚的斗志。
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使貴州成為陽明心學的孕育地,成為陽明心學走向全國和世界的始發點,成為貴州人引以為榮的重要文化資源,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也正是貴州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才促成了陽明心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