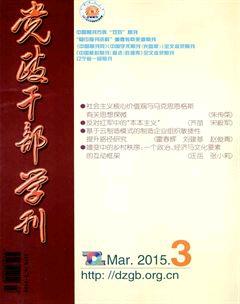洛夫的詩歌創作與現代中國新詩傳統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5)03-0072-05
[作者簡介]王志彬(1973-),男,漢族,安徽靈璧人,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批準號:09BZW065)成果之一。
從鄉愁縈懷的《魔歌》到壯闊通達的《漂木》,三十七本熠熠生輝的詩集見證了洛夫從青春到暮年的心路歷程,六十余年孜孜不懈地藝術追求譜寫了洛夫不斷超越的詩路歷程。那離散的經驗、漂泊的行程、生命的悲劇意識以及繁復的詩歌意象的經營和語言秩序的營建,形成了洛夫詩歌獨特的美學品質。洛夫旺盛的詩心,對自由精神的追求,對自我、民族和人類命運的關注,使他不斷地向漢語詩歌的藝術高峰跋涉。洛夫深受現代新詩傳統的影響,但其詩歌創作卻是在與現代新詩傳統疏離甚或是相斷裂的時空環境中進行的。他的詩歌成就“不僅在現代詩的探索方面走得最遠,而且在回歸中國傳統方面,對中國現代詩的詩學精神的探索與繼承,所取得的成績也引人注目。” [1]62洛夫的詩歌創作是當代海外華文詩歌的縮影,通過對洛夫詩歌創作與現代新詩傳統的把握,能探尋現代新詩傳統在海外的傳承、變異和發展的進程。現代詩歌近百年的發展過程,形成了自身豐富的傳統,而采用“自由體”詩歌形式和借鑒西方詩歌創作技巧無疑是現代新詩傳統較為重要的內涵。本文將從洛夫詩歌創作形式和創作技巧兩個層面,去探求洛夫對現代新詩傳統的繼承和超越。
一、洛夫的詩歌形式與現代中國新詩傳統
現代新詩是現代思想和審美意識在詩歌領域覺醒的產物,是現代詩人參照西方現代詩歌藝術,以極大的創新精神對中國舊體詩的一次變構與解放。自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白話詩八首》以來,新詩在探索、構建和創設自身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新的詩歌體式、詩學形態、詩學觀念等,而這些具有現代性質的詩歌體式、詩學形態和詩學觀念在適應時代嬗變要求,反映現代人的情感、思想和生命體驗之中,逐漸成為漢語詩歌的新傳統。而其中,分行去韻的“自由體”詩歌樣式不僅是現代新詩革新舊體詩的最顯著的外在特征,而且也是現代新詩傳統的重要內涵。洛夫青年時期就接觸到冰心、徐志摩、艾青和馮至等人的作品,這些人的詩作對洛夫日后的詩歌創作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洛夫曾說:“‘五四’以后的詩人對我產生過影響的有兩位,一位是冰心,一位是徐志摩,前者是正面的影響,后者是負面的影響。關于冰心,她對我的影響除了前面提到的那首《相思》之外,還有《寄小讀者》。……至于徐志摩,他對我產生的所謂‘負面影響’,是我把他的詩視為不可學的反面教材。我一開始學作詩便不喜歡‘新月派’的詩,那種夢幻般的浪漫抒情,那種赫糊糊的調子,很不合我的胃口,更不喜歡太講究格律,嫌它礙手礙腳。” [2]276-277在現代詩人影響下的洛夫,承繼了現代新詩詩體解放的精神,反對詩歌創作遵格律、拘音韻,他力求在“自由”的現代詩歌體式中,追尋和展示漢語詩歌的詩性之美。
洛夫在創作實踐中,把現代漢語新詩的“自由體”式進行了淋漓盡致地發揮,除創作了讓他在“‘空’境的蒼穹眺望永恒向度”(簡珍政語)的三千行長詩《漂木》外,他還創作了輕靈簡短、意蘊生動的小詩,情境相彰的圖像詩,和“帶著腳鐐跳舞”的隱題詩等不同樣式的詩歌。在《日落象山》一詩中:“好多人圍在山頂/圍觀/一顆落日正轟轟向萬丈深谷墜去/讓開,讓開/路邊的雁子大聲驚呼/話未說完/地球已沉沉地喊出一聲/痛”。在這首詩中詩人不僅分行,而且也不再遵循現代新詩一句一行的分行習慣,將“圍觀”、“讓開,讓開”和“痛”單獨成行,如此分行突出了場景、動作和感受,也讓靜默的文字產生了奇特的音效和力量。在《好怕走在他的背后當他沉默如一枚地雷》中他寫到:“當蠹魚吃光了所有的文字且繼續產卵/他開始發愣/沉思/默想他雪一般的身世,慘淡/如一張白紙/一/枚無聲的/地/雷,在最深處暗藏殺機”。在這首隱題詩中,為暗合了“他沉默如一枚地雷”,詩人將“一枚無聲的地雷”切割成四句,詩不僅未因此而顯得分散,而且詩歌的節奏、內涵和詩人的思想情感有機地結合起來。尤其是最后一句“雷,在最深處暗藏殺機”,為讀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在《午夜停電——兼懷胡適》中,他寫到:午夜停電/他突然被推進/一方格之黑漆棺柩/大地無聲而眾花紛紛凋落/世人哪/你們可以開始任意議論了/當熠熠星光/隔窗逼射而下/把他狠狠釘在/歷史的中央
在這首圖像詩中,洛夫站在歷史的高度去懷念胡適先生,無論世人如何褒貶評判,胡適在洛夫心中都猶如夜空中閃爍的星光,而原本柔和的星光在借助“隔窗逼視而下”的線性排列下,化無形為有形,化綿柔為凌厲,以顯示胡適的文化與歷史地位。洛夫對“自由體”的追求,并不必然地棄絕一切規范的體式,相反他還以現代語言佐以古典句法進行作詩。如《雨天訪友》便模擬駢文的四六句法,如:雨天過訪/什么樣的天氣/尚未敲門/什么樣的鄉愁/傘的水漬/滿街只有風雨/濺入頸項/不見一瓣杏花/沿背而下/驟聞高樓有人/……“在洛夫看來詩永遠是一種語言的破壞與重建,一種新形式的發現。因而,他對詩歌的形式有著深刻的自覺,千種文意他能設計出千般形式。洛夫所追求并不是現代詩體對舊體詩的表面“形式”上的解放——樣式上分行去韻,而是在自由的體式中,追求詩歌形式的鮮活性和豐富性,以“活”的詩歌形式去承載現代人的思想、情感和想象。
洛夫在《重整詩的形式》一文曾指出:“任何一首詩都有它本身的形式,而且不同的內容都應該有它不同的形式。傳統詩中的任何內容,都只以少數幾種固定的框框來表現,這是違反文學有機原理的,故傳統詩的格律是一種僵固的形式,不適于表現現代人較復雜的情感、思想、和經驗。今天現代詩雖然放棄了舊詩的格律,但并不表示不再需要詩的形式,否則,詩與散文何異?”所以,“詩人為了表現某一特定的內容,就必須要創造出某一特定的形式,而且這一形式是獨一無二的,別人不可能模仿的,……我認為每一個詩人都應該有一個抱負,那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去創造最佳的形式,以表現最佳的內容。” [3]185洛夫對詩歌樣式上的追求不止在于觀念上的闡發,更在于他的詩歌實踐。洛夫通過對語言的重建,以分行、轉行、標點符號的運用,以倒裝、詞語重構的方式,讓詩歌形式和主體情感有機融合,從而使詩歌產生的內在張力和戲劇性效果,讓每一首詩都有優美自足的結構形式,進而提升詩歌質量。在他的《冬天的日記》《湖南大雪》《長恨歌》《白色墓園》《石室之死亡》和《漂木》等詩作中,我們能領略他的詩歌形式之美,也能感受到他在詩歌形式探索所表現出的執著與勇氣。在《白色墓園》一詩中:白的/一排排石灰質的/白的/臉,怔怔地望著/白的/一排排石灰質的臉/白的/干干凈凈的午后……/這里有從雪中釋出的冷肅/白的/不需要鴿子作證的安祥/白的/一種非后設的親密關系/白的
詩人故意以一整排“白的”并列,形成了一種視覺上的奇特效果,詩中的意象也仿佛化作了一處充滿白色十字架和純潔靈魂的靜寂墓園。在《湖南大雪》一詩中:“雪落無聲/街衢睡了而路燈醒著/泥土睡了而樹根醒著/鳥雀睡了而翅膀醒著/寺廟睡了而鐘聲醒著/山河睡了而風景醒著/春天睡了而種籽醒著/肢體睡了而血液醒著/書籍睡了而詩句醒著/歷史睡了而時間醒著/世界睡了而你我醒著/雪落無聲”詩人以“雪落無聲”作為詩的首末兩句,中間加以十行嚴整、重復的“睡了……醒著”的構句,展示出一個雪花滑落的寒夜,無論是自然和人文,世間的一切都處于睡與醒、變與不變之間,詩人不僅讓詩的意象充滿著矛盾和張力,而且詩歌的內容和形式也產生了一種張力。一切仿佛都是應該是沉寂和有秩序的世界,卻又充滿著對峙和沸騰。在現代新詩形式發展進程中,無論是構句和分行都是一個不斷求新的過程,但標點符號卻顯然是被逐步淡化的,或者棄用或者以空白格代之。然而在洛夫詩歌中卻啟用標點符號,并賦予它們以特殊的功能,從而賦予詩歌形式以變化。在《漂木》中他寫到:“西瓜。青臉的孕婦/鳳梨。帶刺的亞熱帶風情/甘蔗。恒春的月琴/香蕉。一簍子的委屈/地瓜。靜寂中成熟的深層結構/時間。全城的鐘聲日漸老去/臺風。頑固的癬瘡/選舉。墻上沾滿了帶菌的口水……”以一個名詞或簡單的意象,中間加以句號,而后以蘊含情思的句子附后,這樣的形式能夠引發讀者的想像,增強詩歌表達效果。洛夫分析這種詩歌形式說:“上下兩句看起來互不搭調,但似乎又有某種意義上的聯系。就意象而言,猶如一幅幅繪世圖,背后的形象看似錯亂,卻又給人十分真切的感受,這是對令人驚悸的現實所做的嚴肅而含蓄的批判。” [4]254洛夫以豐富多樣的詩歌形式去提升詩歌質地,這正是洛夫對現代新詩傳統的意義——不僅讓詩歌自由地飛翔,而且還完善了“自由體”的內涵,成就了“自由體”價值。
二、洛夫的詩歌創作技巧與現代中國新詩傳統
雖然現代新詩借鑒西方詩歌藝術實現體式上現代性轉變,但現代詩人在精神情調和審美心態上難以完全承襲西方詩歌傳統,也難以完全超越中國古代詩歌傳統。因此,在漢語詩歌近百年的發展進程中,如何批判地繼承外國詩歌和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資源,進而推動現代漢語詩歌建設,一直是詩人們無法回避的問題。艾略特在《葉芝》一文中指出:“一個有能力體驗生活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階段,會發現自己身處于不同的世界;由于他用不同的眼睛去觀察,他的藝術材料就會不斷地更新,但事實上,只有很少幾個詩人才有能力適應的變嬗。” [5]169洛夫就是具備這樣能力的詩人之一,不同的生存境遇給了他不同的生命體驗。從離鄉去臺到離臺“放逐”,在行路天涯的途中,洛夫的境遇和心境在變化,洛夫的詩藝也在變化,從高調地宣揚“超現實主義”到默默地回眸古典詩歌傳統,洛夫以復雜多變的詩歌藝術表達出生命的孤絕、苦澀與凄楚,也表達出他對中西詩歌詩學精神的理解。洛夫繼承了現代詩人借鑒西方詩歌藝術傳統,積極推動島內新詩運動,并努力從西方詩歌藝術中汲取藝術精髓。但洛夫對西方詩歌藝術并非全盤接收,他認識到西方現代藝術的不足,因此他接受了西方詩歌的藝術精神,但語言表達上卻回到了中國。同現代詩人相比,洛夫對古典詩歌傳統也并非全盤否定,在拒絕古典詩歌的格律形式的同時,他接受了古典詩歌的美學精神,“以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來溝通現代”。洛夫就是融合運用中西詩歌藝術資源,自覺探索詩歌藝術,讓漢語綻放出了炫麗的詩性之光。
1949年洛夫帶著馮至、艾青的詩集離鄉去臺,故鄉已是“再也不能以仰姿泅回去了”的方向,而異鄉漂泊的行程、殘酷的戰爭和壓抑的文化政治環境,卻又讓他的內心時刻承受著孤獨、“放逐”和壓抑之苦。為紓緩內心的壓力,報復殘酷的命運,洛夫將生命的悲喜全部忠實地反映于詩歌之中。雖然去臺初期洛夫寫下了如《飲》《芒果園》《靈河》等抒情韻味十足的詩歌,但在《投影》《我的獸》以后,他便跋涉于西方詩歌是藝術領域中,開始“超現實主義”詩歌藝術的實驗與探索。洛夫之所以執著于“超現實主義”詩歌藝術,其中既有對官方戰斗文藝話語的自覺抵制,也有對其時西方現代主義主潮的響應,盡管洛夫等《創世紀》的詩人們反對現代派的“橫的移植,但“處于藝術貧血和渴求新的表現手法”的他們,還是“不自覺的乞靈于西方的繆斯”。當然,更重要的還是洛夫在接觸約翰·丹恩、葉慈、里爾克、藍波、尼采、沙特、貝克特等人的作品之后,發現西方詩歌藝術中意象、象征、隱喻、潛意識等藝術手法利于生命個體經驗的表達,洛夫說“一開始接觸西洋文學時,我即對浪漫主義作品產生抗拒,當時令我著迷的反而是那些風格近乎晦澀,讀來似懂非懂,卻又驚喜于那種奇特的表現方式的現代詩。” [6]54洛夫努力在西方詩歌藝術和現代漢語詩歌間尋求連接點,其里程碑式的《石室之死亡》便是這種結合的呈現,“只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瞼后面轉動/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詩人以苦澀而沉重的語言,用密集的意象去表現面對死亡、命運無從把握的那種彷徨、苦悶和恐懼的心理。在表達對親人的情與念時,洛夫寫道“而媽媽那幀含淚的照片/擰了三十多年/仍是濕的”(《家書》“母親/我真的不曾哭泣/只癡癡地望著鏡子/望著鏡面上懸著的/一滴淚/三十年后才流到唇邊”(《悼亡母》)。三十年未擰干的淚、三十年才流到唇邊的淚,是那樣“無理”而卻又那樣的真實。直至《魔歌》以前,洛夫都一直致力于超現實主義詩藝探索。那隱晦的語言和復雜的意象,不僅有效地傳達了詩人生命的感悟和形而上的思考,也為中國漢語現代詩開辟了新的領域。
超現實主義借助想象、夢幻、潛意識等內在精神活動作用,使詩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理性和意識的控制。然而詩歌的語言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完全擺脫理性控制,詩人的想象之翅是無法回到語言的“秩序”之內的,詩也就不能很好地傳達詩人意圖,也就更不能提升詩歌應有的品質。隨著生命智慧和詩歌創作的累積,洛夫逐漸認識到超現實主義技巧的缺陷與不足,他在《超現實主義與中國現代詩》一文中指出:“對以語言為唯一表現媒介的詩而言,如采用‘自動語言’而使語意完全不能傳達,甚至無法感悟,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我不認為詩人純然是一個夢吃者,詩人在創作時可能具有做夢的心理狀態,但杰出的詩最終仍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完成的。” [2]278因為“詩畢竟是一種靈智的活動,超現實主義者所標榜的非理性的自動語言,對于一首詩的完成是不可能的。詩可以‘無理’,只是必須產生‘妙’的藝術效果,這種效果大都體現在語言的趣味上,而完全不受理性控制的語言是無法產生這種趣味的。” [2]272因而《魔歌》之后,洛夫不斷修正詩藝,開始有所批評、有所選擇地運用超現實主義,探索將西方詩歌的創作藝術和中國古典詩歌美學結合起來。洛夫在《月光房子》詩集自序中說:“我確曾一度傾心于唐詩的氣象與妙悟,尤其在我實驗超現實主義表現手法時,經常因某些意象與句構暗合前賢而欣喜不已。我讀唐詩愈勤,所得愈多;我從杜甫和李商隱筆下學到如何經營意象,從李白筆下學到如何處理戲劇結構,從王維與孟浩然筆下學到如何通過自然表現禪趣,從賈島與崔灝筆下學到如何掌握生動的敘事手法。” [7]在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閱讀和詩美的認識中,洛夫不僅發現西方現代主義的某些觀點、表現技巧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有意想不到的回聲,而且他還“驚奇地發現,古典詩中那種幽玄而精致的意象語言,那種超越時空的深遠意境,遠非西洋詩可比。除了探尋到唐詩中那種比超現實主義更為周延的‘無理而妙’的表現手法之外,我更從蘇東坡那里找到了一把開啟詩歌秘宮的鑰匙。他主張‘反常合道’的詩觀,正與我的修正超現實主義吻合。” [2]286從標舉超現實的大旗到追求“無理而妙”、“反常合道”,洛夫逐步打通現代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的隔膜,探索出將西方超現實技巧和東方妙悟之境融合統一的詩歌藝術。在其詩作《金龍禪寺》中,就鮮明體現出他的這種詩藝追求。“晚鐘/是游客下山的小路/羊齒植物/沿著白色的石階/一路嚼了下去/如果此處降雪/而只見/一只驚起的灰蟬/把山中的燈火/一盞盞地/點燃”晚鐘何以成為小徑?羊吃植物何以咀嚼?灰蟬何以點燃燈火?這些看似“無理”語言結構和意象組合,卻又構成了廣闊、深邃、奇妙的意境。
“五四”以后,從早期的象征派到上世紀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群再到上世紀40年代的九葉派,現代詩人對借鑒西方詩歌藝術表現出強烈的傾向,并以之去改造中國舊體詩歌,建設漢語新詩。現代詩人融合西方現代主義觀念、藝術和風格的詩歌創作,對現代詩壇造成了影響,也推進了漢語新詩的現代化進程。洛夫在去臺之前就接觸詩人馮至的作品,多年后他認為自己與馮至在詩藝看法上是同源相通的。洛夫對里爾克的推崇,對超現實主義詩歌藝術的自覺追求,馮至是有引介之功的,我們認為也正是經由馮至,洛夫承繼了現代新詩詩藝的創新精神。但洛夫對西方現代詩歌藝術的態度和指向性是不同于現代詩人的,洛夫曾說:“我是最現代的,但也是最中國的。當年我向西方取經跋涉異域,那是一種偶然,而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來,承襲先賢們的文化遺產,以謀求更優質的創新,這是一種必然。” [8]24洛夫對詩歌藝術探索的最終歸宿是以現代詩歌藝術的眼光去觀照中國古代詩歌傳統,以西方詩歌藝術和中國古典詩歌美學的融合,去實現中西詩歌以及傳統與現代詩歌間的對話,推動漢語新詩建設。詩歌是語言的藝術,任何詩藝都是成就詩歌意義之美的手段,最終都要通過語言來表現的,洛夫對西方詩歌藝術的借鑒以及對古典詩歌傳統的回歸,其指向在于變革現代新詩粗糙的語言,在建設現代美學規范下的語言的基礎上,繼承和豐富漢語詩歌的本質。從“橫的移植”到“縱繼承”,洛夫的詩藝路程正如他回顧《創世紀》發展歷程時所言,“《創世紀》五十年來跋涉過西方現代主義的高原,繼而撥開傳統的迷霧,重見古典的光輝,并試著以象征、意象和超現實諸多手法來表現中國古典詩歌中那種獨特美學,經過多年的實驗,我們最終創設了一個詩歌的新紀元——中國現代詩。這不僅是《創世紀》在多元而開放的宏觀視野中確立了一個現代漢語詩歌的大傳統,而且也是整個臺灣現代詩運動中一項毋庸置疑的傲世的業績。” [9]84對詩歌藝術的探索與追求,并在多元而開放的宏觀中確立了一個現代漢語詩歌的大傳統,這也正是洛夫詩歌藝術對現代新詩傳統的超越之所在。
三、洛夫對現代中國新詩傳統的繼承與超越的當代啟示
傳統是面向未來的活力范疇,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地創新。文學的薪火之所以能傳承不息,不在于守成和復古,而在于超越與創新。縱觀現代詩歌作品所呈現的現代中國新詩發展史,不難看出那其實也是西方詩歌傳統和古代文學傳統的對抗與對話的復雜過程。傳統是發展的,是不能重回的,洛夫說他“向古典詩借火不過是一種迂回側進的策略,向傳統回眸,也只是在追求中國詩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權宜而已。” [2]280因而,我們認為,洛夫無論詩歌形式的創新,還是詩歌藝術的探索實驗;無論是標舉超現實主義,抑或回眸古代傳統,其終極目的不是在推動西方詩歌傳統本土化和古代詩歌現代化的轉型,而是在為現代漢語詩歌尋求更適合的表現方式和角度,實現漢語詩歌的藝術升華,是在豐富現代新詩傳統的內涵。洛夫對現代新詩傳統繼承與超越啟示著我們:繼承和發揚傳統并不是簡單地接受,而是要以創新的姿態去超越和發展傳統,進而去建設真正的中國現代新詩。
自1949年以后,現代新詩拓展為當代大陸詩歌和海外華文詩歌兩大流脈,兩脈雖同根同源,但卻呈現出不同的生命形態。這是現代新詩傳統在不同文化政治和社會環境中傳承、變異的結果,也體現了當代漢語詩歌的復雜性、多樣性的一面。當代大陸詩歌在五六十年代經受政治話語沖擊,而后又受到了歐風美雨的洗禮,新時期以“朦朧詩”發端,“新現實主義”、“整體主義”、“非非主義”、“新古典主義”等詩歌流派不斷推陳出新,從狂熱地借鑒地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思想與藝術到“文化尋根”,當代詩人們在迎接和反叛西方詩歌藝術中,進一步革新了詩學觀念和詩歌技巧,實現了詩歌藝術的創新,詩歌語言也顯現出空前的活力與韌度。但,我們同時也看到也有不少詩人對西方詩歌藝術和古典詩歌傳統存在誤解和誤用的現象,比如在詩歌創作中過度強化個體的心靈體驗,打亂古典詩歌傳統中的意象體系,消解古典意境美,缺乏對語言的錘煉等等問題。沈奇在《重涉:典律的生成》一文中指出:“當代新詩的混亂,不僅因為缺乏必要的形式標準,更因為失去了語言的典律。格律淡出后,隨即是韻律的放逐,抒情淡出后,隨即是意象的放逐,散文化的負面尚未及清理,鋪天蓋地的敘事又主導了新的潮流,口語化剛化出一點鮮活爽利的氣息,又被一大堆口沫的傾瀉所淹沒。” [10]1一些詩歌的表面化創新,可能是出于對時尚的追風,但最終偏離和傷害了詩歌的本質。而這樣的問題在海外華文詩歌創作中也同樣存在。現代新詩在追求現代化進程中形成了自身豐厚的傳統,它和中國古代詩歌傳統以及西方詩歌傳統一起,共同成為當代詩歌創作最寶貴的藝術資源,當代詩人應該利用好、經營好這些寶貴的藝術資源。那么,當代詩人如何利用好、經營好這些寶貴的藝術資源,從而去進行漢語詩歌創作呢?洛夫說:“當代中國詩人必須站在縱的(傳統)和橫的(世界)座標點上,去感受,去體驗,去思考近百年來中國人泅過血淚的時空,在歷史中承受無窮盡的捶擊與磨難所激發的悲劇精神,以及由悲劇精神所衍生的批判精神,并進而去探索整個人類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意義,然后通過現代美學規范下的語言形式,以展現個人風格和地方風格的特殊性,突現大中華文化心理結構下的民族性,和以人道主義為依歸的世界性。” [11]102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匯的今天,洛夫的創新精神,洛夫對新詩傳統的態度,對建設漢語詩歌的責任,都為當下詩歌創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當代詩人不僅要審慎地從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現代詩歌傳統和西方詩歌傳統汲取創新因素,而且要真正地去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漢語現代詩。這樣,才能保持詩人的尊嚴,保證漢語詩歌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