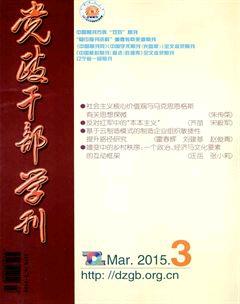近代沈陽詩壇創作特色論略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5)03-0077-04
[作者簡介]趙旭(1975-),男,遼寧沈陽人,博士,沈陽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遼沈地域文學研究。
劉磊(1979-),女,遼寧大連人,博士,遼寧大學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本文系遼寧省社科聯2015年度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立項課題(2015lslktziwx-26),2013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L13BZW008),遼寧省高等學校優秀人才支持計劃資助項目(WJQ2014053)。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此后,清帝國逐漸陷入內憂外患的處境,遼沈政局也隨之受到了沖擊,作為陪都的沈陽更是首當其沖。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近代沈陽的詩壇,也表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本文試對此加以探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沈陽本土文人的詩作
被譽為“遼東三才子” [1]4604之一的劉春烺(1850-1905),字東閣,又字冬葛,號丹崖,奉天府承德縣新民廳人。光緒八年(1882)中舉。《北鎮縣志》小傳中說他“讀書獨觀大義,覃心于經世之學,凡輿地、兵事、農田、水利,以迄器藝之微,無不精究其蘊” [2]。曾由左寶貴推薦,治理新民柳河水患,“獨任其事,堤堰至今尚完固” [2]。可見,劉春烺是一個重視實學的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他主講萃升書院,并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任盛京省學堂的總教習,為沈陽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其詩作多是即景抒情,感物言志之作。如《重九日沈陽城樓》,以“搔首不可問,重陽始何年。登城望東北,漠漠山川連”起句,登高遠眺,見遠天寒鴉,煙靄孤塔,愴然之感頓生。“世界萬封蟻,強者為鳥鳶。蠢靈同吾族,欲拯愁無緣。又無羨門術,白日飛金仙。仰天百感集,落木正蒼然。” [3]列強環伺,時局堪憂;欲濟蒼生,又無處著力,感時傷志之意充溢其間。
《聽角行》則是一首更為直接的紀實之作:
沈陽城頭角嗚嗚,老鴉飛上城頭呼。大街小兒拍手笑,兒勿上城官人驅。
官人猙獰面貌粗,長鞭打人壯且都。問其姓名姓則無,但道將府兵與夫。
春風二月草木蘇,鳴角朝夕摧封租。老農封租已向畢,鋃鐺枷鎖尤盈途。
身有百口辯不得,誰歟夢見流民圖。圖亦不得見,罪亦不得除。
孤兒寡妻走邊隅,路逢猛吏神仙如。錦衣大馬出民廬,歡歸酒肆聽笙竽。 [3]
晚清吏治廢弛,官府橫征暴斂,屢增賦稅;官兵亦為虎作倀,兇殘粗暴。這首詩所述就是詩人在沈陽街頭親眼目睹之景象,“老農封租已向畢,鋃鐺枷鎖尤盈途”,陪都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而朝廷大員們“錦衣大馬出民廬,歡歸酒肆聽笙竽”的生活,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令人氣憤填膺。
繆潤紱是與“遼東三才子”同時的沈陽本土詩人。繆潤紱(1851-1939),字麟甫,號東霖,別署吟溪釣叟、釣寒漁人、太素生、含光堂主人等,漢軍正白旗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繆潤紱出身于書香門第,其曾祖父繆公恩是沈陽著名文士,其祖父繆圖箕、父親繆景文及其叔輩繆景其也是有文才的人。繆潤紱年輕時就表現出極高的才華,與韓小窗等人共同創建了著名的“薈蘭詩社”,并與韓小窗和喜曉峰并稱為“沈陽三才子”。《沈陽百詠》是其代表作。刊行于光緒四年,民國十一年(1922)又經作者加以修訂出版,詩作和按語都做了一定的修改。從內容上看,《沈陽百詠》“摭拾舊聞,涉筆拈毫。竊以生居豐鎬之鄉,忝附緣飾沅湘之例,隨時湊集,爰成百章” [4]自序1,采用七言四句的竹枝詞形式來記錄沈陽的民俗風物,共計100首,“是一部有關沈城掌故、風俗、起居、飲食、服務、婚喪、信仰等方方面面內容的詩集” [5]368。其中對當時的武備問題也有所涉及,如光緒本第二十首:
識字仍須學挽弓,教場昨夜換春風。諸童嬉戲將軍怒,都在彎弧一笑中。 [4]40
這首詩通過形象的對比,在表面的嬉鬧中,蘊含著對旗人武備松弛的感傷,很有些“含淚的微笑”之味道。
張之漢(1866-1931)也是一位愛國的本土詩人。字仙舫,署遼海老漁,宣統元年(1909)優貢。歷任自治局顧問、諮議局議員、官銀號總辦、實業廳廳長等職,卒于東三省鹽運使任上。《奉天通志》中載有張之漢為王永江《鐵龕詩草》所作序文。序中寫到他和王永江深夜對酌,“酒酣耳熱,縱談時局”,王永江“憤然碎杯起,目光電閃,吐氣如長虹”;而兩卷《鐵龕詩草》,亦“大都感時憤世,托物見志之作”。 [6]張、王二人為至交好友,性情文章庶幾近之。甲午戰爭時,金州廳南關嶺塾師閻世開不屈于日寇,慷慨殉國,王永江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張之漢,張聞聽后悲憤不已,提筆作《閻生筆歌》。其詩云: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奮椎難擊博浪沙,抗節直比胡天雪。非椎非節三寸毫,竟憑兔穎探虎穴。千軍直掃風雨驚,披肝瀝血凝成鐵。飲刃寧惜將軍頭,振筆直代常山舌。頭可斷,舌可抉,刃可蹈,筆可折,凜凜生氣終不滅,吁嗟閻生古義烈!閻生著籍遼海東,系心家國身蒿蓬。……九連城頭將星落,頹軍斷后誰盤矟?東南銅柱沉江濤,太阿倒柄憑人操。十萬橫磨豈不利,一割無用同鉛刀。胡為乎!刀圍大帳筍鋒密,挺然獨立閻生筆! [7]
這首詩慷慨悲憤,感人至深。其后流傳極廣,令閻世開的悲壯事跡廣為人知,極大地鼓舞了國人的愛國熱忱。張之漢此詩,為飄搖動蕩的晚清沈陽詩壇留下了一個挺立不屈的身影。
二、外來游歷、求學、客居者的詩作
有清一代,沈陽作為“陪都”重鎮,成為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隨著近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到沈陽游歷、客居、求學者也多了起來。
魏燮均生于嘉慶十六年(1812),“卒年尚未考證清楚,當在1890年左右” [8]。初名昌泰,字子亨,號芷亭。因慕鄭板橋之為人,遂更名燮均,字伯柔,又字公隱,別號鐵民,又自號九梅居士,著有《九梅村詩集》。《奉天通志》小傳中說他“工書法,善古文詩詞,負笈遠游,多覽名山大川。” [1]4602魏燮均大半生漂泊,風塵困頓,和社會底層較為接近,其詩歌中經常能看到當時社會民生的真實情狀。如《李小南明經遷居小河堰》詩后小注中說“小南本鄉居,因盜賊警遷居省城” [9]781,可見清末盜匪之患,已成常見景象。他在《沈陽客館夜坐感懷》一詩中寫道:“天街無月明,漏下禁宵行。人語遠過巷,鐘聲高出城。歲寒猶在客,世亂每談兵。自顧頭垂白,愁吟對短檠。” [9]445次句有小注“時城中戒嚴,禁止夜行”。魏燮均生年至少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戰火尚未涉及東北內陸地區,但連年的兵亂,以及吏治廢弛,盜賊蜂起的內政,已經令詩人感到了亂局將至的風雨飄搖。以此為題材的作品蒼涼沉郁,頗有杜甫“詩史”的味道。
客居沈陽的詩人,以劉文麟最為著名。劉文麟(1815-1867),字仁甫,號仙樵、衍陽山人。他是近代極有影響的詩人。《清史稿·劉文麟傳》稱他“論詩以婉至為宗,語必有寄托,英光偉氣,一發之于詩。論者謂足繼遼東三老。” [10]清嘉慶二十年(1815),劉文麟出生在遼陽東沙滸屯。9歲便能作詩。11歲隨父親入川。遼東文化和巴蜀文化共同濡養了這位少年才俊。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劉文麟進京應進士正科考試,中進士,授官廣東任知縣。歷史給了年輕的詩人一個表現的機會。劉文麟親歷了禁煙運動和鴉片戰爭,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冬之際,根據所見所聞所感寫成八首七律組詩,題為《感事·辛丑八首》。他稱得上是“近代史上第一位親歷并參與鴉片戰爭,及時以詩歌反映這場戰爭,真實記錄下這場戰爭實況的詩人。” [5]342
咸豐六年(1856),劉文麟受王曉坪之邀主講沈陽萃升書院,至同治元年(1862),執教近六年。在沈陽期間,劉文麟悉心講授儒家經典,熱心教授學子,同時,自己也堅持寫作詩歌。經劉文麟教導的學子中,有不少人成為了名士,如《清史稿》所載:“其門人王乃新,字雪樵,承德人。亦能詩,有《雪樵詩賸》。” [10]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河。身在陪都的沈陽,正主講于萃升書院的劉文麟當然會受到觸動,難以抑制心中的憤懣,寫下《感成》三首。“漏卮枉用民膏塞”以“漏卮”來形容當時的國勢,很有形象性。而一個“枉”字表達了內心對當權者無能的極大痛恨。在抨擊當權者無能的同時,又冷靜地想到“全局終思國手收”,熱情呼喚救國人才的出現,這也為其在萃升書院的教學增加了動力。而對咸豐帝的出逃,也予以了痛斥:“海氛急掃孤衷切,天步足回萬頸延。圣祖神宗疆域在,是誰陳策議東遷。” [11]表面上是批判慫恿東遷的臣子,實際上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
此外,與劉春烺并稱“遼東三才子”榮文達和房毓琛也時常經過沈陽。榮文達有《沈垣旅寓養病》詩二首,其一云:
洋笳洋鼓沸城陰,郭笛溪碪寂不音。病客聽雞憎夜永,衰翁如鶴警秋侵。
乾坤懷古悠悠淚,歐亞傷時耿耿心。聞說翠華西返蹕,荒原風露可勝禁。 [1]5036
以“洋笳洋鼓”喻指虎視眈眈的列國諸強,寂寥無聲的“郭笛溪碪”則好比日暮斜陽的清帝國。當時榮文達正在病中,但直至深夜還憂心忡忡,思慮國事,真可稱“歐亞傷時耿耿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沈陽讀書的周恩來也留下了詩作。1910年春天,他隨伯父周貽庚來到沈陽,就讀于奉天省官立東關模范兩等小學校,度過了三年讀書生活。就是在這里,他提出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言。1911年暑期,他和同班好友何天章與何履禎去位于沈陽沙河一帶的魏家樓子度假,這里曾是日俄戰爭的戰場,日本在此建塔,俄國則在此建碑。在何履禎家居住期間,與何履禎的祖父何殿甲寫詩應和,為沈陽文壇留下了重要的一筆。何殿甲是村中的私塾先生,經常和周恩來談起日俄戰爭,并帶他去附近的戰場遺跡察看。年僅十三歲的周恩來通過實地考察,并親耳聽到鄉鄰談到日俄軍隊在此犯下的罪行,極其悲憤,同時也認識到政府無能必然會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對自己,對青年的責任也有了思考。這充分體現在他的《村望》一詩中。當時,在煙龍山,面對戰場遺跡,何殿甲老人含淚吟誦杜甫的《春望》,周恩來心有所感,依原韻改寫《村望》一詩:
國破山河在,村殘草木深。感時勿落淚,誓叫寇驚心!
烽火連歲月,捷書抵萬金。白頭休志短,患除賀更新。 [12]
此詩一反杜甫原作的深沉痛楚,詩中表達了激蕩的少年豪情。面對眼前殘破的戰場遺跡,想到國家的衰弱,少年周恩來不是沉溺于悲憤,而是想到要不受欺凌,必須要自強,“誓叫寇驚心”,改變頹勢,去取得勝利,“捷書”報喜。尾聯更是對未來充滿信心,即使是白發者亦有作為,國家除患興盛日,就是青春再來時,當為新的時代繼續做出貢獻。這不僅是對杜甫詩歌的升華,而且也是對何殿甲老人乃至自己的激勵。表現出少年周恩來寬廣的胸懷和不凡的見識。對此,何殿甲老人深受感動,在《登東山歌》中寫道:“登彼龍山兮山巔,望彼河水兮潺潺。憶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戰兮心酸。”“吾已生于斯兮長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煙。今我老兮有何志愿,圖自強兮在爾少年。” [13]一老一小因國勢所激而產生的詩歌交流,成為了沈陽詩壇的一段佳話。
三、《盛京時報》的詩歌主張與傾向
《盛京時報》是近代沈陽的主流媒體,由日本人中島真雄創辦于沈陽大東門里,1906年10月18日(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出刊第一號,1944年9 月14日曾改名為《康德新聞》,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停刊,歷時近40年。“據中島真雄自述,《盛京時報》這個報名,‘是襲用俄國占領奉天時發行的俄文《盛京報》而定的’,并請清末進士張元奇(后任奉天民政使)題寫報名。” [14]
從文學史角度看,主要發表在《盛京時報》“文苑”欄目中的詩歌,題材多樣,數量眾多,而且作者身份各異,既有守舊官吏,也有維新革命者;既有中國文人,也有外國作者;既有本土寫手,也有外地投稿者。其復雜的寫作狀況,構成了當時沈陽豐富的文學生態,也是當時中國詩壇上重要的一環。同時,這份由日本人創辦的報紙所刊載的詩歌又具有與當時社會時局緊密結合的特點,體現著當時社會的審美取向,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義。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發表在“選論”欄目《圣人與詩人》一文,可以視為一篇關于詩歌社會功能的論文。此文極力鼓吹詩人之力量,首先將詩人與圣人并稱,辨別其異同:
一言以蔽之曰:悲世之惡而知所以救之者,圣人也;悲世之惡而不知所以救之而唯思逃之者,詩人也。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滋,則一而已矣。
指出詩人與圣人雖然對世人的具體態度不同,但其內心的憂患則是一致的。然后進一步指出世人對詩人的不理解:“世之奉圣人如天神,其視詩人雕琢薄技而已。余乃以之與圣人并稱,誰不以為狂惑?”然后表面自己的態度:“然吾憂圣人,吾愛詩人。”作者認為,圣人和詩人的共同點在于,面對嚴酷的現實社會:
其吐辭立義,或非世俗所能知。雖取相非笑駭怪,然能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道廣大而盡精微,譽之不以為喜,毀之不以為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洋洋乎,淵淵乎。故曰圣人參天地者也,詩人邈天地者也。世俗惡足以幾之哉。……談要之,推其識,性則圣人與詩人蔑不同耳。……見世之溷惡,人之淪墮,以為非吾徒也。乃冥想無際,上薄九天下徹九淵,不知所以寄其情者,而發為怪麗之辭,如屈原之《離騷》,和謨之古詩,李白、李賀之歌行,唐德之《神曲》,米爾敦之《失樂園》,格泰之優師劇。其他不可患述,大率用意相類也。
詩人和圣人的本性是一致的,但詩人更愿意追求個性的自由和情感的解放,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作者也清醒認識到,推崇圣人之道者,卻有許多人“委曲阿世,則其志異于圣人。而所行或詹詹需需,競利持祿,立身本末,每有不強人意者”。這樣的生存狀態,“何如詩人之灑然不可羈,為高潔之至者哉”。作者不是厚此薄彼,而是針對所處時代特點,主張人們多一點詩人的精神,遠離污濁,遠離庸俗,多一些獨立精神。進而談到文學領域中更需要詩人:
吾國夙尚文學,千百年來,其能完然無愧于詩人者,何其少也。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詩人斯可矣。詩人乎,豈尋常吟弄風月鋪續景物者足以當之乎!
本文作者大聲呼喚詩人的出現,而且明確指出,真正的詩人決不是吟弄風月者,而應該是具有獨立精神者。此言擲地有聲,可以視為《盛京時報》刊發詩文的一個綱領性的文獻。可惜這篇文章并沒有對《盛京時報》所刊發的詩歌真正起到指導性作用,因為所刊發的詩歌大部分還是吟風賞景,抒發個人情緒的作品,缺少時代精神。
總的來看,近代沈陽是一座重鎮,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都在此發生。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大量本土文人包括近代的一些著名人士或來求學、或來仕宦、或來客居,與沈陽發生了密切聯系,并因為各種機緣在沈陽留下詩作,他們與沈陽本土文人共同構建了近代沈陽詩壇,為沈陽近代文學增加了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