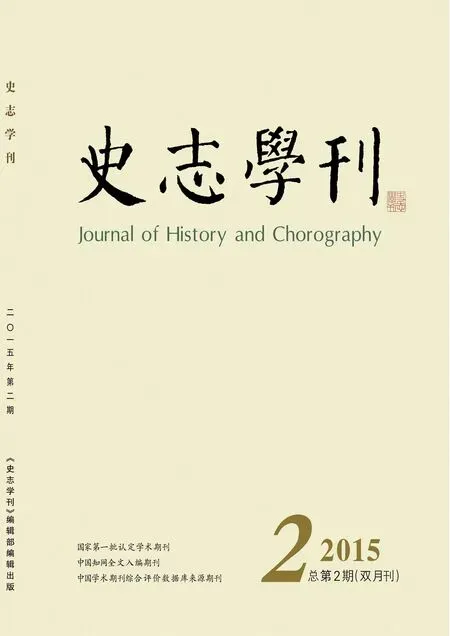金代學者的文化傳承——以李純甫為中心的考察
李美榮
(山西大同大學 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山西大同,037009)
無論研究文學史,還是儒學或者學術史,金代都是一個尷尬的時期。在中國文學史或中國儒學史種種著作中,作者往往采取便宜行事的方法,要么遼金或者遼金元合述,要么將其附于宋朝之下。雖然整體考察金代文學和學術的論著并非沒有,但是這一長期的認識和處理誤區,對我們全面探析這一時期的文化極為不利。
就發展演進來說,金代文化在初期的“借才異代”之后,經過當朝統治者的提倡和士人的努力,逐漸走向了制度化和學術化,最終得以在后期開花結果,附庸蔚為大國。金代文化尚中務實,兼收并蓄,對于三教合一、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元修三史,視金代文化程度在同是少數民族政權的遼代之上,“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1](元)脫脫.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藝傳序.中華書局,1975.,不無道理。
學術泰斗余英時在史學方法上貢獻給學界用于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大成果——“內在理路說”,對海內外的歷史研究有著巨大的影響。簡言之,就是依一時代思想學術的自身要求,追尋其內在邏輯,從而展現其變遷發展。筆者認為,一個朝代文化發展程度的高低,不僅體現在少數杰出學者的文化成就,也體現在社會文化的整體變遷,更體現在學者的文化傳承之上。文化繼承是文化創新的基礎,而文化傳承則決定著文化繼承。從這一層面上來說,考察金代學者文化傳承對于我們把握金代文化事業的影響和其文化發展的“內在理路”有著極大的裨益。
作為金代南渡之后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李純甫與趙秉文雙杰鼎立,共執金末文壇之牛耳,其縱橫捭闔,儼然一代文宗。黃宗羲撰修《宋元學案》,于金朝眾學者之中僅為李純甫一人單獨作《屏山鳴道集說略》,由是可見其地位。因此,考察李純甫的文化傳承,對從中透析有金一朝的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管中窺豹,略見一斑。
一、繼承與傳承
李純甫(1177—1223),字之純,號屏山居士,西京弘州襄陰(今山西大同)人,金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李純甫自幼好讀《左傳》,“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其“為文法莊周、列御寇、左氏、《戰國策》”,宗主黃庭堅,為人行文講究放蕩不羈,主張創新,自成一家,與趙秉文等起而反對江西派重理輕情的傾向,倡導風雅文風,“后進多宗之”[1](元)脫脫.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李純甫傳.中華書局,1975.。劉祁《歸潛志》稱“南渡后,文風一變,文多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2](金)劉祁.歸潛志(卷八).。李純甫“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楞嚴外解序.,思想上出儒入釋,主張三教合一,援儒入釋,以斷言“西方有中國書,中國無西方書”[3],提出“圣人心學,西方文教”聞名于世。元好問稱贊說“南渡以來天下稱宏杰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4](金)元好問.元好問全集(卷二十一)·雷希顏墓銘.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在考察李純甫自身的文化傳承之前,有必要先對李純甫本人所接受的文化傳承,也即他的文化繼承做一簡單分析。
自隋唐設立科舉以來,科舉便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媒介,金代亦是如此。史載“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5](元)脫脫.金史(卷五十一)·選舉志一.中華書局,1975.。本文無意考察金代科舉的社會政治效用,而強調其對文化傳承的媒介作用。科舉制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之上,鼓勵舉子讀書,分科取士,其最重要的一個社會效應就是培養人才,從傳統社會的學者大多是有功名的士人便能看出。女真一朝共開科38次[6]關于金代開科次數,學界向來意見不一,有21次、28次、41次、43次等不同的說法,見都興智先生《遼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薛瑞兆《金代科舉》一書認為有47次,而都興智先生詳細考證為36次,孫孝偉在此基礎上多考證兩處,定為38處,這里暫采用這一說法,見其《金朝科舉制度探析》,《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3月。,科舉條目除了上述幾個方面,還于“海陵天德三年,罷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后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童中選者,曰舉人”[5]。李純甫的父、祖皆中詞賦進士,他自己也于承安二年擢經義進士。李純甫由好讀《左氏春秋》,從詞賦轉為經義學,成為金末儒學的代表人物,由此可以看出金代科舉對文化傳承的功用。
以上對金代科舉的考察,我們注意到另外兩個對李純甫文化繼承起到重要作用的方面,即地域文化影響和家學影響。由大及小,先論地域文化。李純甫父、祖皆為詞賦進士,李純甫最初亦學詞賦,后才轉向經義研究,李純甫一門三代都曾研習詞賦,并非巧合,而是由金代科舉政策決定。金代科舉根據地域文化的不同實行“南北選”,南北方士人根據所習之業,分試經義和詞賦,李純甫故籍西京大同府便是試詞賦,因此才有了上面的現象。另一方面,李純甫受地域文化的影響又表現在金代西京經過遼金兩代的經營,已經成為當時北方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人才輩出,除李純甫外,還產生了邊文鼎、曹之謙、王元節等著名文學家,以及渾源劉、雷這樣的文學世家,其中雷淵、劉祁尤為突出[1]關于金代西京文化,參見馬晉宜、杜成輝《金代我國北方的文化中心西京》,《雁北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6月。陳福來《遼金西京研究》(碩士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07年5月,24-27頁。馮娟娟《金代西京文化研究》(碩士論文),渤海大學,2013年6月,26-29頁。,劉祁曾不無自豪地說道“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云中三老圖》,魏參政子平弘州順圣人,梁參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參政輝蔚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又,蘇右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順圣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李屏山,弘州人,高丞相汝礪,應州人,其余不可勝數,余在南州時,嘗與交游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東、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2](金)劉祁.歸潛志(卷十).,不得不說地域文化對于金代文化傳承有著突出的作用。
李純甫“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3](元)脫脫.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李純甫傳.中華書局,1975.,一門三代皆中進士,深厚的家學淵源可以說是極重要的,李純甫自述“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4]李純甫.重修面壁庵記;(金)劉祁.歸潛志(卷一).,家學影響可見。錢穆先生指出“‘家族’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5]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P51)。家學影響也即家族傳承,在文化史上,家族傳承始終是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方式。家族傳承和地域文化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地域文化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學術世家的形成,而學術世家的繁盛也可帶動地域文化的發展。金代有很多杰出的文學家族,這些文學家族的產生是金代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6]關于金代文學家族對金代文化發展和文化交流的影響,參見楊忠謙《科舉文化視野下金代家族與文學》,《民族文學研究》,2011年6期,及其《金代文學家族的空間流動和與文學交流》,《北方論叢》,2012年11月。關于金代文學家族的個案研究,參見杜成慧《金元時期渾源劉氏家族研究——以劉祁為中心》(博士論文),中央民族大學,2005年5月。。
在考察了李純甫身上所折射出來的金代文化繼承的幾個大的方面之后,以下簡單討論一下他的思想轉變。一般認為李純甫由詞賦、經義,經由老莊,轉向佛教。一生思想經歷了早歲信佛、青年排佛,再到中晚年信佛,最終“三教合一”的轉變,這期間,史肅、行秀和萬松對他起到重要的影響[7]東梁.李純甫的“三教合一”論.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動態.1984年3、4合刊;胡傳志.李純甫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02,(2);封樹禮.李純甫佛學思想初探.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本文不擬就此深入,只是簡單敘述,便于下文的展開。
二、方式與途徑
一個朝代文化發展的中心力量在于學者和學者構建的學術群體,學者和學術群體的一個重要社會文化功用在于,他們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收徒授學,致力文化傳承。需要注意的是,學者不但傳授共同的文化資源,更突出的在于傳授后輩自身所秉承的文化理念和認識。章學誠《文史通義》在論及“浙東學術”時,提出“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可謂的見。金代學者的文化傳承里雖不免有門戶之見,但畢竟學有所宗,不可不察。上節簡單闡述了李純甫的文化繼承,并且簡單介紹了他的思想轉變,這節便以方式和途徑來考察李純甫的文化傳承。
學校和書院在中國古代是不同的教育場所,對于二者的區分不在這里的關注范圍,暫且不論。三代以來學校是文化傳承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自唐末五代,書院興起,逐漸分擔了學校傳承文化的職能。兩漢經師傳經大多都是私人講學,恪守家法。有關李純甫和學校、書院的關系,記載不詳,這里也不在此探討,但兩者對于金代文化傳承亦有重要的作用,這里不可不提,暫表于此。至于私人講學,李純甫交游論學之中,是否有私人講學的成分,尚有待商榷和考證,須另文專述,茲不具論。就筆者愚見,現今史料中所見的李純甫的文化傳承方式約略有以下幾項:
1.提攜后進。李純甫“天資喜士,后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 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志年齒相歡,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1](金)劉祁.歸潛志(卷一).,史料中關于他“好賢樂進”[2](金)元好問.中州集(卷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雅喜獎拔后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于人”[3](金)劉祁.歸潛志(卷八).這樣的記載頗多。李純甫這一舉動不能單純從其為人秉性來看,應結合對他學說的傳播的作用觀察,自有其深意。趙秉文和元好問不解此,皆對他有所非議,元好問批評他“雖新近少年游其門,亦與之為爾汝交,其不自貴重又如此”[4](金)元好問.中州集(卷四).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劉祁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但在對比趙秉文和李純甫之后,劉祁得出結論“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向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后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5](金)劉祁.歸潛志(卷八).,李純甫對后進晚輩提攜有加,后進晚輩自然也就“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將李純甫當做座主恩師,傳播其學說。其中最有名便是有著“中朝第一人”之稱的雷淵,金史本傳記載他說“從屏山游,遂知名”[6](元)脫脫.金史(卷一百一十)·雷淵傳.中華書局,1975.,李純甫對雷淵為人和文風影響甚大,二人“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7](金)元好問.元好問全集(卷二十一)·雷希顏墓銘.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根據《歸潛志》記載“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卻后進,只獎譽,教為狂。’后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又如此。’”,又李純甫宗黃庭堅,文尚奇怪,主張自成一家,雷淵亦是宗黃,并在李純甫去世后成為金代文壇黃派領袖。《歸潛志》記有“雷尚奇峭造語也”,“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8](金)劉祁.歸潛志(卷八).關于雷淵事跡,參見呂秀琴,杜成輝.金末文壇黃派領袖雷淵.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9).這些背后無不透著李純甫的影子。
2.交游論學。李純甫的交游和提攜后進頗有重合,但這里注重的是其交游中的論學。學者論學自然是為了交流促進,并宣傳自己的學術思想取向。李純甫交游極多,“如周嗣明、張彀、李經、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1]。據胡傳志先生《李純甫考論》中《交游考》一段考證,僅和他同調的就有雷淵、宋九嘉、李經、張彀、周嗣明、王權、趙元、劉昂霄、李遹、劉祖謙、張谷英、馬天采、梁詢誼、王特起、高永十五人[9]胡傳志.李純甫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02,(2).,這里可以看出李純甫交游背后的尋求同道,傳播自身學識。至于其論學之處,文化象征更是明顯。李純甫與人論學,縱談古今,品評文風,有關史料頗多,現摘錄一條劉祁《歸潛志》里一段關于他和趙秉文論學的記載,可見其文化內涵:
李屏山教后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剌底,人難及也。”趙閑閑教后進為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句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后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云[1](金)劉祁.歸潛志(卷八).。
這樣的講學,對傳播其學說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隱含的文化傳承的象征意義,自是不可小覷。
3.文章著述。“文章千古事”,歷代學者除了號稱不著書的陸象山等少數學者之外,無不把文章著述作為傳承自身文化的重要方式[2]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有這樣一條記載"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成為哲學史上著名的命題,有學者考證認為,原文應是"六經注我,我安注六經",參見陳來.宋明理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203.,李純甫自然不例外。耶魯楚材為他的《鳴道集說》作序稱: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老師,深攻亟擊。宿稟生知,一聞千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贅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圣人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于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余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椹,不見好音,誣謗圣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贊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后世何!屏山哀矜,著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發揮孔圣隱幽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骎骎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拚陷韓歐之隘黨,孰如屏山尊孔圣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鉆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奧,懇為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影響耳[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李純甫為官期間志不得伸,“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稿’,其余應物文字為‘外稿’。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4](元)脫脫.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李純甫傳.中華書局,1975.,顯然是把文章著述當做表露傳承自己學說的武器。耶魯楚材在為李純甫《楞嚴外解》作序的時候,就曾直言不諱的指出:
昔洪覺范有言:天臺智者禪師聞天竺有首楞嚴經,旦暮西向拜,祝愿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竟不得一見;今板鬻遍天下,有終身不聞其名者,因起法輕信劣之嘆。若夫征心辨見,證悟窮魔,明三界之根,探七趣之本,原始要終,廣大悉備,與禪理相為表里,雖具眼衲僧,不可不熟繹之也。余故人屏山居士牽引易、論語、孟子、老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解,實漸誘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餌也[5]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楞嚴外解序.。
耶律楚材是與李純甫交善的友人,這樣的評論自然是建立在了解基礎上的允實之論。史料記載,李純甫著述甚豐,經胡傳志先生考證有33種之多[6]胡傳志.李純甫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02,(2).,可惜現如今大多散佚,百不存一,不然的話定能向我們呈現純甫思想學說之全貌。
三、選擇與接受
文化傳承有著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前輩學者對后輩的傳道、授業、解惑,另一個方面是后輩弟子的選擇與接受,也就是說文化傳承既需要傳承者的傳承,又需要有傳承對象的取舍承繼,二者缺一,不足以構成真正的文化傳承。
就李純甫而言,上文所述的與他同調的十五個人自然是比較接受他的文化觀念和學術取向的,此不贅述。但是雷淵是個例外,《歸潛志》記載他“初善李屏山,后善馮公叔獻,后善高公獻臣,最后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雷淵與李純甫這種先近后遠的關系表明了他思想的轉變和學術觀念的取舍,于是就不得不引起對他有知遇提攜之恩的李純甫的不滿了,史料中有“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后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后見其鋒芒氣勢,恐其害己,甚憚之。嘗為檄以疏其過,已而焚之”這樣的記載也就不足為奇了。李純甫去世,雷淵“作《屏山墓志》,數處有微言,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刻石,猶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怠,有不屑為’之言”[1](金)劉祁.歸潛志(卷一,卷八).,恐怕也有對他不滿的回應吧。當然,縱觀雷、李交往,當是以長久友好為主調。
師承關系中的弟子對師長學術的承繼固然是主流,但是杰出學者的影響往往不會僅僅限于門人,其學術取向無疑會對一個時期的學術風氣有著巨大的影響的。陳平原先生考察現代學術之建立時對“大學者”文化功能的評述指出“所謂‘大學者’,除了在專業范圍內做出杰出貢獻,足以繼往開來外,更因其乃學術史上的中心人物,你可以引申發揮,也可以商榷批評,卻無法漠視他的存在。史家之所以格外關注某些‘大學者’,還因其與師友弟子及論敵共同構成的網絡,本身便能初步勾勒一時代的學術走向”[2]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導言.西潮東漸與舊學新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P21)。這一評述不僅僅適用于處于學術轉型時期的晚晴民國學界學人,同樣適用于傳統文化下的碩學鴻儒。比如對于作為曾有力改變金末文風的李純甫來說,考察其文化傳承必須就放寬眼界,旁及曾與之接觸的學者的各個層次,只有這樣才能對他有一個整體全面的認識。深入了解之后,可以發現其他與李純甫交游的士人雖尊敬他的為人,推崇他的文化成就,但對他的學說和學術取向則有所選擇地接受,有時甚至是不敢茍同。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劉從益,《宋元學案》里有這樣的記載:
劉從益,字云卿,渾源人也。以進士累官御史,坐言事去。金南渡后,寓居淮陽。最為滏水、屏山所重。工詩文,滏水尋薦之入翰林曰:“吾將老而得此公,有代興之寄矣。”然尤喜其政事,曰:“官業當為本朝第一。”滏水頗欲挽先生學佛,先生不可,嘗以詩諧屏山曰:“談言正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攀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屏山笑而不忤也[3](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一百)·屏山鳴道集說略.中華書局,1986.。
趙秉文和李純甫二人都好佛,欲使從游之人亦如自己一般有著相同的思想取向,尊奉儒學的劉從益等人自然是不能贊同的。劉從益之子劉祁亦從李純甫、趙秉文等游學,和其父一樣,終身不談佛,對兩者的詩文也多有取舍,劉祁《歸潛志》自述行誼:
興定、元興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為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粗,止論氣象大概。李于文甚細,說關鍵賓主抑揚;于詩頗粗,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為文法[1]。
劉祁的取舍頗能見當時一半士人對待李純甫學說的態度,這種態度可謂具有相當實用主義傾向的。歸納來說,傳承對象對所傳承文化的選擇和接受,既有雙方不同的秉性好惡,又有學術取向的差異。考察文化傳承的時候,萬不可僅僅注意到前輩學者如何傳承自身學說,亦應該注意到后輩的接受程度,二者缺一,不足以見文化傳承之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