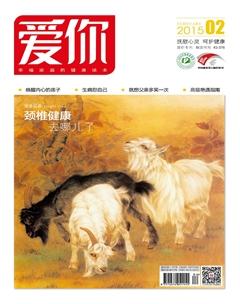八二年初夏
[日]新井一二三
1982年大二的初夏,我趁著暑假到北京進(jìn)修四個(gè)星期的漢語。
剛改革開放不久的北京,連長安街上都沒有汽車的影子,許多待業(yè)青年蹲在路邊。天黑后,他們在大街上踢起足球來。當(dāng)時(shí)的北京人還沒有穿牛仔褲的,他們一看我們的打扮,馬上就知道是國外來的。“你們是華僑吧?”他們跟我們打招呼。“不是啊,是日本人呢!”我們用日本腔的普通話說道。
“啊,原來是真由美!”這時(shí),他們的眼中充滿了憧憬。真由美是中野良子飾演的女主角的名字,來自七十年代在中國公演的日本影片《追捕》。
在北京的四個(gè)星期,我上午上課、下午復(fù)習(xí),周末參加校方安排的活動(dòng)。可好奇的我總想找機(jī)會(huì)溜出去逛街,想盡可能接觸到當(dāng)?shù)氐默F(xiàn)實(shí)生活。后來,我也跟當(dāng)?shù)氐膶W(xué)生交上了朋友。記得第一次單獨(dú)約會(huì)之際,他在西單大街南邊的素食餐廳請我吃飯,因?yàn)辄c(diǎn)的菜肴很多,導(dǎo)致我以為有別的朋友要來,其實(shí)只有我們兩個(gè)人。就那么一頓飯,他花了四十塊人民幣,那數(shù)目等于他三個(gè)星期的餐費(fèi)。第二次約會(huì)的時(shí)候,他的錢包已經(jīng)空蕩蕩的了,于是問我:“你有錢嗎?我只有糧票呢。”
北京給我的第一印象好比是冷淡的帥哥——他不會(huì)說甜言蜜語,也不會(huì)伸開臂膀擁抱你,卻有獨(dú)特的魅力,令人難忘。不過,當(dāng)時(shí)的北京也確實(shí)有很多帥哥,至少比東京多三倍——一來北方人個(gè)子高、皮膚白;二來外國人有異國情調(diào)。最重要的因素是:當(dāng)年北京沒有胖子,大家都苗條得像時(shí)裝模特兒一般。日本媒體認(rèn)為:那是中國人常喝茶、能用自然方法減肥的緣故。于是,日本市場上一時(shí)流行起了中國產(chǎn)的“減肥茶”。現(xiàn)在,事實(shí)很清楚:“喝中國茶自然就會(huì)減肥”之說是胡說八道,只要熱量攝取得少,誰都不會(huì)發(fā)胖——事實(shí)就這么簡單。
1982年的夏天,北京街上到處可見“文革”時(shí)留下來的大標(biāo)語。當(dāng)時(shí),整個(gè)北京城的飯莊、食堂只有中午和晚上的固定營業(yè)時(shí)間,如果錯(cuò)過了,就得挨餓。即使在午飯、晚飯時(shí)間,如果你沒有糧票的話,有錢也不能吃飯。可憐的外國人只好在路邊的副食品店買塊干巴巴的面包充饑。當(dāng)時(shí)的北京也還沒有普及冰鎮(zhèn)的飲料,啤酒是從公共浴池那么大的桶子用塑料勺舀起來喝的。有橘子味的常溫汽水一瓶賣三毛錢,相比之下,擺在專用冰柜里,八毛一瓶的可口可樂算貴的了。當(dāng)時(shí),除了北京飯店、民族飯店等國營飯店以外,中外合資的建國飯店已經(jīng)開門,去那里就可以吃到外國食品。不過,我們留學(xué)生覺得,跟中國老百姓一樣“大口吃喝”才夠酷,就連服裝、發(fā)型都要模仿北京姑娘,女同學(xué)們甚至互相幫忙,梳了辮子一塊去照相館拍了“中國味”的照片。(摘自《獨(dú)立,從一個(gè)人旅行開始》上海譯文出版社 圖/傅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