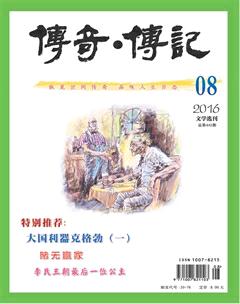正常人都會有“心病”
朱仲南
心病是什么東西?各國的說法不一樣,但無論什么樣的總結與歸納,心病都與心理、情緒有關,與環境、語境、心境有關,與人和人之間的交往、與人和自然是否和諧有關。每個人可能由不同的原因產生心病,一定是心里不舒服,腦袋混沌不清晰,詞不達意,四肢乏力等。有的人有了“心病”,可能持續一段時間,愁眉苦臉,茶飯不思,感到生活無趣,睡不安寧。也有不少人有了心病,起初來勢很猛,但無意中看了一本書,或一次偶然的郊游,和同學朋友一次沒有主題的聊天,這心病突然間灰飛煙滅,多情應笑己無端自擾,瞬間一片晴天。所以有社會經驗豐富的人總結道:心病來由復雜,但認識了它之后并不可怕,治心病只能靠心藥醫治,別無它法。
那到底什么是心藥呢?這是一個大學問。心藥的“本質”是化解,是散憂慮焦慮,是把復雜的事簡單化,是把你認為很大的事分解為每件小事,逐一排除去結,是善于觀察,善于預測,善于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就是“心藥”的主要配方。許多人認為心病自愈率很高,有心病也可找心理學專家治理,這都是有道理的。但必須記住:如果不注意調理,它造成的惡果十分嚴重。
有事找心理學專家,說對了一半,但不全面。現在不少心理學家、心理工作者,有學問沒實踐,有生活沒經歷,有專業不全面,心理學知識必須融合大量的待人處事的經驗、體會,必須融合社會學知識、倫理學知識、哲學理念、邏輯推理的基本功,才是一個合格的、知識結構良好的心理學工作者。這類人現在奇缺。現在不少心理學工作者不太會對癥下藥,不會量體裁衣,不會科學分眾,不會因人施教,結果應用的手段多是“本本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有心無力,空嗟嘆。
醫治心病,重要的手段是看人,聽事,關心人。要知道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必須很短時間內搞清楚,才可能觀六路、聽八方,心中有數。你如若不知面前的是什么樣的人,什么職業,什么性格傾向,什么地方人,十有八九胡亂吹口琴——不成調子。
治心病你若是“自治”的話,你就要和這類挑事者少接觸,少談話,一見面你三言兩語說罷立即飛奔而去。你若是為人疏導,助人一把的話,你就必須掌握“事情的要點”之后,根據此人的性格特征展開救治,一矢中的,不要“亂燉”。要注意不必興師動眾,不要四處傳播,不要上綱上線,不要夸大或百上加斤。要善于大事化若干小事,這樣容易逐一破解,善于把沉重變成云霞,善于把焦慮變成天高云淡,善于把霧霾變成藍天如洗,一望無際,不帶走一片云彩。
心病的多發者,一般是心思多的人,是比較聰明的人,是拿得起“放不下”的人,是心中裝有苦惱,沒有及時排解而積壓的人,是有困擾事喜歡攬上身的人,是敢于承擔責任但不懂計算的人。當然,有心病的人中也有一些是比較固執,比較教條,比較暴躁的人,但這類人較多是遺傳、基因及人格、性情的問題,許多是與生俱來的,是不斷重復犯的,是一種頑根或劣根性——這評價可能重了一點,但事實如此。
所以,對有心病的人,最好的辦法是抓好“四個教育”及一個規矩。“四個教育”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自我教育。缺一不可,要緊緊盯住這四類。一個規矩是建立不同年齡階段應遵守的做人做事規矩,相當于一個人的“公約”指標,相當于一個社會“公約”的限定,不可逾越。為什么說孔子、孟子的學問很好、引導力強呢?根本原因是孔孟之道,尤其孔子學說,它把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私塾)、社會教育、自我教育融合得很完美,高度的概括,行大道,是正道。
全世界的正常人都有心病,當你和一個杰出人物熟悉之后,無話不談之后,你便發現他們同樣有心病,同樣有焦慮,同樣存在著歡欣和恐懼等等。如此,我們的智庫,我們的專家,我們的科研機構,不要一股心思盯著GDP,盯著人民幣、美元,盯著高端的表面繁華而忘記和諧得體的追求,盯著發展而忘記歷史的積淀和人文精神,盯著豪車高樓而忘記生活真正的本質。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