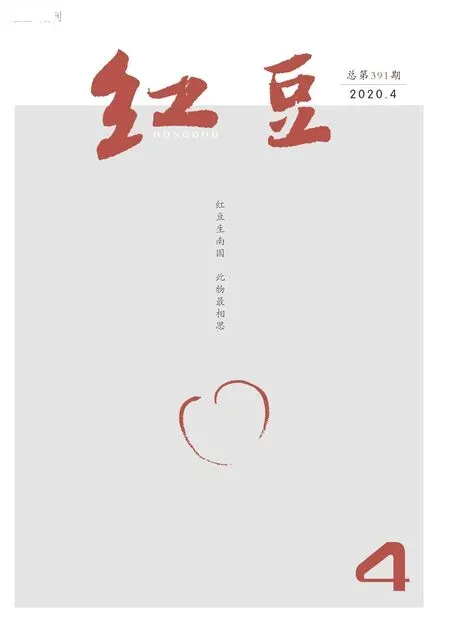故鄉(xiāng)的鳥兒
林紅賓,筆名山泉,山東省棲霞市桃村鎮(zhèn)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已在《兒童文學(xué)》《少年文藝》《綠葉》《山東文學(xué)》《雨花》《朔方》《鴨綠江》《雪蓮》等百余家文學(xué)期刊發(fā)表文學(xué)作品約400萬字,榮獲首屆齊魯文學(xué)獎。已出版長篇兒童小說《翡翠谷》,小說集《最后一只山鷹》《鬼谷》等文學(xué)專著17部。
在我的少年時代,故鄉(xiāng)村里村外有好多杏樹。陽春三月,一夜春雨輕灑,逗樂滿樹杏花。周圍的山上,全是黑壓壓的松林。沿河楊柳將河水掩映得綠瑩瑩的,相距二三里的村莊根本看不見。居高遠(yuǎn)眺,但見密林含煙,深樹吐霧,故鄉(xiāng)仿佛一幀古色古香的山水佳作。
樹林是鳥兒的家園,是鳥兒的舞臺,無論是留鳥還是候鳥,無不在這里登臺亮相,一展風(fēng)采。麻雀、喜鵲、山雞、貓頭鷹、畫眉是當(dāng)?shù)氐耐林I诫u端莊秀麗,色彩斑斕,尾翎漂亮,就像戲曲中的青衣,可惜唱腔不雅,只會“哼啊哼啊”地單調(diào)發(fā)聲。它形體較大,起飛時有些吃力,頻頻拍打雙翅,“撲棱棱”的,像一支響箭射向遠(yuǎn)處的山林。喜鵲嗓門大,站在高枝上喳喳喳地叫喚,人們稱之為報喜鳥,故年畫花鳥四條屏上有喜鵲登梅。麻雀離不開村莊,離不開屋檐,愛偷吃鄉(xiāng)親們的五谷,因此得了個“老家賊”的綽號。它們愛湊群,愛爭辯,成天嘰嘰喳喳的,時常像一些落葉“唰”地落在地面上,受到驚嚇,又“撲棱”一聲飛向別處。貓頭鷹晝伏夜出,即便數(shù)九隆冬周天徹寒,照樣站在村邊的樹上叫喚,而且還會獰笑。據(jù)說它連續(xù)幾夜叫喚,村里十有八九會有人病逝,鑒于這個緣故,人們說它不吉利,稱它為“喪門鳥”。山鴉鵲比喜鵲小得多,臉上有斑點(diǎn),像三花臉兒。鄉(xiāng)間有“山鴉鵲,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的童謠,意思是挖苦有些人一旦有了本事就翹尾巴,就連生他養(yǎng)他的親娘都忘了。山鴉鵲由于尾巴長,結(jié)果讓人們把它與不孝之子聯(lián)系在一起遭到貶嘲,委實(shí)是蒙受不白之冤。畫眉擅長打扮,描著白眼圈兒,身上還有黑褐色的斑紋,愈發(fā)顯得嫵媚,唱起來字正腔圓,娓娓動聽。
當(dāng)柳葉長齊時,一些候鳥便來旅游逗留或是在此寄居。綬帶鳥是鳥中的極品,通體五彩紛呈,尾部有兩根綬帶般的長翎,名字緣此而得。由于它愿在樹林中徜徉,俗稱“柳樹郎子”。名字很文雅,確如彩旦,唱腔清麗,惹人注目。樹鹠是柳林中的常客,羽毛為淺綠色,有點(diǎn)像驢屎蛋蛋,俗稱“驢屎綺鹠”。它短小精悍,動作敏捷,在樹冠中飛行如履平川。黃雀與樹鹠相差無幾,只是為淺黃色,常在林中獵食,它技藝嫻熟,眼疾手快,故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之說。黃鸝喜歡在柳樹上棲居,長相俊秀,音質(zhì)很美。鷦鷯不足雞蛋大,赤褐色,身上有斑點(diǎn),小家伙身手不凡,像一只飛鏢在樹蔭中閃過。鷓鴣與云雀相似,背黑腹白,頭為棕色,腿為黃色,愛吃蚯蚓和昆蟲,成天像個勤勞的農(nóng)民在田野上勞作。它不甘寂寞,時常與同類們遙相對歌。云雀喜歡站在地堰上盡情放歌,抑或振翮懸在半空即興表演,歌兒悅耳動聽,令百鳥折服。翠鳥名沒錯起,確如一塊會飛的翡翠,常見它沿河捕捉魚蝦,花鳥畫上常見其尊容。沙綺鹠是一種小水鳥,羽毛黃褐相間,尖嘴長腿,一邊“嘀溜溜溜”地叫喚,一邊像戲曲中兵卒走臺步般在沙灘上轉(zhuǎn)悠,樣子挺滑稽。
有一種鳥兒類似麻雀,叫聲為“嚎唏哩”。它有點(diǎn)憨,窩兒做得不隱蔽,很容易被人發(fā)現(xiàn),人們管它叫“老彪”。杜鵑一向懶惰,從來不做窩,而且不愿撫養(yǎng)孩子。懶人自有懶辦法,它專瞅“老彪”不在家里,就偷偷地進(jìn)去下蛋,不多不少,只下一個。按說杜鵑的蛋比它的蛋大得多,然而它卻毫無察覺,照樣孵化。當(dāng)小杜鵑出殼了,竟然“遠(yuǎn)來的和堂欺廟主”,將幼鳥全擠出窩外,讓螞蟻搬走當(dāng)作美餐。盡管禍起蕭墻,“老彪”卻在津津樂道:“好事哩,好事哩。”鄰居們聽了都將嘴一撇,心里話,你幫別人撫養(yǎng)孩子,連自己的親骨肉怎么死了還不知道,還有臉顯擺“好事哩”,你彪吧你!
叼魚郎子和野鴨離不開水灣,總是歪頭側(cè)腦地盯著水下,伺機(jī)捕獲獵物。戴勝頭戴花冠,眉清目秀,風(fēng)度翩翩,像個文質(zhì)彬彬的小生。白頭翁戴著白帽,膚色灰白,如同一位穩(wěn)重的老仆,與戴勝出沒于松林之中。
鳥兒都有防范意識,選址安家無不獨(dú)出心裁。斑鳩總愿把窩做在喜鵲窩下面,為的是仰仗喜鵲的尊嚴(yán),求得喜鵲庇護(hù)。田雞又稱麥鹠,喜歡在麥田里生活,為防不測,索性將窩兒搭在麥秸上。黃鵪最精明,把窩兒用馬尾吊在大樹橫枝的末端上,那窩兒還帶蓋兒,儼然小小的搖籃,風(fēng)兒推著他,搖啊搖啊,美化了生活,搖大了娃娃。大葦鶯更是匠心獨(dú)具,將灣中的幾株蘆葦圍擾在一起,用嘴銜著葦葉將其纏好,然后在葦叉上做窩,誰也休想偷襲。山鷹將家安在懸崖峭壁上,野獸們只能望崖興嘆。山鵓鴣在石壁的巖縫中生兒育女,就連兇狠的黑鶻都奈何不得。啄木鳥是樹木的郎中,在給老樹捉蟲祛病的同時,順勢在樹干上鑿洞穴居,繁衍生息。鵪鶉的窩在不顯眼的草叢中,即便在你眼皮底下也難以發(fā)現(xiàn)。沙綺鹠特刁,在沙灘上撲拉個窩就在里面下蛋。它的蛋跟沙一個顏色,足可魚目混珠,以假亂真。相比之下,“瞎簸箕鳥”就大為遜色了,手腳拙笨,且不擅遠(yuǎn)飛,因飯量大,老是吃不飽,人們趁它專心致志捉蟲時,將它捉住拿回家飼養(yǎng)。當(dāng)喂它螞蚱時,它把個嘴張得老大,像個簸箕,故而得名。大雁是匆匆的過客,早春和暮秋,常見它們排著整齊的隊(duì)伍,像一串歸帆,“嘎勾嘎勾”地唱著嘹亮的號子從蔚藍(lán)色的天幕上劃過。
故鄉(xiāng)的鳥兒大多不知尊姓大名,只能根據(jù)其叫聲而稱呼它們。譬如有一種小鳥,總愿站在柳樹梢上叫喚,其韻調(diào)為“吱扭,吱扭”,人們就舉一反三,管它叫“筲了帶鳥”“紡花車鳥”和“吱更”。有的叫聲為“光棍好過”,有的叫聲為“王干哥兒”,那就隨韻而名。日暮時分,深山里有一種小鳥開始叫喚,韻調(diào)為“歐——齁——”酷似病人在哮喘,人們就稱它為“小歐齁”。有一種鳥,動輒驚呼“抓——抓——”,人們就管它叫“抓抓”。還有一種鳥叫起來“咯嗒咯嗒”的,就像雞叫,人們就稱之為“咯嗒雞”。還有好多鳥兒連個俗名也沒有,只能統(tǒng)稱為鳥兒。
故鄉(xiāng)的鳥兒各有姿色,競相媲美,音色俱佳,皆有韻味。
只要你進(jìn)入山中,就會看到喜鵲衣著典雅,黑衣白領(lǐng),站在高枝上喳喳喳地大聲叫著,儼然一位落落大方的節(jié)目主持人。云雀是山中的民歌高手,如同一塊不落的石頭懸在蔚藍(lán)色的空中振翅啼囀,“啁啁唧唧勾哩嘀,哩哩哩哩唧勾哩嘀嘀……”歌兒悠揚(yáng)婉轉(zhuǎn),娓娓動聽。臘子鳥叫聲優(yōu)美,歌聲嘹亮,傳得很遠(yuǎn),尤其那花腔,宛若有人在演奏木琴。
節(jié)目依次上演,叫聲各有千秋。
啄木鳥在拍打著手鼓助興,山雞在忘情地大聲喝彩,畫眉和山雀在發(fā)表天真活潑的議論,斑鳩則不滿,與山鵓鴣在“咕咕咕,咕咕咕”地低聲嘀咕。
布谷鳥在宣傳獨(dú)身主義:“光棍好過!光棍好過!”王干哥鳥卻在斷崖上急切地呼喚伴侶:“王干哥兒!王干哥兒!”吃杯茶鳥吐字清晰,儼如一個口吃的小堂倌在殷勤地張羅顧客:“吃杯,杯,茶——吃杯,杯,茶——”黑老哇好不驚訝,像港臺人那樣發(fā)出由衷的贊嘆:“哇!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貓頭鷹在擠眉弄眼地嘲笑。
鷗齁鳥不會唱歌,只能模仿發(fā)齁的人哮喘:“齁——齁——”黑鶻長著一副兇相,只會惡抖擻地叫:“狠虎!狠虎!”再不就會用堅硬的喙啄擊巖石,“嗒嗒嗒,嗒嗒嗒。”仿佛戲臺上的司鼓在敲打小鼓。“抓——抓——”抓抓鳥動輒制造恐怖氣氛,也不知道張羅著要抓什么。
但是,隨著人口增長,故鄉(xiāng)沿河的柳林早已蕩然無存,全被墾為糧田,好多山上的松林也被砍伐殆盡,光禿禿的。村里村外的樹木寥寥無幾。鳥兒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家園,大多銷聲匿跡,有的正瀕臨滅絕。葉落知秋。亡羊補(bǔ)牢,為時不晚。否則,就再也見不到那些鳥的倩影,再也聽不到那些美妙的天籟之音了,最后只剩下人類自己,那將多么寂寞,多么清冷,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