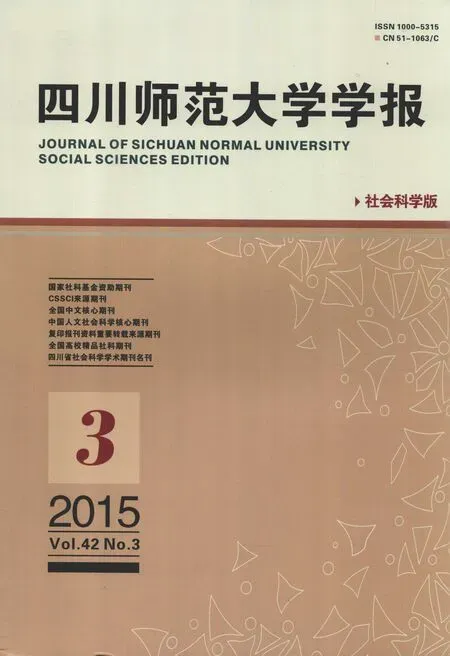清末編修民律之爭議
冉 琰 杰
(中山大學 歷史系,廣州510275)
清末編修民律之爭議
冉 琰 杰
(中山大學 歷史系,廣州510275)
宣統二年底,大清民律草案脫稿,但未能核定頒布。不久,清王朝覆滅,清末民律編纂成果付諸東流。然而,這樣的結局,不僅是時勢使然。通過考察民律編修前“民”“刑”概念的分野,朝廷各方對民律的關注和討論,民律脫稿后朝中的人事變化,民律核議時有關親權條文的爭議,以及報刊輿論的反響,可以呈現修律過程的復雜性,民律的結局是朝中不同意見妥協的結果,不宜簡單地以傳統與現代、進步與局限來評判。
清末修律;大清民律草案;刑民之分;禮法之爭;報刊輿論
學術界對清末民律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1-4]。有學者從相關奏折檔案中梳理了一條脈絡,注意到民律編修工作正式啟動的契機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禮部與大理院的修律權之爭,研究遵循的是“近代化”范式,旨在吸取法典編纂的經驗教訓,指出修律者是“政府代言人”,民律與民眾的生活習慣有差距[5],但卻未能重視清末修律過程中“刑”“民”概念的分野、“民”的概念及內涵的變化以及民律草案脫稿后朝野人士對它的態度和圍繞其中親屬編親權問題引發的爭議。雖然也有研究提到,新刑律引發的禮法之爭給民律的編修造成了影響,使民律草案“在編纂時注意了對中國固有傳統的繼承”,法律編修館也派人進行了民事習慣調查,但研究仍然沒有留意禮法之爭的延續性,忽略該爭議對民律草案稿本修訂的影響[4]。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回到清末修律與政局人事變動的歷史脈絡,考察民法草案編修核議的情事語境和史實細節。
一 “刑”“民”之分及編修民法的討論
《大清律例》不存在區分“刑事”、“民事”的語言,但是清人有“詞訟”(戶婚、田土、錢債、斗毆等)與“案件”、“細故”與“重情”(謀反、叛逆、盜賊、人命、貪贓壞法等)的概念,不過這些詞匯的內涵也不固定,或有混稱[6]41-43。 “刑事”、“民事”,這是晚清修律時受歐洲大陸法系影響才出現的新概念。修律伊始,廢除《大清律例》中的凌遲等酷刑和審案中的刑訊[7-8],成為朝廷臣工關注的重點。在這樣的情境中,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五,曾任刑部御史的劉彭年奏呈看法,不同意將刑訊完全禁止,指出應視民事、刑事案件的性質而酌情使用刑訊,稱:
東西各國裁判所,原系民事、刑事分設,民事即戶婚、田產、錢債等是也,刑事即人命賊盜斗毆等是也。中國民事、刑事不分,至有錢債細故、田產分爭亦復妄加刑嚇。問刑之法似應酌核情節,以示區別。所有戶婚、田產、錢債等事,立時不準刑訊,無待游移。至于人命、賊盜以及情節較重之案,似未便遽免刑訊,相應請旨飭下修律大臣體察時勢,再加詳慎。并飭于刑事訴訟法告成后,即將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克期纂訂,以為完備法律,則治外法權可以收回。[9]
修律大臣伍廷芳上奏覆議劉折,引用各國法律和香港實例批駁劉“酌核情節,以示區別”的問刑建議;至于纂訂民法及民事訴訟法以完備法律的意見,伍廷芳表示:“洵屬有條不紊,臣等俟刑律告竣后,即行分別編輯,陸續奏聞。”[9]
此為民律編修被正式提上修律議程的第一次契機。劉彭年把戶婚、田產、錢債等案視為民事案,把人命、賊盜、斗毆等情節較重之案視為刑事案,這樣的分法并非一家之言,朝中大臣多有相同看法。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二,伍廷芳將《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進呈御覽,在該法第一章總則第一節“刑事民事之別”中,把“凡叛逆、謀殺、故殺、偽造貨幣印信、強劫,并他項應遵刑律裁判之案”定為“刑事案件”,“凡因錢債、房屋、地畝、契約,及索取賠償等事涉訟”定為“民事案件”;他在奏折中還指出:“中國舊制,刑部專理刑名,戶部專理錢債田產,微有分析刑事民事之意。若外省州縣,俱系以一身兼行政司法之權,官制攸關,未能驟改。然民事刑事,性質各異,雖同一法庭,而辦法要宜有區別。”[10]41-44
伍廷芳以日本為鑒,認為先變通裁判訴訟法,是立法工作的當務之急,可化解因華洋爭訟而釀成的外交問題,藉此收回治外法權,所以他在刑法、民法尚未修成之前,先行編纂出刑事民事訴訟法。他這樣的工作安排,得到了修律大臣沈家本及修訂法律館章宗祥、曹汝霖等人的理解[11]。
但是,刑事民事訴訟法的先行編撰引來了很多批評,不得不暫緩施行。在眾多批評意見中,大理院正卿張仁黼在上奏中指出:
民事訴訟法,當以民法為依據,今既未修訂民法,則民事訴訟法將何所適從,未免先后倒置。至民法為刑措之原,小民爭端多起于輕微細故,于此而得其平,則爭端可息,不致釀為刑事。現今各國皆注重民法,謂民法之范圍愈大,則刑法之范圍愈小,良有以也。[12]833-836
可見,張仁黼也是把民事案件看成小民因細故引發的爭端,刑事案則是由細故引發的大案。
有研究者指出,光緒三十三年(1907)初,法部與大理院的權限之爭中,張仁黼和沈家本就已積怨,同年五月張的奏折又挑起了修訂法律權的爭奪,因為張仁黼意在請朝廷“欽派部院大臣會訂”法律,削弱修訂法律大臣的修律專權[13]。法部尚書戴鴻慈提出不同意見,而憲政編查館大臣奕劻又復議戴折。戴鴻慈主張特設立法機關(即修訂法律館),以資修訂法律,將來法院編制法、民法,修而未備的商法,待改正的刑法、民刑訴訟法等一切法律,都應由修訂法律館編纂提議改正;王大臣可為總裁,各部院堂官、督撫、將軍請旨特派會訂、參訂法律大臣,法部開單請派編纂協纂之人[12]839-842。 奕劻既不同意一切法律都統歸修訂法律館編纂,也不贊成派王大臣為總裁,主張將來刑法、民法、商法諸法典由修訂法律館草擬,其余各項單行法由各該管衙門草擬,最后都統歸憲政編查館覆定[12]849-851。奕劻的意見得旨依議。這些奏折體現了修訂法律權的爭奪和討論,固然需要注意,但有關修律步驟的看法,促進了民法編修的議程,也值得重視。
在上述爭論期間,朝廷新設的民政部也看準時機議論修律,并奏請派修律大臣厘訂民律,會同該部奏準頒行。民政部奏稱:
臣部所系為民,查歐美日本皆以此為內務行政之樞紐,惟是規模初具,綿蕞方新,凡所設施,略無成軌,自非立法周詳,相為表里,將欲變通,盡利其道無由。查東西各國法律,有公私法之分,公法者定國家與人民之關系,即刑法之類是也,私法者定人民與人民之關系,即民法之類是也,二者相因不可偏廢,而刑法所以糾匪僻于已然之后,民法所以防爭偽于未然之先,治忽所關,尤為切要。各國民法編制各殊,而要旨宏綱大略相似,舉其犖犖大者,如物權法定財產之主權,債權法堅交際之信義,親族法明倫類之關系,相續法杜繼承之紛爭,靡不縷晰條分,著為定律。……中國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稱,見于《尚書》孔傳,歷代律文戶婚諸條實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李悝六篇不載戶律,漢興增廟戶為三,北齊析戶婚為二,命曰婚戶,隋唐復更定次第,改為戶婚。國家損益明制,戶律分列七目共八十二條,較為完密,第散見雜出于刑律之中,以視各國列為法典之一者,尤有輕重之殊。……職守竊以為推行民政,澈究本原,尤必速定民律,而后良法美意乃得以挈領提綱,不至無所措手。[14]
其意見得到朝廷采納,開啟了民法典的編纂工作。
清末民政部由巡警部改名而來,下設民治、警政、疆里、營繕、衛生五司。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初九,思想較為開明的肅親王善耆被任命為民政部尚書[15]。善耆奏請朝廷編修民律,是以該部職權所系、民政所需為立論點,繞開了收回領事裁判權這一常見的論調,所逞述的觀點頗有新意,如“民”為“內務行政之樞紐”,法律有公法私法之大別,“私法者定人民與人民之關系,即民法之類是也”。善耆還注意到各國民法的體例內容,民法不是小民鬧細故那么簡單,物權法、債權法、親族法、繼承法都在民法中有定律,這些律條涉及財產之主權、人們交際之信義、家庭倫理、繼承等方面。奏折中使用“民律”一詞,與同時期的“刑律”相對應。“厘訂民律”得旨依議,此后“民律”成了官方欽定的對民法典之稱謂。不過,“民法”一詞仍然被朝野使用。
二 禮部、學部預聞民律草案
在民律編修之際,禮與法的調和問題就受到了朝廷臣工的關注。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遼沈道監察御史史履晉以“維禮教而正人心”為由,奏請禮學館與法律館共同商訂法律。八月,會議政務處上奏覆議該折,各部尚書與軍機大臣的總體意見是:
近日修律大臣多采外國法律,于中國禮教誠不免有相妨之處。除學部曾經條奏奉旨,飭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再行詳慎斟酌修改刪并外,京外各衙門亦多有指摘。查方今教育之責注重學部,應請敕下學部擇其有關禮教倫紀之條,隨時咨會法部暨修律大臣虛衷商榷,務期宜于今而仍不戾于古,庶幾責任不紛,而可以收補偏救弊之益,較為簡要易行。[16][17]
該折諭旨依議。自此,學部便能名正言順對修律工作指手畫腳,當然也預示著此后學部可與法律館共同商訂民律草案。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宣統元年(1909),張之洞以軍機大臣身份管理學部[18]。張之洞是朝中禮教派的代表,他以維持禮教為由,上奏反對日本法學家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頗得京外各大臣響應。所謂“學部曾經條奏奉旨”,應指張之洞批評新刑律的奏折和諭旨[19]。
宣統二年(1910),資政院核議新刑律草案時,議員們圍繞有關倫常諸條(如子孫違反教令和無夫奸)進行了激烈的禮、法之爭[20]。在此背景下,民律編修中禮與法的調和問題,又引來朝中大臣奏議。先是,內閣侍讀學士甘大璋奏請憲政編查館、禮學館、法律館共同核議新編的法律。十二月,禮部大臣覆議支持甘大璋,認為:“民律則日用民生在在與禮教相為表里,臣館若不預聞,非特法律館所編民律,恐有與禮教出入之處,即臣館所編民禮,亦恐與民律有違異之端,將來實行之時,必多窒礙。”禮學館建議由本館與法律館會同集議民律,再咨商憲政編查館覆核,最后交由禮學館與法律館共同奏呈頒行;其集議章程如下:一、兩館館員應互相聯絡,一、法律館編出草案底稿,應一律分送禮學館,一、兩館書籍案卷,準彼此檢查,一、民律議定之后,由禮部禮學館、法部法律館會同具奏;這些建議,得旨依議[21-22]。十二月二十七日,任職于憲政編查館,且為法律館第二科總纂的汪榮寶得知禮部奏議,又聽說憲政編查館擬于明年召守舊派勞乃宣參與核議民律,他“不禁為法典前途懼”[23]760。
禮部覆議甘大璋折時,恰逢民律草案脫稿。草案共有五編,其中總則、債權、物權編由法律館顧問日本法學家松岡義正起草,親屬編由章宗元和朱獻文起草,繼承編起草人是高種和陳箓。章宗元留學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習商科;朱獻文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習法科。高種是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學士;陳箓是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學士。此時的法律館中,隨著舊館員知識轉型和留學歸來之新館員的調進,新式法學人才成了法律館主干力量[13]。
翌年正月,《大公報》聽聞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與禮部尚書榮慶核定:“嗣后除有應行會核之件,當知照禮學館隨時協商外,并于每月舉行會議三次,研究一切問題,以資聯絡,此舉準由二月起當即實行。”[24]二月,禮學館開始核議民律。
報界輿論對禮學館核議民律之舉頗有批評意見。《北京日報》刊文稱:
法律館修訂民法、商法草案,本定于去年十二月進呈。因禮部上一折言民法與禮教攸關,必須會同本部逐條商榷方可,并要將來須會同共奏云云。禮部此折上后即奉旨依議,法律館因此遂將民法、商法已定之草案暫行擱起,未能進呈。蓋法律館皆新學之士,禮部多舊學之士,此中甚難融洽,會同商訂一事,不知如何結果。[25]
這段評論被《申報》引用,并以《禮部人員亦有商訂民法之學識乎》為題,諷刺禮部“舊學”之士參與商訂民法之不妥[26]。《北京日報》還探得,禮學館認為民律草案內容“喪失親權太甚”,俟會同法律館商訂時“將力爭之”[27]。《大公報》也得知禮學館正簽出民律草案中違背禮教之處分別駁議,但未悉沈家本意見如何[28]。
三 民律脫稿后修律大臣的更換及輿論反響
剛剛脫稿的民律草案正被禮部禮學館牽制,似難奏呈,報界輿論又對民律的前途十分關注,法律館承受著朝野內外的壓力。恰在此時,法部尚書廷用賓因患重病,請辭開缺,傳聞沈家本有補升法部尚書之消息[29]。不久,廷尚書逝世,朝廷命紹昌為法部新尚書。沈家本非但沒有升職,反于宣統三年(1911)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開去修訂法律大臣及資政院副總裁之差,回法部本任(左侍郎)供職。大理院少卿劉若曾充任修訂法律大臣,學部右侍郎李家駒充任資政院副總裁[30]。法律館的汪榮寶對此非常吃驚,并在日記中記述為“殊出意外”[23]816。
沈家本被開缺,報界紛紛猜測原因。《大公報》說到:“沈子敦侍郎修訂法律大臣一差,日前奉諭開去。茲聞其原因,系為政府以該侍郎所訂法律多與禮教不合,屢被言官指摘,且在資政院毫無建白,監國深滋不悅,故有同日開去法律大臣及資政院副總裁之旨。”[31]若依該報之言,那么沈家本被開缺一事,暗示著宣統朝新當權者(“監國”指攝政王載灃)的政治風向,即不過度羨慕西方憲政,敦崇禮教,支持守舊派。《大公報》又報,沈家本得旨謝恩,感到輕松愉快,曾語人云:“予今開去此兩項兼差,外間多有為予惋惜者,殊不知修訂法律與充資政院副總裁,此兩差最難理處,稍有不慎,非受責于政府,必受謗于輿論,無論如何,恒處于叢怨地位。今一律釋此重負,何快如之。”[32]沈看透時局,深知修訂法律大臣與資政院副總裁是腹背受怨的差事,既要應對朝廷,又要承受外界輿論的批評,行事如履薄冰,故得旨開缺而感欣悅。
其實,早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請旨開缺后,沈家本已感孤掌難鳴,萌發退意。光緒三十三年(1907),各省督撫奏議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時,沈家本的修律工作遭到許多批評。同年,大理院正卿張仁黼上奏影射沈家本大權獨攬,沈家本順水推舟請旨開去修訂法律大臣差;但憲政編查館覆議張折時,肯定了修訂法律大臣和修訂法律館是必要的差職和機構,諭旨采納憲政編查館建議,不久又任命沈家本為修訂法律大臣。由此可見,沈家本當修律大臣的幾年中,并非一帆風順[33]。
《時報》認為沈家本開缺一事不簡單,沈開缺資政院副總裁,同時溥倫開缺資政院正總裁,繼任的資政院正總裁世續是奕劻保舉,副總裁李家駒乃那桐保舉[34],這些都是軍機重臣奕劻和那桐上奏促成的。《時報》評論道:溥倫對議員“感情既深”,有恩威并濟、涵蓋眾流之度;沈家本“威望似不如倫,然沈固法律專家也,于舊律既經驗數十年,于新律亦研究數載,其智識實遠出于諸老朽之上”;那桐是“著名守舊之輩也,當在軍機時,碌碌無所短長,曾未聞有所建白,久已不協于眾望,即轉而掌內務府事”;慶親王奕劻和那桐,既握軍機中之大權,又握外務部之大權,“去歲,因彈劾軍機處案,屢為議員所迫也,固已惡之深而恨之極矣。然語有之,蛇無頭而不行。慶、那以為議員之所為,皆由倫貝子釀成之,于是以惡議員恨議員者,轉而遷怒于倫貝子,此則慶、那之處心積慮也”[35]。
似乎劉若曾充任修訂法律大臣,也是由那桐所保,而且就在沈家本開缺上諭發出的第二天,曾為學部右參議、現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的劉廷琛便奏參沈家本,請飭禮學館和法律館以大清律例為本,刪訂各新律以維禮教。《時報》隱晦地說:“樞臣因沈家本修訂法律專主從新,故保劉若曾代之,復嗾令劉廷琛奏請申明新律宗旨,飭禮學律學兩館依據舊律參訂各新律,以維名教。”[36]《申報》有《時評》稱:“沈家本既開去資政院副總裁差,又開去修訂法律差,而僅飭回法部侍本任,動輒得咎,可憐。劉若曾既肯為樞臣傀儡,又能傀儡劉廷琛,故得一修訂法律差,心勞日拙,可憐。”[37]這些議論隱射了修律背后的人事紛爭。
劉若曾是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當過翰林院庶吉士、國史館協修纂修、文淵閣校理、會試同考官、河南鄉試正考官、八旗學堂副總辦、湖南辰州府知府[38]第六卷,720-721;第七卷,137。 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任太常寺卿,同年九月改為大理院少卿[39]第二冊,1339;第四冊,3090-3091。 從劉若曾履歷可知,他對修史、科考、學務有經驗,但法律方面的工作較沈家本資歷淺。宣統元年(1911)七月,《申報》報道了劉若曾的近況,稱他是“禮教家之專門”,以孝行聞名,最得張之洞器重,被贊為“才堪大用”,將升授禮部侍郎[40]。雖然他沒有真的進入禮部,但從其仕途經歷、品行、傳聞情況來看,他于宣統三年(1911)被任命為修訂法律大臣,說明朝廷對待新律編纂的傾向性態度變化,即更加偏重維持禮教。
四 民律宗旨和親權條文的爭議
民律草案上呈御覽的進度,既因禮學館的核議工作而受到牽制,又因沈家本的開缺而受到打擊,而且其編修宗旨和一些具體內容還遭到朝中禮教派的批評。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首先上奏稱:
竊維政治與時變通,綱常萬古不易,故因世局推移而修改法律,可也,因修改法律而毀滅綱常,則大不可。蓋政治壞,禍在亡國,有神州陸沉之懼,綱常壞,禍在亡天下,有人道滅決之憂……今年為議民律之期,臣見該館傳抄稿本,其親屬法中有云,子成年、能自立者則親權喪失,父母或濫用親權,及管理失當危及子之財產,審判廳得宣告其親權之喪失。又有云定婚須經父母之允許,但男逾三十,女愈二十五歲者,不在此限。各等語,皆顯違父子之名分,潰男女之大防……該法律大臣受恩深重,曾習詩書,亦何至畔道離經若此?臣反復推求其故,則仍以所持宗旨不同也。外國風教攸殊,法律宗旨亦異,歐美宗耶教,故重平等,我國宗孔孟,故重綱常。法律館專意模仿外人,置本國風俗于不問,既取平等,自不復顧綱常,毫厘千里之差,其源實由此。[41]
劉廷琛上奏一事被各大報紙紛紛報道,輿論嘩然。《申報》載文批駁道:“劉廷琛云禮教盡滅,新律可行,不滅則萬難施行。尤如斷鳧續鶴,指鹿為馬之瞀語……至謂忠義之衰,由于孝悌不明之故,而牽引三綱以武斷其詞,尤屬不通之論……往者禮教與法律視同一物者,因學者無法律之智識,而依托禮教以規律本族之故,乃遂誤認為一種之成文法爾。不知禮教云者,屬于國民之秉彝,固為吾數千年來立國之一要素,而特不能與一國之法典相混。”[42]《申報》還刊登文章,以“隔墻似有吠花聲”①為副題,暗喻劉言似犬吠,“大學堂監督劉廷琛奏參沈家本一事,聞者莫不大嘩”,“無禮教則天下亡”,此論“奇哉”!可惜“上監國為之動容,諸老為之起敬,而新律一線之生機,又歸消滅矣”[43]。這篇評論旋即被《盛京時報》轉載[44]。
《時報》也刊文發表意見,稱:“新舊黨競爭之燒點,無過父子夫婦倫理之問題,記者對于此項新律,原不敢絕對之贊成。誠以民間習慣既久,而驟然易之以新法,則社會之心理必將為之杌隉不安,無寧受之以漸,使潛移于不覺之為愈也。然此不過就事實上言之耳。其于父慈子孝,夫唱婦隨之大義,固未嘗有絲毫之損害也”;劉廷琛“其手揮目送之巧,意固別有所在。殆欲舉憲政之全局而推翻之,非徒爭新舊刑律之優絀而已”[45]。
劉的奏折被軍機處抄發法部和禮部。禮部堂官對其中內容極力贊成;法律館認為該折所言殊與新律大有牽掣,表態將盡快會同禮部妥議辦法[46]。不久,法律館開會討論劉折,《時報》詳為報道,感嘆新律“前途顛倒”。會中,擔任法典起草員的諸日本法學家,如岡田朝太郎、嚴谷孫藏等,皆力持文明諸國法律通例,認為:“凡法律之定,自有法系,斷無合篇采用新法系,而中間忽間雜舊法系中語之理,法律禮教,各有范圍,不能牽混”;但禮部尚書陳寶琛、翰林院檢討宋育仁“皆著名維持禮教之人”,極力支持劉廷琛折;最后,法律館妥協,“議訂調停之法”,將男至30歲、女至25歲、結婚不必得父母承諾一條酌情刪減,至于父母喪失親權條則作出限定:“所謂親權者,不外數種,一管理財產權,一懲戒權,一監督權,一教育權,中間惟財產管理權,關系自由能力者大,而在親權中不過一小小部分,特提出另訂外,其余各種親權,均不在喪失之列。”[47]
結婚須得父母同意,但男滿30歲、女滿25歲之后不受此限制,這是1898年《日本民法》中的內容。梅謙次郎曾解釋該條立法原由:“子之配偶者,與父母生姻族關系,又況乎其夫婦間所生之子,復為父母之實孫,是更安可置父母之意于度外耶?時無論古今,國無論東西,結婚均須得父母之同意,蓋以此耳。惟此種之同意,果為永久且絕對之條件與否,則各國法例不一。”“本條之條件,為法律上之條件。自德義上言之,則子無論若干歲,均須求父母之同意,此固當然之事也。”[48]56-57法律館民律起草者似乎照搬了該條。而《大清律例》則規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或父母已故,由余親主婚[49]551。換言之,不管男女年齡多大,只要家中尊長健在,那么婚事就要由尊長做主。這有維護父母、祖父母親權之意,若男女超過一定的年齡,婚姻可自主,便意味著尊長親權將部分喪失。
禮學館對親權問題不讓步,不能接受父母親權有任何喪失,法律館中留學生群體則相持力辯。據《申報》載文稱:
禮學館對于民法草案,自奉諭旨以來,只會議一次。會議之時該館某提調謂中國政體向重立綱,外國政體向重平等,父為子綱,親權斷不可拋棄,如親權可拋棄,將來亂臣賊子彌滿天下矣。此說頗為一般舊學究贊成,而章宗元等十數人則竭力反對。謂中國政體向重立綱,因便于專制故也,今既改為立憲政體,即應變為個人平等自治獨立主義,以矯其依賴性,使人人均有獨立營生之能力。若親權終世不停止,父母終世有教育子女之義務,而無享子女奉養之權利。且子女犯法可問及父母,因其父母有管理之責也。果如此,則父母終身有管理保養子女之義務,子女終身有依賴安全之權利,為人父母者,不亦苦哉!況所謂拋棄者,不過俟子女成年時,或嗣有自治能力時,始拋棄其管理權,非謂從子女出生后即拋棄其權也。……新舊聚訟不決,兩派爭持甚力,因此未能解決。[50]
親權問題之爭,反映兩種修律的理念,即基于綱常的家族主義與基于自由的平等主義,而且也象征著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的中國大家長制、子從父綱的禮教觀開始受到歐美個人主義思想的挑戰。不過,從北洋政府時期《法律草案匯編》所收錄的《大清民律草案》內容來看,清末法學館在修改民律草案時,還是向禮學館妥協了。比如親屬編第三章婚姻第一節成婚之要件第二十二條有言:“結婚須由父母允許。”無男逾30、女愈25歲者不在此限的字樣。又如親屬編第四章親子第一節親權中有關父母親權喪失的規定,只限于母親再嫁后不得行使親權,女兒出嫁后,父母不得行使親權;子成年后,父母依然享有親權,財產歸父或母管理,關于財產上之法律行為,由行親權之父或母為之代表[51]。
法律館之所以妥協,與當家法律大臣的個人意志有關。劉若曾擔任修訂法律大臣后,修律態度和辦事方針都以維持禮教為宗旨,甚至有另起爐灶之意。《大公報》探知,劉若曾“決定將尚未入奏的法律草案,親加詳閱,大為修改,總期符合禮教,便利通行”[52]。《北京日報》載文說:“修訂法律大臣既經易人,辦事方針亦略有改變,聞沈大臣手中所業經訂成各草案,現在劉大臣均擬另行纂輯云。”[53]《大公報》亦報道:“劉仲魯少卿對于修正法律一事,抱定維持禮教宗旨。”[54]至于民律,劉若曾很不滿意其中的親屬編和繼承編,有意今后奏呈民律時,將兩篇除開,暫時不奏。法律館的汪榮寶在宣統三年(1911)五月十一日日記中寫到:“到修訂法律館,子健告予親屬及承繼法中,問題甚多,仲魯畏首畏尾,意主遷就,現擬將此兩編提開,暫不具奏,委諸將來編纂云。甚矣!編訂法典之難也。”[23]893九月,修訂法律大臣果然拋開親屬、繼承編,只將民律草案的總則、債權、物權編上呈御覽,奏折稱:“凡親屬、婚姻、繼承等事,除于立憲相背酌量變通外,或取諸現行法制,或本諸經義,或參諸道德,務期整飭風紀,以維持數千年民彝于不敝……親屬、繼承二編,關涉禮教,欽遵疊次諭旨,會商禮學館后再行奏進。”[12]911-913十月,辛亥革命爆發,時局驟變,民律草案不了了之。北洋政府修訂之清末民律,雖未頒行,但民間訴訟仍以清末民律草案為法理依據之一②。
編修新律是清末新政變革中的重要環節,是近代中國政制轉型的重大舉措,但民律的編纂議程和進度卻相對滯后,民律草案脫稿后還陷入禮、法之爭,并且未能核定頒布。正因為有這樣的結果,導致學術界對民律的研究,多致力于尋找它的局限性,并把它放入中國法律近代化進程中給予定位和價值評判。前述通過對民律編修前“民”“刑”概念的分野、朝廷各方對民律的關注和討論、民律脫稿后朝中的人事變化、民律核議時有關親權條文的爭議以及報刊輿論的反響等方面的考察,一定程度呈現了清末民律編修核議過程的復雜性。可以說,民律編修被提上議事日程,一方面是因為清末修律參照了同時期歐洲大陸國家和日本的各種法典,修訂法律大臣和各部臣工開始區分“民事”、“刑事”為不同的概念,編纂單獨的民法典成為必要;另一方面也是朝中各方分爭修律權使然,大理院、法部、憲政編查館、民政部、禮部、學部都把參與核議民律納入自身的職事范圍,推動了民律編纂核議工作的進程,而修成的大清民律草案則是朝中不同意見妥協的結果。因此,恐怕不能簡單以傳統與現代、進步與局限來評判清末民律草案的編修核議過程,而應回到清末修律與政局人事變動的歷史脈絡,考察民法草案編修核議的情事語境和史實細節,從而更深入、更細致、更客觀地揭示民律草案編修核議進程的復雜性。
注釋:
①清中期詩人李勉有詩云:“誰家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塵,偏是關心鄰舍犬,隔墻猶吠折花人。”
②張生教授在《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一書中認為,民律草案未經清廷正式審議,在清末民初都沒有正式公布施行,裁判官的知識水平和法律意識與草案“存在較大距離”,“當時大多數法律界人士對該草案知之甚少”。此觀點并不準確。因為雖然民初南京臨時政府有令對清末民律草案不予援用,但是草案親屬編的離婚條文卻在民間婚姻訴訟的案例中被律師援引,而北洋政府大理院也承認該條文內容有效。比如:1913年,北京附近大興縣的于某與妻張氏訴訟離婚,于某不滿京師高等審判廳的判決,上告大理院,訴狀陳述離婚的理由,全部引自清末民律草案離婚條文;大理院接受了訴狀,依據原訴訟記錄,又通過審訊,了解事實后,逐一駁回了每條離婚理由,認定離婚事由與法定離婚條件不符。此案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第六冊《大理院檔案》,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458頁。
[1]楊志昂.晚清民法觀念的變遷與清末民律的修訂[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4(3).
[2]張生.大清民律草案摭遺[J].法學研究,2004,(3).
[3]孟祥沛.《大清民律草案》法源辨析[J].清史研究,2010,(4).
[4]王彬.清末民律修訂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5]張生.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6]吳佩林.清代縣域民事糾紛與法律秩序考察[M].北京:中華書局,2013.
[7]李欣榮.清末修律中的廢刑訊[J].學術研究,2009,(5).
[8]李欣榮.清末死刑方式的轉變與爭論[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
[9]修律大臣外務部右侍郎伍、刑部左侍郎沈奏復御史劉彭年奏停止刑訊請加詳慎折[J].東方雜志,1905,2(8).
[10]伍廷芳,等.大清新編法典[G]//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270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11]伍侍郎編纂裁判法之用意[N].申報,1906-03-29(3).
[12]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G].北京:中華書局,1979.
[13]陳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訂法律館:中國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14]民政部奏請厘訂民律折[J].東方雜志,1907,4(7).
[15]上諭[N].申報,1907-06-19(2).
[16]掌遼沈道監察御史史履晉奏禮學館宜專派大臣管理與法律館匯同商訂折[J].政治官報,1908,(234).
[17]會議政務處奏議覆御史史履晉奏禮學館宜專派大臣管理與法律館匯同商訂折[J].政治官報,1908,(300).
[18]關曉紅.張之洞與晚清學部[J].歷史研究,2000,(3).
[19]李欣榮.如何實踐“中體西用”:張之洞與清末新刑律的修訂[J].學術研究,2010,(9).
[20]李欣榮.清末關于“無夫奸”的思想論爭[J].中華文史論叢,2011,(103).
[21]禮部奏遵擬禮學館與法律館會同集議章程折[N].北京日報,1911-02-14(3).
[22]禮學館將參預民律[N].申報,1911-02-19(1:4).
[23]汪榮寶.汪榮寶日記[G]//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21-623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24]法律禮學兩館之聯絡[N].大公報,1911-02-16(2:1).
[25]新律延擱之原因[N].北京日報,1911-02-26(2).
[26]禮部人員亦有商訂民法之學識乎[N].申報,1911-03-06(1:4).
[27]反對民法因恐喪失親權[N].北京日報,1911-02-28(2).
[28]大清民法尚須詳擬[N].大公報,1911-03-08(2:1).
[29]沈侍郎將升法部之預聞[N].大公報,1911-01-17(2:1).
[30]上諭[N].申報,1911-03-23(1:3).
[31]沈侍郎開去兼差之原因[N].大公報,1911-03-26(5).
[32]沈侍郎撤差后之愉快[N].大公報,1911-03-30(2:1).
[33]史洪智.清末修訂法律大臣的政治困境[J].史學月刊,2013,(1).
[34]專電[N].時報,1911-03-23(2).
[35]論資政院更調正副總裁事[N].時報,1911-03-24(1).
[36]專電[N].時報,1911-03-24(2).
[37]時評[N].申報,1911-03-25(1:6).
[38]秦國經.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G].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39]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0]京師近事[N].申報,1909-09-11(1:5).
[41]劉廷琛反對新刑律奏折[N].時報,1911-04-05,06(4).
[42]辯劉廷琛反對新刑律[N].申報,1911-03-29(1:3).
[43]劉廷琛參沈家本之原奏[N].申報,1911-04-02(1:5).
[44]劉廷琛參沈家本之原奏[N].盛京時報,1911-04-12(2).
[45]劉監督參劾新刑律疏書后[N].時報,1911-04-07(1).
[46]法律館與劉廷琛[N].大公報,1911-03-28(5).
[47]新刑律之前途顛倒[N].時報,1911-04-08(2).
[48]梅謙次郎.日本民法要義(親族編)[M].陳與燊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49]大清律例[G]//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50]禮學館親權之爭議[N].申報,1911-04-22(1:4).
[51]大清民律草案[G]//北洋政府修訂法律館.法律草案匯編(一).北京:京城印書局,1926.
[52]劉大臣調閱未奏法律草案[N].大公報,1911-03-29(2:1).
[53]法律草案另纂之風聞[N].北京日報,1911-04-06(2).
[54]劉大臣修正法律之方針[N].大公報,1911-04-21(2:1).
The Dispute of Drawing up the Civil Law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AN Yan-jie
(History Depart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
The Civil Law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completed in the end of 1910,but it had not issued.Soon the Qing Dynasty collapsed,which means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Civil Law became in vain. However,That is the unchangeable the trend of times.By studying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the attention from all parties of the royal court and their discussion of the Civil Law,personnel changes after the complete of the Civil Law,and different opinions of the parental right in the Draft of Civil Law,and the reflection from the newspapers and press were all proves to show the complexity of amending the law.The Civil Law was a compromise of various views of the court so that it’s improper to evaluate the Civil Law with the simple conclusion as being whether traditional or modern,progressive or limited.
amending the civil law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Draft of Civil Law of the Qing Dynasty;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criminal and civil;the dispute of feudal ethics and law;the public opinion in newspaper
DF092.49
A
1000-5315(2015)03-0149-08
[責任編輯:凌興珍]
2014-06-29
冉琰杰(1985—),女,土家族,貴州銅仁人,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