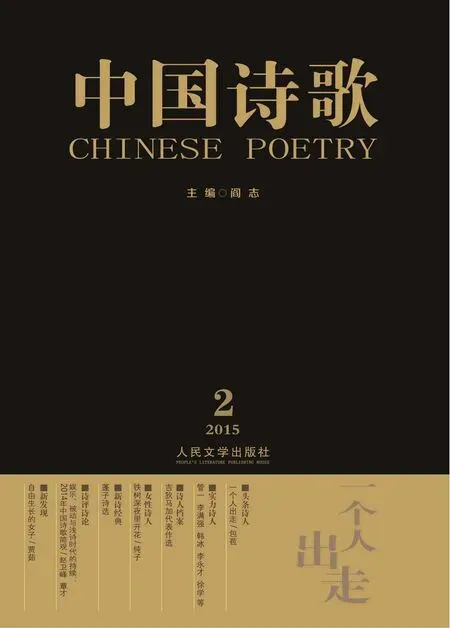竹之箋(七章)
□耿林莽
竹之箋
竹林滴水。
每一片葉子都流著自己的淚。
有一滴落到你的眉尖上了。
“涼的!”你說。
只有竹葉子流下的淚,有著如此清涼的氣息。
晚上,竹葉子流下來的,便不是淚,而是清淡的月色。
你喜歡藏在月光照不到的竹影深處,聽風吹葉響,仿佛在劃動著槳櫓。
而現在,這槳聲聽不到了,因為,
你早已離開了竹林,你已經去遠。
風聲簌簌,細雨如梭,風雨中的竹林,是一個音樂的王國。
一千片葉子都在顫顫地動著,動著。
他們說了些什么?
摘下一片來寄你,便是一頁
竹之箋了。
竹之箋,你收到的時候,她早已干枯,
再喚不出一片淡淡的,淺淺的翠色。
再喚不出一滴,音樂的殘留。
在此人間
渺渺長空,無一只禽鳥飛過。
在此人間,有一間屋子寒冷,孤獨。
窗子外面,光禿禿的樹枝條上,一朵臘梅花,開了。
(何處駛來的,一艘
冷冰冰的船?)
冬之孤女,涂了蠟的嘴唇,什么也沒有說,
這一瓣淺黃色的,瑟縮的微笑,忽使我想起,想起你目光深處的寒……
在此人間,我們不幸相遇,相遇而又不能相守。
目光深處,波濤隱約,是海的青色,并不溫暖。而寒冷,乃雪的搖籃,人性中深沉的一角。
我在想,數千里外,荒涼的邊陲小鎮,你正仰起面孔,承受著碎雪的一吻。
在此人間,我們不幸相遇,相遇而又不能相守。
思念乃釀成一種不治之疾,如一尾蛇在纏繞,蜿蜒。
在此人間,我一無所有,光禿禿的樹枝條上,那一瓣寒冷之唇,喚來了漫天飛雪,凝聚著風的戰栗。就將她視為一種問候,一種祝福吧,如何?
水橫枝
勒馬于懸崖,凜凜然萬丈絕壁。有一株古樹不老,伸出勁臂,橫越于水上。
這,便是水橫枝了。
水橫枝,在水之鏡中顯影,
郁郁蒼蒼的葉子,如翅如羽,引發了小魚們的追逐:
一種飛翔的幻覺,油然而生。
水橫枝,裸體的花朵淡雅,潔白,
暗香浮動,柔弱花瓣一片片飄遠,如船。
那影子因水的波動而飄忽,而模糊。
(誰聽見了她們的槳櫓?)
歲月流去,水流去,悄然無語。
瘦
水波紋折疊,起伏,清清淺淺,每一折都呈現各自的獨特。不同體式,不同品位的瘦。
風之影移動,日之影匍匐,留一種簌簌之聲于寂然的水濱。
逃亡之水,瘦是隱于其間的一尾尾小魚,模擬著水波紋的身段,沿著她們的足跡,在游。
瘦山,瘦水,瘦瘦的竹。
一片片青竹葉子,淡淡地青著,淡到近于無。
風來的時候,雨來的時候,聽見了她們相互的撞擊,或是,靈魂被撕裂?
還是一種自言自語呢,歸屬于
瘦瘦的孤獨。
而在你的眼波濤里,總有一條條光亮的小魚,在安然地游。
干凈,潔白,是寒冷所孵化的,一朵
弱小的閃電,而不是雷。
夜深人靜時刻,月光悄然而來,纏繞你顫顫的手指,我聽見了一種聲音,在對自己言說:
“瘦,是一種精神,一種氣質。”
門 洞
老屋。
老屋門前的古潭,積水深綠;天光剪碎的樹影沉重地壓在上面,不堪重荷。
老屋。
老屋的身后,綿延著荒山一脈;朽木枯株,兀鷹們不肯一落。
老屋。
老屋墻上排列的青磚,昏暗肌膚的粗糙裂縫之間,滲出了歲月的夢魘,灰鼠般進進出出。
老屋。
老屋的門洞里貯滿了濕漉漉的陰森,不是黑,是比黑更神秘些的
莫名的恐怖,漸漸變成了謎一般的誘惑。
陽光無法穿越;晚上也不點燈;
門洞之謎遂成為永恒。
門洞深處,昔日的影子藏在其中嗎?
羽毛,根須,獸的碎骨殘渣;人的牙齒咬嚙過的器皿,藏在其中嗎?
那些蟄居其間的幽靈,躲避著世界的追問。
黃昏
進門洞去了。我想等她出來,探一點“最新消息”。
然而,一只黑貓鉆進沒有。她再沒有跨出神秘的門洞。
幽靈的腳步
六朝古都,龍盤虎踞的南京城,曾被血洗過。三十萬亡靈沉睡地下,每年的耳朵,都聽得見
靖國神社里熾熱的香火,提醒往事于遺忘的深淵。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門口,密密麻麻罹難者的影子,螞蟻般爬游,黑窗簾在紀念館的陳列室內,抖動不休。參觀者不敢咳嗽,怕驚動了
戰戰兢兢,膽怯的亡靈。
花壇,草坪,一望無際的淺淺碧波,遮住了當年人頭落地浸血的泥土。所有的骨骼早已塵化,消釋于無。
歌聲和畫舫的秦淮河,陽光燦爛,嫵媚依舊。李香君們腰肢舒展,她們彈唱的曲子,亡靈們一句也聽不懂。
喧囂和歌聲沉寂之后,夜已熟透,是金陵春夢正酣的時刻。三三兩兩寂寞的幽靈才探出頭來,放風式地在路邊的草坪間小坐片刻,隨后,又消失了。
誰聽見了他們的腳步?
天 籟——擬阮籍
天籟
奇特的一種聲音,從哪里飄來?
一只蜜蜂,隨砍柴的樵夫飛過,綠幽幽的山谷,油茶花正開。
天籟!
奇特的一種聲音,從哪里飄來?
打唿哨的詩人,吹口哨的詩人,是你,走過一段田野,登上了奇峰:蘇門山。
悠悠地,清徹而尖利,唿哨聲直入云端。
你是在呼天。天,在你的唿哨聲中,抖開。
你是在呼地。一切禮教的羈絆,世俗的煩擾,統統被驅散。
何必再寫那些如履薄冰的詩,風吹草動時,每一句都成禍源。
倒不如躺在這里,脫光衣服,讓陽光輕輕撫摸。蘆葦葉子與青草的香味俱在,一只只蝴蝶潔白地飛來。
遠處傳來砍柴人深山里伐木丁丁的節拍。白茫茫的水,在流:松濤正澎湃。
你輕輕地以唿哨之聲應和:天籟!
這時候,天又下起微雨,淋濕了你的裸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