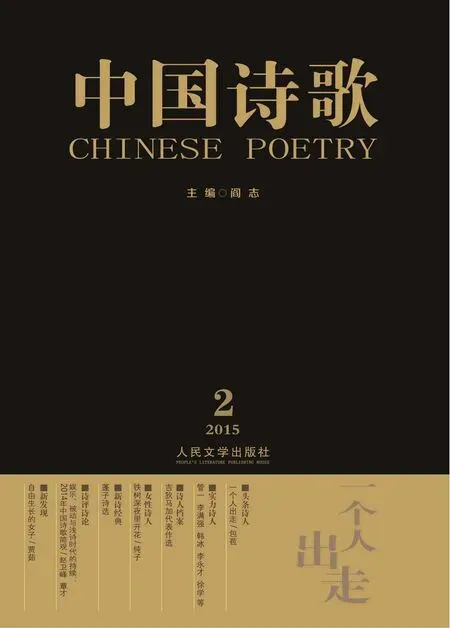林中私語(十章)
□許 淇
林 語
林語。
森林在說話。
猶如發自體內神經的耳鳴,痙攣的震幅,那聲音是懸浮于深潭之上的朦朧月色,是不確定的模糊輪廓的流動空間。
耳鳴不絕。溪澗瀨響。回溯最初的潛滴暗流,不知在哪一塊被苔蘚覆蓋的石頭底下躲藏——
吹著笙笛的小精靈,
在傾吐生之喜悅。
新栽的小樹的芽,幼兒的嘴里,粉紅的牙周像花苞,因為呵癢而嘻開了,一朵朵懵懵懂懂的歡笑。
葉子擦著葉子,嫩枝摩著嫩枝。
是即將出巢的雛鳥,振動光的羽衣。
是凍土苔原的馴鹿,舔著石松和鹽。
是白樺林里最后一抹冷卻的夕照,終于淬了火,青靄的暮煙吱吱的響。灰鼠和花鼠在枝頭親密地私語。
當神秘的黑夜襲擊老林,由上而下降壓一股濃重的腐爛植物的濕氣和令人暈眩的松脂香,以及夏季候鳥留下的亞硝肥料的氣味。
山貓經過那里的腳步,令人心悸。
欲望的季節,胡蜂毀了巢,發瘋似的螫熊瞎子。鑼鼓鏜韃聲掩蓋了一切。
風葬的鄂溫克老阿爸,跨越了死之門限,像他的祖先那樣,被高高地架上百齡落葉松的樹梢。這時,風卷著陽光奔瀉而來,洶涌著葉浪,將無欲的老人顛簸在森林之上。
而此刻在林中,食肉獸暴露著誘惑。蝴蝶雙雙合而為一。花朵每一蕊都赤裸著。鹿哨在顫聲呻喊……
繁衍生殖,狼藉滿地,森林必須經過一番洗滌……
雪,恰恰在這時刻,并無預示地降落下來。白雪是無瑕的、干凈的。雪是真實的,是固體的霧。
是所謂“白色的寂靜”。果真寂靜無聲了么?一切動作都休止,世界因此永恒地沉默了么?
但,聽啊!這里,那里,整個森林在說話。樹枝承受不住積雪的重壓,彎曲,彎曲,大塊的雪落下,樹枝反彈,連帶所有的枝椏條件反射似的顫抖,雪刷刷地崩潰,發哀松碎玉之聲。

在密林深處
密林深處的白樺林像一群蒼白消瘦的詩人,是另類,被黝黑的落葉松重重包圍;又像一群自我沉湎的芭蕾姑娘做無伴奏的亮相。興安嶺欲相抱相擁,空 的間離卻無法逾越。
然而,彼此都遭遇激情。激情使一切矜持化為烏有。是激情升華理性,還是理性升華激情?聲光雷電過后,陣雨是令人窒息的吻。于是,整個森林急劇地喘吁。小白樺尖叫著。落葉松分泌出多汁的芳香和濃郁的淚液。貝爾茨河昏厥了,河水暴漲如獸。
橫倒的豎琴,瘋狂的手指抹過一串琴音。
河水淹了草地和林中空地,冒一股腐爛水草和鮮蘑菇的氣味。草叢中藤似青蛇,向樺林游去;忍冬、野百合、白頭翁、櫻草、迷迭香……全都半醉半醒。(我赤裸的靈魂在雨林中。我像愣怔的樹木一動不動。我忘卻了自己。在無比的喜悅過后,手指的綠在一寸寸地瘋長。)
雨住。白樺林如一座圣潔的殿堂,祭壇的枝形燭臺上,每一棵樹都點不著燃燒的火焰。河面上蒸騰白煙,冪一層霧紗,小白樺像道姑或新娘,將童貞奉獻給了愿望。(我在撮羅子旁挖一條溝引開澗水,燒潮濕的苦艾草熏制肉干。今天,山巒的云靄的郁結化不開。今天,是喝酒唱歌的日子。)
虹的出現是森林上空意外的驚喜。
轉瞬間,白樺變成一群歡笑的孩子,齊搖著淺金的、嬌綠的鈴鐺。但有一株被風雨強暴,躺倒在近側百年落葉松的懷里。
落葉松喜極而泣,頻頻譫語:小白樺是我一生的思念。
落 葉
落葉,覆蓋了林中小徑。
落葉似花,我愿采掇。
行將死去或已經死去的落葉也是收獲物,他們慎重地告訴我另一個世界的消息。落葉似金黃的,是溫暖的,即使被蟲蛀過玲瓏多孔,即使遭扭曲后蜷縮而呈衰頹。思想的火焰之本質功效乃“點燃”和“照亮”,不在于它的外觀是盛綻還是凋萎,是飛花還是落葉。
它輕輕的訴說,你或許聽不見,在你的腳下發出愛的警告,因為那終結是歌的止息。
落葉,一片又一片。
北方森林中的落葉積累千年的腐殖土。我愿采掇。隨意地拾取思想,赤裸的思想沒有形式,赤裸的語言便是思想。將獨自的紙片收集起來,會聽到出人意料的吶喊,瞬間完成了“我”。
綿延的時間和短暫的瞬間并沒有區別,如晨起吸納清新的空氣又吐出;如風吹樹葉顫動而悄吟;陽光將整個森林鍍金然后又洗盡鉛華。
最后一片葉子被暴風雨催離枝頭,滿身掛著雨滴淚珠,依依不舍地告別母體、回歸大地,如神話中的安泰,死而復生。
落葉,一片又一片。
林中的湖
森林中低洼的塔頭甸子中間有多年冰雪融化沖積的湖泊。
林中的路直通湖里,致使一頭涉世不深的小鹿不幸溺斃。
幾年前有過一對失路的天鵝在那里棲息。舍倫巴圖老爹命名這湖叫“天鵝湖”。
深夜,他聽到天鵝悲哀的絕唱。
每年,天鵝或別的水鳥僅僅途經。
因為湖里沒有魚,缺乏生物鏈。
這是死亡的湖,無生命的湖,不孕的湖。
湖底有一個冰冷的世界么?
我不知人是怎么死去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然后四肢漸漸僵硬,意識沉墜入黑暗,而眼睛依然亮著一絲微弱的希望,視網膜的功能最后起著作用,末了,罩一層淡霧的白障。
舍倫巴圖老爹在他的林中小屋里死去了,他眼睛始終睜著,似乎瞳仁里映現林中的湖。
暮色中森林幽暗,湖還亮著。米·普里什文說:湖是大地的眼睛,該也是森林的眼睛吧?
但森林時常先閉住眼睛,若催眠狀態,四周的樹木仿佛在夢游。夜盲的目視而不見,相反,天空像綠的湖,星星滴著水珠。翠翠的星星雨。
雨霽。湖映影幻美迷彩。虹若挑逗的眉。
白樺林里住著神秘的光,如迸發的靈感。
失眠的白夜里哀愁的情緒凝止的湖呵。
林中的湖是不孕的圣處女。
流 取
流取即水聲,嘶嘶的。
水聲,很遠很遠,一陣模糊的夢囈。
訴說夜心的沉哀么?
嘶嘶的,黎明的熹白,疾步而來。
稀疏的再生林如缺牙的老婆婆,吧咂漏風的嘴,唱一段流傳久遠的謠曲。
唱。水聲。應和著斷續的溪流。
跳躍的山神。林鳥的謦咳。
忽而水聲中止,思想一片寂靜。
有一種力量,由遠而近地流瀉,沖過淺灘,沖向深淵。落葉和羽毛,就是滿帆的行舟——抵達或者覆沒。神經質的纖白的指尖,在比牙琴的黑鍵上滑翔。
河中央有一根倒木桿,流水趴在那里喘息。因為深層意識的空洞,心里表象有險惡的漩渦。一顆溺斃的靈魂,碰撞林木發出魔鬼的詛咒。
直到河流漸開闊,各路水聲匯齊一泓。水面上有閃光的雪,洗凈了白石的丹心。
水是冷的,水是熱的,水是又冷又熱的。活水水流,涓涓、潺潺、淙淙……
流取生水聲。無窮生命力的激蕩!
興安嶺秋歌
落葉松的葉子是針狀的,到了秋天,就像金黃的茸毛,金黃的發絲,在曉風中舒卷,在夕照里瀟灑。
在落葉松林中,當葉子掉落,你腳踏的是圖案斑駁的細軟的針毯,是大自然用時間的經緯編織的。
深紅的柞樹下面,臨風顫搖著淡黃的線葉菊,那是夢寐著的斑斕的秋。
在斑斕的秋之夢寐時,落葉松、蒙古赤松、柞樹、黑樺和白樺,彼此之間似有特殊的默契和關聯,整個原始森林在手拉手地詠秋歌而曼舞。針葉和闊葉混交的森林,秋風沒有忘記去親吻每一片樹葉。
于是,森林里不停地紛落著黃金雨,把小徑、把風倒木全埋了,轉瞬間,一切都顯得異樣,樹與樹之間,彼此隱藏著黃金的秘密。人也被周遭的秋光照亮了。小白樺掛著無數鈴鐺隨風搖蕩,你聽到甜蜜又怯生的嘆息。
林子的那邊流過阿里河。阿里河水是藍的,湛藍,湛藍,藍得那么深,那么濃。
秋 夢
邂逅林中,秋,靜美而清幽。
落葉松,你的針狀的睫毛——啜露的,餐英的。你的濃密而深垂的睫毛待風來輕吻。
深紅的柞樹林!臨風顫搖的淡黃的線葉菊。我不禁迷醉于你的斑斕。
秋,你在夢寐,我倆都在夢寐:
再不要關于刀斧的噩夢,貪婪、貧窮和愚昧,是盜伐者的三把利斧。
我只愿夢見落葉松、蒙古赤松、黑樺和白樺,整個森林手拉手地詠秋歌而曼舞。
獵 狗
獵狗,它叫尼坎。
像黑色的閃電,透射淡藍的光。
鳥似的掠過。哪怕被灌木枝劃破皮膚,流著血,蔓草間似珊瑚紅豆。

主人的臉是各種各樣的符號。笑是一種可愛的符號,黃黑的板牙展露,便拋來一塊鮮嫩的脂肪肝。醉酒是又一種符號,莫名其妙的昏昏然和茫茫然,酒后便出現了哭的符號。呵,人類的悲戚也讓它傷情。有的符號尼坎費解,因為人就是一個偉大的謎。它可以捕捉到榛雞,卻無法捕捉這個謎。
有時候饑餓為了攫取,主人是殘酷的野獸,他吝嗇每一粒鹽,每一塊肉,直餓得尼坎眼花,森林旋轉,星光翔舞。尼坎恨他,但卻更加愛他、愛他。
槍口。死神的瞳孔。嗚嗚鹿角,永遠在召喚,讓尼坎激動得如同穿石的湍流。金秋的嘹亮,在黃葉林里,拾到沉酣的歡喜。
它滿足地伸直前爪,將臉埋下,瞇細眼睛,斜眺樹冠上遠山巔的雪線。枝隙溫暖的陽光,舐著自己的傷口,牙齒回味著飛禽的熱血。像一名退伍的將軍。尼坎果真老了么?夢繁而碎而更多了么?
森林乃至自然的法則是嚴酷的。
它已經感覺到太累了,疲乏侵襲僵軟的四肢。它希望永遠躺下,
但,耳邊始終響著那嗚嗚的鹿角。
納西斯
希臘神話里有一個美少年納西斯。
俯臨平如明鏡的深淵,他只為自己的美麗而醉。
朝朝暮暮,守望著這真實的幻影。
他憔悴了,他投水死了,變成一叢搖顫的水仙。
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說:“……我沒有在岸邊待過。”
也許他怕在水中看見自己?
興安嶺的馬鹿棲息在順風的山坡,
機警而靈敏,任何外來的偷襲不能讓他們就擒。
當雄馬鹿來到水沼邊,它驚訝地見到自己珊瑚枝般多叉的角茸,
華美煥發,玉樹臨風,簡直太美了!
雄偉的馬鹿果真是鹿中之王。
幽暗的樹葉,叢密的花冠,透徹的天光,勾畫出它頸的柔韌和角的變化。
它俯首細細地端詳,這難道是“我”的映象?
要認識“我”并不容易,必須審視再審視,認真地看個真切。
它敏感的鼻尖埋進沁涼的柔波,一陣微妙的顫動,蕩開了漣漪。
模糊了,攪和了。
藍天、綠葉、鹿角、枝丫、草花、眼睛……它感到幻滅,難道“我”竟是如此脆弱么?
漸漸地,深淵恢復表象的平靜。再凝注:
——遠遠觀照完整的形。
馬鹿徘徊不去,它欣賞自己,忘掉一切。聽,有回聲:“美少年,美少年,納西斯!”
這時,早就躲在沼邊灌木后面的盜獵者扳扣了槍機。
維吉爾從岸邊逃遁。
他甘愿引領但丁赴難地獄的忘川。
紀德卻偏偏要到水邊:“俯臨意象的深處,慢慢地參透象形字的奧義”(卞之琳譯)。
由自戀而戀他,瓦雷里的“他”:“想象這千萬的熒熒群生只是他的自我化身……”(梁宗岱譯)
而我國詩人一向將水仙花比作女身,“凌波仙子”是她的別稱。
“一江湘水碧漪漪,波上夫人淡掃眉。”(徐渭詩)
納西斯如同馬鹿一樣徘徊不去,諦聽水湄凌波仙子的簫管、泉聲和四山仙女們應答的回聲。
黑天鵝
在高高的山上森林里潔凈的湖邊。
湖水是去年的冰雪融化成的,
所以潔凈如野天鵝的羽翎;
冰雪是被綻出泥土的百花融化的,
所以湖心漾著春天的柔情。
野天鵝飛來了,排著隊飛來了,在黝黑的樹冠上空,呼喚著:
“咕咕,嘎——!咕嘎!嘎——!”
收斂翅膀,落在湖邊——依然去年曾經的湖邊。
湖邊有一個達斡爾族少年,他驚訝于神奇的降臨。
他吹彈起一種達斡爾族祖先流傳的古老的口胡——嬌小的小庫蓮。
那不過如同微風吹拂樹葉的喧響,只有天鵝才能聽得見。
“嘎咕——!咕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