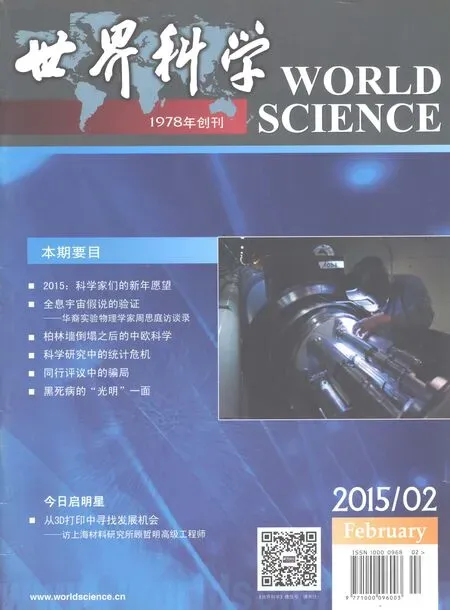柏林墻倒塌之后的中歐科學
王大鵬/編譯

●在東歐劇變后的25年間,地處中歐的各個國家都在科學事業中奮力顯現自己的地位。
在一個仍可聞到油漆味道的新裝修的實驗室里,卡塔日娜·科摩羅斯卡(Katarzyna Komorowska)嫻熟地操作著一臺看起來十分前衛的咖啡機一樣的機器。而實際上這是一臺高端的掃描電子顯微鏡,這臺機器能夠操作精致的樣品并且對微小的細節進行可視化。這臺機器是科摩羅斯卡的實驗室中擁有的高端設備之一,該實驗室位于波蘭西南部的弗羅茨瓦夫。科摩羅斯卡打開這臺設備的離子束,幾分鐘后,一個屏幕上就顯示出一個刻在石墨烯分子上的長胡子小矮人的清晰圖像,這個圖像是她剛剛刻在一粒沙子上的。
這粒蝕刻的沙子既是一個歷史回響也是一個技術偉績。這個小矮人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于弗羅茨瓦夫的抵抗波蘭政權的抗議運動的象征。現在它已經成為了這個城市的吉祥物:弗羅茨瓦夫有超過300尊矮人雕像,參觀者們可以用小冊子和應用程序來追蹤他們。這個矮人的形象可以在幾秒鐘的時間里刻在一粒沙子上這樣的事——也象征著這個城市在成為中歐科學樞紐方面所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自2007年以來,歐盟撥出超過2億歐元的經費幫助弗羅茨瓦夫從廢棄的軍事醫院轉變為致力于學院科學和商業科學的校園——作為整體來說這只是波蘭在科學方面的雄心壯志的一部分而已。
自從25年前共產主義在歐洲崩潰,變化就席卷了中歐。這種革命是快速且無法預見的。在1989年的好幾個月時間里,抗議活動在鐵幕背后膨脹開來,鐵幕是自二戰結束后出現的將共產主義中歐和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分離開來的政治障礙。然后在同年11月9日,東德政府推倒了柏林墻,星星之火迅速燎原,東德和西德人開始欣喜若狂地跨過這道障礙。一年后,東德和西德實現重新統一,并且這個區域內幾乎所有的前共產主義國家都創立了民主政府。
科研人員也分享著這份歡樂:鐵幕的落下使他們獲得了個人自由和智力自由。但是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在45年的共產主義統治中,從波羅的海到巴爾干半島的科研機構在學術上被孤立,無法和全球其他地區展開競爭。現在突然要用國際標準來對他們進行評判,他們的科學看起來已經完完全全過時了。對于很多人來說,政治變革還帶來了貧窮,因為經濟崩潰了。少的可憐的工資,科研經費的缺乏和實驗室的陳舊導致很多科學家投奔西歐或者在學術圈外謀生。而那些留下來的科研人員幾乎都依靠國外援助過活。“在鐵幕落下之后,科學研究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陷入混亂之中,”位于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的前校長利維烏·馬太(Liviu Mattei)說到,“世界上遭受這樣快速且殘酷的變革的地方為數不多。”
25年過去了,科研人員發現他們正處于一個更加穩定的科學景觀之中。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經濟滑坡基本已經結束。在過去的十年中,有些國家已經開始了明顯的經濟增長,從而使政府有能力將資金投放于科學研究之中。歐盟成員是這種變化的主要推動力。2004年,歐盟接納了八個前共產主義國家為其成員,包括波蘭、愛沙尼亞和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于2007年加入歐盟,克羅地亞也于2014年加入歐盟。現在有五分之一的歐盟公民居住于這些新加入的成員國中。
那些相對貧窮的國家獲得了歐盟注入的大量的結構性資金,這些資金旨在縮小歐盟各區域間的經濟差距和社會差距,并且有各國政府進行分配。在2007到2013年間,布魯塞爾在新加入的成員國發展方面投入了數量驚人的1700億歐元,其中超過200億歐元被指定用在科學和創新領域。大多數國家還設立了資助機構以在嚴格的競爭基礎上分配經費。“科學家們必須知道績效不是獲得資助并發表論文的唯一標準了。”位于盧布爾雅那的斯洛文尼亞研究機構(Slovenian Research Agency)的主任弗朗西斯·德姆薩(Franci Demsar)說到。“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是它極大地改善了世界上這一地區所產生的科學。”
但是在中歐和東歐內部,不同的國家在科學方面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軌跡,正如該區域內三個備受關注的國家所顯示的那樣(見圖“新歐洲的科學”)。波蘭直到近幾年才開展一定規模的研究,但是它現在已經成為了該區域的政治強國和經濟強國,并且在科學領域也在迅速地擴展。作為歐洲北部邊陲的一個小國,愛沙尼亞很早就改革了其研究體系,現在正在從中獲益。相反,匈牙利則維持著共產主義時期的一些科學優勢,但是缺乏投入正在讓這種遺產危如累卵。
這意味著當談到科學的時候,中歐和東歐國家——在共產主義時期彼此很相似——正在逐漸地分道揚鑣。此外,幾乎所有的國家仍然都在和人才向西歐流動做著斗爭。“科學方面的人才都在那里,”挪威奧斯陸大學的生理學家兼歐洲科學院前院長拉斯·沃勒(Lars Walle)說到。“現在這個區域的科研條件和科研機構需要按照新的方式來發展,即最優秀的人才發現他們留在這里是值得的。”
波蘭:追求卓越
像這個區域內的其他國家一樣,波蘭也敞開胸襟懷抱科學,弗羅茨瓦夫大學中的矮人雕刻機器就是例證。大學里到處彌漫著創建中的創業公司的氣氛。大量的實驗室空間還在建設之中,并將在2015年向科學家和企業家開放。在2014年一個下著雨的九月早晨,實驗室和會議室聚集了很多調試設備與討論科研結果的科學家。
該大學被稱為EIT+,為了呼應位于布達佩斯的歐洲創新與技術研究院(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ologg),后者是歐盟大力建設的一個研究中心網絡。就職于EIT+的科學家們在納米科技、材料科學和生物技術等學科中開展獨立研究。但是這個大學的運營像是一個有限公司,其目標是為產業提供研究和服務以賺取利潤,比如顯微鏡和晶體學。“在20年前,我們無法想象現在做的事情,”EIT+的主管兼前波蘭科技部副部長杰西·蘭格(Jerzy Langer)說到。“這里的科學家說‘不好意思,我不能做這個那個,我還沒有得到經費和設備’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科摩羅斯卡于2012年加入EIT+。她畢業于弗羅茨瓦夫,隨后離開波蘭先后赴法國和比利時進行博士后研究,并沒有打算回來。當她從這個新成立的弗羅茨瓦夫研究中心獲得一份工作邀約時,她改變了主意,該中心是EIT+的一部分。她現在領導著這個中心的納米科技實驗室以及半導體結構實驗室,在這里她研發出了一套巖石成分含量的自動分析系統,波蘭大規模的采礦業正在使用這些數據。大約3500萬茲羅提(1050萬美元)的經費被用來給這個實驗室配置最新的用來描述并觀察材料的電子顯微鏡。“在波蘭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現在我們擁有了同大多數西歐國家的科研人員一樣的設備。”科摩羅斯卡說。
當波蘭只是有一些基本的科研機構時,在共產主義時期,上述情況是不能實現的。1990年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團結工會主席萊希·瓦爾薩(Lech Warsa)接任波蘭總統并開始著手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當民主和市場經濟到來的時候,波蘭經歷了一系列痛苦的轉變——科學徹底地被動搖了。在獲取更多的有利可圖的機會中,數以萬計的科研人員開始下海經商或者到其他國家尋求科研崗位。所遺留下的是由一群越來越朝國內看的“年老體衰的”學者小心翼翼地守護的共產主義研究基地,以及在國際上關鍵科學領域上少的可憐的產出。

當波蘭于2004年加入歐盟之后,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了改觀。波蘭到目前為止是該區域內人口最稠密的歐盟成員國,它擁有3850萬居民,并且也獲得了歐盟最多的結構性經費。這筆錢有助于促進其巨大的經濟發展,自2008年以來其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大多數其他歐盟成員國了。科學已經駕上了波蘭經濟繁榮的這匹快馬,政府也已經意識到科研是未來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渠道。在過去五年里,國內投入的資金也翻了兩倍,雖然同歐洲其他國家相比科學的總體支出還相對較少,還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
在弗羅茨瓦夫之外的區域,相關的情況并非欣欣向榮。波蘭科學仍然面臨著人員短缺的情況,在整體勞動力中,每千人只有不到4人是科研工作者——這遠低于歐盟千分之七的平均水平。科學家們承認波蘭的很多科研機構——特別是由波蘭科學院主管的80個科研機構——不愿意進行改革。此外,蘭格認為,在一些大學院系中,一種來自于共產主義時期的順從(委曲求全)的精神仍在持續,并且會扼殺創造力。“很多學生都過于羞赧,”蘭格說到。“如果權威人士還沒有同意和贊同他們的意見,那么學生們就會認為這種意見還不夠好。”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波蘭國家研究和發展中心現在正運行一個項目,該項目旨在吸引那些在國外完成學業的“新科”波蘭科學家,以及引進國外的科學家,該項目為這些人提供了多達120萬茲羅提的啟動經費以供其組織獨立的研究團隊(經費到位的保證也是科摩羅斯卡被說服回國的另外一個原因)。一群年輕人才正走在投奔波蘭的路上。波蘭大學里從事科學相關專業的畢業生人數在過去的10年里也翻了兩番多,自1990年以來學生的總數也增加了四倍多。在歐盟中每十個學生就有一個是波蘭籍的。“這是最令人感到歡欣鼓舞的,”蘭格說到。
波蘭的科學家們仍然想看到更好的科學教育標準,以及更好的創新性機構,比如EIT+。“現在有足夠的經費對前景廣闊的創意予以支持,但是我們需要創造一種科學可以在其中開花結果的制度環境,”華沙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國際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學家簡納斯·布尼茨基(Janusz Bujnicki)說。“這項任務才剛剛開始。”
愛沙尼亞:小且專注
運營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人類基因庫之一的德烈斯·梅特斯巴魯(Andres Metspalu)認為他的生命40歲才剛剛開始。那是1991年,當時愛沙尼亞宣布脫離蘇聯并獨立,并且開始了邁向西方式的研究基地的坎坷之路。
在這之前,梅特斯巴魯做世界一流科學的抱負,受到了蘇維埃制度的持續破壞。蘇維埃制度承認梅特斯巴魯的天賦:他于1981年入選全蘇聯最年輕的25位年輕科學家,并且在獲得博士學位后被派往美國的實驗室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他先后在位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的耶魯大學學習生物化學)。但是他剛組成不久的家庭成員不得不居住在愛沙尼亞的塔爾圖,以便當局可以確保他不會叛逃。在回國之后,他被禁止出境,直到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掌握了蘇聯政權。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梅特斯巴魯看到了蘇聯的分崩離析。
由于只有130萬人口,愛沙尼亞認為同其他人口較多國家相比,自己更容易進行變革。上述因素,加之一些好的政治決策,使愛沙尼亞成為了該地區第一批扭轉經濟滑坡的國家之一。政府在刺激早期的商業取向的研究以及企業家精神方面也精明的多。在塔爾圖和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和科技園,已經成為令人矚目的科學研究中心。
在人類基因組于世紀之交測序完成之后,在塔爾圖大學就職的梅特斯巴魯(Metspalu)看到了科學的機遇。由于來自于歐盟結構性經費的支持,他可以發起一個招募個人向國家生物銀行捐贈他們的基因信息和健康信息的項目。在其他國家,比如冰島,采集全體公民的個人信息的類似工作是受到懷疑的。但是在愛沙尼亞這些新近獲得自由并樂觀的公眾中并不存在這種情況,很多人都樂于報名。生物銀行現在擁有全國5%成年人的基因信息和健康信息,并且這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個價值連城的國際資源,該研究需要大量公民的數據以識別與常見病相關的風險基因,包括肥胖與精神分裂癥。英國卡迪夫大學的精神病專家邁克爾·奧多諾萬(Michael O'Donovan)認為這個數據庫“非常有幫助”,他參與到了精神分裂癥的研究之中。
除生物技術之外,愛沙尼亞政府正把科研投入聚焦于諸如材料科學和信息科學這些學科上。比如,塔爾圖大學的化學院在超強酸和超堿領域十分著名,超強酸和超堿用于電動汽車電池的開發中,并且已經與幾個國家的汽車生產商開展了合作。愛沙尼亞在研發方面的投入也在持續地增加,從2002年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72%增加到2012年的2.18%——這在中歐和東歐地區位居第二,僅次于斯洛文尼亞。
愛沙尼亞迫切希望通過把生物銀行用于研究來獲得其投入的回報。2014年,愛沙尼亞政府正式宣布對一個將在接下來幾年里把生物銀行與愛沙尼亞中央健康數據庫連接起來的項目,以為醫生們根據個人基因信息診斷疾病和制定治療方案提供支撐。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這將使愛沙尼亞邁入個性化醫療的世界先行國家行列。“25年前,我難以想象還能夠對生物醫學革命做出貢獻。”梅特斯巴魯說到。
匈牙利:超越歷史
2013年,植物生物學家伊娃·康多羅斯基(Eva Kondorosi)決定打點行囊離開巴黎,帶著她獲得的歐盟研究經費回到匈牙利科學院的生物研究中心,那是她于20世紀70年代晚期開始自己研究生涯的地方。但是她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與很多中歐和東歐的科研機構不一樣的是,和共產主義時期相比匈牙利科學院反而不那么讓人感到興奮了。“它喪失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我們在這里所感受到的活力,”她如是說。
如果這聽起來有些自相矛盾的話,是因為科學在匈牙利也有點自相矛盾。在共產主義時期,科學在面臨極大困難的情況下幸存了下來。科學從大學中分離出來,并且集中于一些科研機構,而這些機構則由高度政治化的匈牙利科學院管理,且往往將執政的共產黨的密友或者成員派往關鍵的研究崗位。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匈牙利科學院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即在匈牙利南部城市塞格德建立生物研究中心以改弦更張,重新開始生物學研究,塞格德靠近匈牙利的南部邊境且遠離首都令人窒息的政治環境。這個多學科中心工作人員的任免取決于其能力而非政治地位。這個中心成為了知識分子的安全天堂,康多羅斯基在那里獲得了植物科學的博士學位。和其大多數共產主義伙伴相比,匈牙利的邊境還稍微開放一些,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科研人員可以獲得對西歐國家進行訪問和交流的許可。這確保了塞格德的科學處于前沿地位,以及科研環境的繁榮。
在共產主義瓦解之后,缺乏投入抑制了科研人員的激情,很多科學家離開了。科研經費從來沒有全面回升過。匈牙利是自2007年以來降低科研支出僅有的三個國家之一(其他兩個分別是克羅地亞和保加利亞),并且它僅把2007到2013年間歐盟結構性經費的8.5%用在了研究方面——愛沙尼亞是20%,波蘭是14%。此外,大多數結構性經費進入了公司的口袋,而不是學術界。
盡管如此,匈牙利豐富的學術遺產仍然吸引著最優秀的匈牙利科學家。同其他的前共產主義歐盟成員國相比,匈牙利有更多的科研人員——包括康多羅斯基——獲得了著名的歐洲研究委員會經費。康多羅斯基之所以回到匈牙利是因為生物研究中心這個多學科的機構給她提供了從學習植物-細菌共生關系中得到的教訓并把它們用于醫學中的機會。比如,她和其他人已經在用于固氮的植物的一些細菌中發現了抗菌活性。
匈牙利的科學文化也激發了其在國際上的信心。2012年,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在布達佩斯附近建立了一個先進數據中心。而塞格德也將成為極端光基礎設施三個節點中一個節點的所在地,這是歐盟的一個促進激光科學的合作項目。
科學家們希望科學的氛圍可以活躍起來。2014年6月,富有魅力的約瑟夫·帕林卡斯(József Pálinkás)被任命擔任一項新的職務:政府科學和創新專員。帕林卡斯以前是匈牙利科學院院長,2011年他強力地推進改革,將匈牙利科學院40個研究單位精簡為15個大型研究中心,并且加強了科研經費的競爭。在他新的工作崗位上,他將負責為政府的科學政策提供建議,并且協調當前一輪與研究相關的結構性經費的支出。他說,在本輪大約有12%的結構性經費會分配給科研。
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科學家們都把目光投向了歐盟“地平線2020”項目,該項目已于2014年啟動并將持續到2020年,其研究經費高達800億歐元。為了擴大參與面,布魯塞爾創立了一個“團隊”計劃,以讓較弱的成員國在與來自其他國家的頂尖科研機構合作的過程中成立或者升級其有競爭力的研究中心。
資金援助與組織援助在縮小國家間的差距方面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沃勒如是說。“在科學方面,有些國家總是會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能力,”他說。“但是每個國家都應該至少有一個這樣或者那樣真正強大的東西。這就是科學在美國的組織方式——這也應該是科學在歐洲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