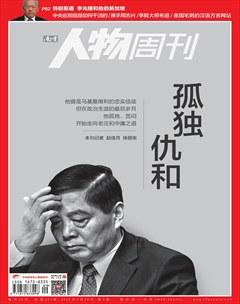一個中國官員眼中的新加坡
劉光明 張明萌

新加坡是世界金融中心,有集裝箱吞吐量排第三的碼頭,有石油基地,是亞洲旅游勝地,還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2011.03-2012.01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習公共行政與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獲公共行政與管理碩士學位
我是2011年3月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習的。當時我在廣東省物價局擔任副局長,正在研究在公共政策上借鑒新加坡的平價商店、組屋制度。能爭取到這么一個學習機會,我非常珍惜。組織上很支持,很快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學習。
求學的過程是艱辛的,重新背上書包,完成作業,參加考試;但也是愉快的,新加坡國立大學還是很有底蘊的。很快我就不僅局限于工作和專業,而是多方位地開展政策比較、深入鉆研公共治理。比較吸引我的是學校組織的講座。講座形式很生動,新加坡的部長、《聯合早報》總編、金融大鱷羅杰斯、國際政要、知名企業家、學者等等,現場交流互動,提問對話也常常擦出火花。國立大學對世界的開放性,令我印象很深刻。
我當時在武吉知馬校區,生活上主要依賴平價商店。平時走到平價商店十來分鐘,在這里買食材,享受到了平價商店的好處。微觀經濟學課程中的一個作業題是“一個社區買菜可到超市和菜攤,超市遠且貴,但現在降價了,菜攤如何改變”。這是一個開放式的題目,市場有規律,超市有規模優勢,而菜攤要賺錢,就必須生產環節直接對接銷售環節,省下流通環節的成本,平價策略就可以發揮作用。
回國后我到地方工作,推動區域里建立了平價門診,群眾很歡迎。城鎮化進程中,欠發達地區年輕勞動力去外面打工,留守老人增多,他們的看病問題愈發突出。我們在每一個街道建立平價門診,請一些醫生坐診,給老人建立醫療檔案。這樣就省去了老人因一些小毛病去大醫院排長隊的麻煩,也方便各街道長期跟蹤老人的身體狀況,效果挺好。
在獅城的一年,我感到這個國家有其獨到之處。首先以小見大。雖然新加坡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還不到我所工作的地級市的七分之一,人口也只有五百多萬,但是它的GDP近3000億美金,是世界金融中心,有集裝箱吞吐量排第三的碼頭,有石油基地,是亞洲旅游勝地,還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雖然面積小,但卻以一個國家的架構在與世界競爭,形成的是開放性的國家戰略。
同時,新加坡平中見奇。最高的武吉知馬山僅164米,這么小的島國,想法也非常務實,它的供水要依靠鄰國,但他們將水凈化后又賣回給鄰國。精英教育使這座城市的管理、工業的設計、產業發展、政府部門治理……都井然有序。這里的資源并不豐富,但勝在區位優勢,地處馬六甲海峽的關鍵位置,大力發展港口業,把大量資源聚集在那里,務實的政策贏得了發展空間。
李光耀先生一直給外界的印象就是極端務實,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總理,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脫離,他是獨立建國后的首任總理,也是人民行動黨的締造者。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迅速崛起。人民行動黨務實、廉潔的執政,不斷地提升了經濟發展層級。
對新加坡人來說,李光耀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和新加坡的政治體制結構聯系在一起的。老一輩也好,新一輩也好,共同的感受是“李光耀為這個國家做出重要表率作用和貢獻”。他有著別人無可取代的威信。他的自身規范、反腐歷程、政策制定都是國民津津樂道的典范。與此同時,人民行動黨也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新加坡的清廉是世界聞名的。他們常常講一個故事,一個部長因貪腐被調查,他打電話給李光耀求情,李光耀沒有接,部長跳樓自殺了。他們總說“新加坡不存在腐敗問題,因為即使總理也救不了你”。 他們高薪養廉,可公職人員仍然不敢開好車、不敢高消費,因為要注重公眾形象。
還有一個就是新加坡安中思危。無論是政府還是國民,都具有憂患意識。新加坡的國際化視野決定了其制定政策的前瞻性,公共政策制定時要反復思考,出現問題時成立獨立的檢討委員會進行校正。2011年恰逢新加坡大選年,人民行動黨丟掉了包括5個席位的集選區和一個單選區。當時他們也在反思對網絡輿情和一些公共政策的不足。我在和當地的群眾接觸中,也感受到社會各個層面的需求有很大的差異,不同時期的需求也有差異,如果沒有深入傾聽群眾的呼聲,就很難做好工作。到地方工作后,區內的網格化治理、干部直接聯系群眾制度,也有很好的效果。
當時我們雖然在新加坡學習,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新加坡,對世界經濟格局進行系統認識、理解和思考,這種思維意識對現在的工作很有幫助。新加坡與西方價值觀并不一樣,比如政治體制、嚴苛的鞭刑等,但是們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游刃有余。國與國策略上確實要尋求共同利益,像我國“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平臺,就在國際社會中贏得廣泛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