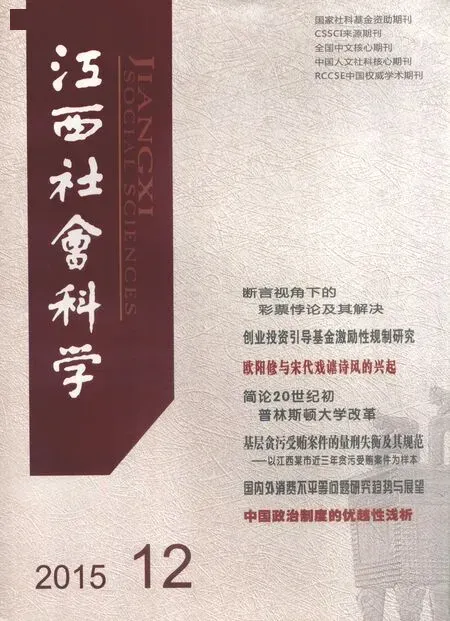論宋代御宴簪花及其禮儀價值
■楊倩麗 郭 齊
自隋唐以降從帝王到平民都產生了濃厚的愛花習俗。[1]世人不僅愛花、賞花,而且還出現了男子簪戴花朵的風俗。即便在宮廷宴會中也出現了簪花現象,如唐懿宗宴進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飲酒’,世以為榮”。[2]宋代沿襲前朝習俗,不論社會地位或性別年齡,在平時或節日都簪戴花朵,而且在宮廷中還形成了正式的御宴簪花之禮。關于宋代的御宴簪花禮儀目前學術界已有涉及,如朱瑞熙先生主編的《宋遼西夏社會生活史》對此禮有所論述,不過因為此書體例的限制沒有深入分析其中的政治內涵。[3](P369)又如韋兵先生的《星占歷法與宋代政治文化》一文中提到了南宋時期的御宴簪花現象。[4]另外,還有一些專門論述宋代簪花禮儀的文章,不過相對來說都較為籠統。總體來看,宋代的御宴簪花禮儀還有必要進行系統的研究,以凸顯當時的時代色彩。本文對宋代宮廷宴會中的簪花禮儀、御花的品種及其內涵等方面試作初步探討,不足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一、宋代宮廷宴會中的簪花禮儀
御宴簪花是宋代宮廷宴會中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現象。這里所說的“御宴簪花”是指在宮廷設宴之時,以皇帝名義賜予群臣宮花,并簪戴于頭上,以示榮寵,大臣們在宴集之時皆“公裳簪御花”。[5](P50)宋代在祭祀、節慶大典和宮廷設宴時都有簪花之禮,這些花因都是皇帝賜予的,所以稱為“御花”或者“宮花”,御花一般都插在幞頭之上,稱為“簪帶”。[6](P3569)
北宋太祖、太宗兩朝并無宮廷宴會簪花的具體記載,據此推測宋代宮廷宴會中的簪花禮儀是從宋真宗時期開始的。由于史料所限,御宴簪花具體開始的年份無法考證,不過,宋真宗景德末年御宴簪花已經頗為流行。據 《能改齋漫錄》卷十三載:
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為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后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墮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為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為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為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為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飲吃酒時。”眾皆榮之。[7](P395)
上述史料記載之事發生在宋真宗東封之前,時間應當為景德末年。曲宴之時皇帝與大臣皆戴牡丹而行,可見當時宮廷宴會當中皇帝也要簪花。按照慣例只有親王、宰臣才能得到內侍戴花,其他官員則自己戴花。陳堯叟時為樞密使本應當自己戴花,但是,宋真宗為了凸顯對其恩寵之情,特意親自為陳堯叟戴花,這對大臣來說自然是莫大的榮幸。從“令陳盡去所戴者”與“真宗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兩句可知,當時皇帝與大臣所簪之花不止一枚。由寇準侍宴之時真宗的夸贊之語,也可推知,當時御宴簪花已經成為一種時尚。
自宋真宗時期開始,御宴簪花成為普遍的現象,凡春秋大宴、圣節大宴、聞喜宴乃至曲宴都會簪花。御宴簪花最初并沒有具體儀制規定,天禧四年(1020),直集賢院祖士衡言:“大宴將更衣,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則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8](P3686)謝賜花禮儀本來是大臣在各自座位進行,祖士衡上言后,特改為在殿庭中進行,此舉顯然使謝賜花禮儀更加正式。大宴之時一般在酒行五巡之后皇帝更衣,而此時就是臣僚的戴花環節,皇帝與群臣皆簪花,再行酒四巡結束宴會,即所謂“中飲更衣,賜花有差”。[9](P3684)曲宴當中也有簪花之禮,不過一般在宴會結束后簪花。不管大宴抑或曲宴,群臣皆簪花而歸。御花是天子的恩賜,御宴人員大多以簪花為榮,不過,簪花之禮行之已久,則出現臣僚對此不重視的情形。《宋會要輯稿》禮四五《宴饗》有云:
(慶歷)七年正月十八日,侍御史知雜李柬之言:“本朝故事,錫宴推恩,赴座臣僚所賜花并戴歸私第,在于行路實竦榮觀,耀于私門,足為慶事。自景祐以來,因近上臣僚或威重自處,或輕率自便,才出殿門未及行馬,已取賜花授之左右。冬則擁裘而退,夏則頂帽而歸,自茲澆風襲成慢禮。今除執政大臣并人使遇內宴及御筵并戴花歸第,其余兩省至百寮率皆相仍輕擲賜,以為雅厚。欲乞今后凡預大宴并御筵,其所賜花并須載歸私第,不得更令仆從待于馬后,仍令御史臺糾舉違犯以問。”從之。[9](P1453-1454)
由李柬之此篇奏疏可知,宮廷宴會當中只有赴坐大臣才能得到皇帝的賜花,按照規定御花必須由大臣親自戴回家。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凸顯宮廷宴會在世人心目中的威嚴,另一方面對大臣來說也是光耀門楣之事。可是這一禮節沿襲到仁宗慶歷年間,除了執政大臣和國外使者能夠謹守不移之外,其他下層官員往往隨便將御花賜予隨從。這種做法自然是有損皇威的,因此李柬之才奏請御史臺糾察。由此事可看出,御宴簪花是朝廷樹立起威嚴的一種舉措,是宮廷宴會中重要的禮儀之一。
按照舊制,宮廷宴會中只有赴坐人員才能得到御賜之花,不過,御宴簪花之禮在宋徽宗時期得以進一步推廣。徽宗本人多才多藝,擅長詩詞歌賦,尤其鐘愛玩花弄石,在位期間大搞花石綱,對御宴簪花之禮也格外推崇。每逢重要節慶或賜宴,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及從駕侍衛皆簪花而歸。如徽宗時期在冬至過后,就命人在宣德樓下作山棚、陳拍戲,供都人游賞,又設露臺一所,“彩結欄檻,兩邊皆禁衛排立,錦袍幞頭簪賜花,執骨朵子。”[10](P165)據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歲時雜記》載,每歲正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十四日,徽宗出游觀燈時,“衛士皆戴花,鈞容、教坊樂導從”。[10](P99)正月十四日之時,徽宗攜群臣幸五岳觀迎祥池,“有對御 (謂賜群臣宴也),至晚還內”,回宮途中親從官皆“頂球頭大帽,簪花。”[9](P170)元宵節設宴所賜宮花更是倍于常時,宋人劉昌詩在追憶徽宗時期元宵節設宴時云:“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11](P77)又徽宗每次于三、四月份巡幸金明池之后,回宮時則“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前后從駕臣僚、百司儀衛,悉賜花。”[9](P199)由此看徽宗時期賜花的范圍明顯增加,特別是在外出巡游時,不僅參加宴會的大臣可以得到賜花,就連從駕侍衛皆簪花。
南宋時期御宴簪花之禮繼續流行,除上壽、圣節、錫宴、聞喜宴簪花外,“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及扈從并簪花,恭謝日亦如之。”[6](P3569)也就是說南宋沿襲北宋舊制,除宮廷宴會簪花外,其他如祭祀、節日慶典等比較隆重的場合都有簪花之禮。
二、宋代御花品種
牡丹以雍容華貴姿態立足于世人眼中,自來有富貴吉祥、國色天香等美譽,自隋、唐、五代以來,牡丹逐漸成為帝王們最喜愛的花朵。[1]宋人也尤其鐘愛牡丹,而且以牡丹的花瓣總數定其品級高低,其中以千葉牡丹最為稀有。宮廷宴會中的御花一般均用牡丹,不過因千葉牡丹比較珍貴,只有皇帝和宰臣才能夠簪之。
北宋宮廷宴會中的御花一般是人工制作的假花,不過質地和制作工藝都格外精巧。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一有云: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在庭,則內用絹帛花,蓋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也。春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為甚美麗。至凡大禮后宮謝,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藿矣。又賜臣僚燕花,率從班品髙下莫不多寡有數,至滴粉縷金花為最,則倍于常所頒,此盛朝之故事云。[5](P18)
按照宴會性質的不同,賜花品種大體有三類。圣節大宴之時賜絹帛花,由“且祖宗舊程”之句可看出,最初宮廷大宴時所賜之花均用絹帛花。后來特別是徽宗時期,朝廷逐漸趨向奢侈,絹帛花只在有遼史參加的宮廷宴會中使用,目的是為對外宣傳宋廷的節儉之風。春秋大宴所用為羅帛花,質地和制作都要比絹帛花更為精巧。曲宴即小宴所用為滴粉縷金花,概為用金絲鑲嵌而制成的御花,此種為御花當中最為珍貴的品種,所賜的數量也最多。曲宴本是小宴,參加人員一般只有皇帝及其近臣,而曲宴當中所賜御花卻是最為珍貴的。這說明當時北宋宮廷當中對外提倡節儉,實則崇尚奢華的本質,這種現象在徽宗時期表現尤為明顯。
上述三種類型的御花均為人工制作的假花,不過,北宋在舉行宮廷宴會時還會簪生花即真花。洛陽所產牡丹,自古號冠海內,到北宋時期姚黃和魏紫成為牡丹當中的極品。元豐中宋神宗曾到金明池巡幸,當時恰逢洛陽進姚黃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神宗“遂卻宮花不御,乃獨簪姚黃以歸”,之后傳為盛事。[5](P117)
南宋時期御花的品種有所改變。當時御花仍分為三品,即為:大羅花、欒枝和大絹花。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6](P3570)由御花的質地來看皆有羅、絹制成,其精致程度自然不能與北宋時期的滴粉縷金花相比。這種現象也說明御宴簪花禮儀與國家政局以及國力是密切相關的。宣政年間的奢華縱然是徽宗崇尚奢侈、腐敗所致,不過,北宋百年的穩步發展,使當時國家物資豐厚,從而為宮廷宴會的奢華提供了經濟基礎。南宋政權建立于戰亂當中,時常面臨外敵的威脅,江山尚且在風雨飄搖中,統治階層自然無暇過分追求奢侈,而因戰爭的破壞和支出,國庫物資匱乏,經濟方面的窘迫也使宮廷宴會雖有北宋時期的名頭,其實卻是相去甚遠。
三、御宴簪花之禮儀價值
首先,御宴簪花是朝廷宣揚太平盛世,體現皇恩的手段之一,這在宋元戲文中有所反映。[12](P139-147)北宋宮廷宴會當中,御花不僅制作精巧,而且尺寸頗大,大宴之時酒過五巡之后,皇帝與群臣皆簪牡丹花,群臣拜謝于庭,場面蔚為壯觀。又朝廷所賜御花必須由大臣親自戴回家,徽宗時期甚至連參加宴會的侍衛也簪戴花朵。外出巡游,宴會結束后,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和侍衛,皆衣華服,簪花而歸,其沿途風景自然相當美觀。朝廷此舉顯然是為烘托喜慶的氛圍,在官民心中制造國家無事,盡情娛樂的景象,從而達到宣揚太平盛世的目的。
又宴會中宮花都是以皇帝名義賜予的,所以稱為御花,而且朝廷特意強調謝賜花的禮儀,這樣做旨在將皇帝的恩惠夸張化。皇帝有時為了特意拉攏某位大臣,還專門在簪花禮儀上開特例。如上述宋真宗在封禪前宴請陳堯叟時,親自為其簪花。封禪乃國家大事,歷來君王封禪皆是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真宗決定封禪之始,朝中多數大臣是反對的,不過,陳堯叟卻是封禪之事的堅決擁護者,對此真宗必是對其恩寵有加。封禪前宋真宗特將陳堯叟作為東京留守,東京即指北宋都城開封,皇帝離京之時,就由東京留守來處理日常事務,故此職頗為重要。宋真宗在封禪前特意宴請陳堯叟,并且親自為其簪花,以表明皇帝對他的器重。從宴會結束后陳堯叟的反映看,真宗此舉著實達到了收買人心的效果。又宋真宗還非常看重翰林學士一職,經常通過簪花禮儀體現朝廷對此職的重視。天禧初,晁迥時為翰林學士,一次在宜春殿曲宴,“出牡丹百余盤,千葉者才十余朵”,本來只有親王、宰臣才可得到千葉牡丹,真宗特賜給晁迥和錢文僖各一朵。還有一次侍宴時,真宗賜晁迥禁中名花,真宗為表示對晁迥的禮遇之情,特命內侍為其簪花,觀者榮之。[13](P2)可見,御宴簪花禮儀也是皇帝借以播撒皇恩,拉攏大臣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次,御宴簪花雖是喜慶與榮耀之事,不過此事發生在君主專制社會,其中貫穿著嚴格的等級觀念。宴會中簪花的具體禮儀以及所賜御花的品種和數量都顯示著濃厚的等級色彩。在舉行簪花禮儀時,只有皇帝、親王和宰臣能夠享受內侍簪戴的殊榮,一般的臣子只能自己簪花。御花當中較為珍貴的品種如千葉牡丹等也只有皇帝、親王、宰臣及個別寵臣能夠簪戴。簪花的具體數量多寡有差,官職越高簪戴御花的數量也越多。
到南宋時期御宴簪花的等級觀念更加濃厚,當時宴會的排場乃至御花的制作工藝都落后于北宋,不過等級觀念卻比北宋更進一步。南宋宮廷宴會中唯獨皇帝不簪花,只有參宴大臣簪花,此舉旨在凸顯皇帝九五之尊的身份,特意將皇帝和大臣區別開來。又御宴人員因身份的不同,所簪之花也有欒枝和絹花的差別。紹興十三年(1143),高宗恢復了圣節上壽、大宴儀制,并制定大宴儀節,其中明確規定了大宴中百官簪花的數量,簪花最多者為親王和宰臣,即大花一十八朵、欒枝十朵,以下官員按照品級逐步遞減,品級最低者僅簪大花兩朵。同時規定,宰臣以下至百官并系羅花,禁衛、諸色祗應人并系絹花。[4]御宴簪花之禮興起并流行于等級嚴格的君主專制社會,必然難以擺脫時代的烙印,而且隨著君主專制的加強,這種時代烙印愈加明顯。
再次,御宴簪花的盛行,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內心對美的訴求。宮廷宴會中的簪花現象在唐代就已有,不過僅是偶爾為之,直到北宋時期御宴簪花才流行起來,成為時尚。南宋沿襲北宋儀制,御宴簪花禮儀繼續流行,南宋之后宮廷宴會當中則再無簪花之禮。中國古代君主專制社會共存在兩千余年,而御宴簪花之禮何以單在宋代盛行,其中的緣由還是值得探索的。
北宋歷代皇帝都不同程度地提倡文治,特別是在太宗即位之后,朝廷大肆擴大科舉名額,錄用人數動輒上千人。其結果是朝廷乃至全國各地匯聚了一大批熱愛吟詩作畫、賞花游玩的士大夫。這批士大夫皆生活清閑,同時追求情調,因此有大量的時間愛花、賞花、簪花,用花卉陶冶情操,進而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詠花之作。蘇軾《吉祥寺賞牡丹》中就有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14](P655)表現了詩人不顧世人眼光,樂觀豁達的性格。又邵雍《插花吟》中有云:“頭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15]作此詩時邵雍已年過花甲,但仍以簪花、飲酒為樂,表現出詩人在太平盛世中悠然自得的樂觀心態。宋人的詩作當中也有不少直接反應御宴簪花情景的,如楊萬里在《正月五日以送伴借官侍宴集英殿十口號》中有云:“廣場妙戲斗程材,才得天顏一笑開。角抵罷時還罷宴,卷班出殿戴花回。”[16]南宋時描寫御宴簪花盛景的詩作更是不乏其數,姜夔有關于宮廷宴會結束后群臣簪花而歸的詩,其中曰:
六軍文武浩如云,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萬數簪花滿御街,圣人先自景靈回。
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見紅云冉冉來。[17](P22)
姜夔此詩題為《郊祀后景靈宮恭謝紀事》,所述之事為淳熙三年(1176)宋孝宗于冬至行南郊禮畢,赴景靈宮致謝,進而賜宴百官,簪花而歸的盛景,詩中盡顯詩人對簪花的崇尚與愛慕之情。宋代的士大夫或借簪花寄托自己高潔的品格,表現怡然自得的樂觀心態,或者是以御宴簪花為殊榮,此中皆包含著他們高尚的情操與對美好事物的訴求。御宴簪花之禮在北宋的興起與當時的文官政治密切相關,以皇帝為首的宋代士大夫對于簪花的熱愛,直接推動了此禮在兩宋時期的盛行。
南宋以后的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對于男子簪花現象自然難以接受,明清時期文官政治雖有所恢復,但是御宴簪花之禮早已淡出歷史的視野。也就是說御宴簪花是兩宋時期宮廷宴會當中特有的禮儀。
[1]魏露苓,蘿莉.唐五代的愛花風習與花卉產銷管窺[J].廣西社會科學,2004,(7).
[2](明)彭大冀.山堂肆考[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3]朱瑞熙.宋遼西夏社會生活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4]韋兵.星占歷法與宋代政治文化[D].成都:四川大學,2006.
[5](宋)蔡絳.鐵圍山叢談[M].馮惠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6](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7.
[7](宋)吳曾.能改齋漫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清)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7.
[9](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0](宋)陳元靚.歲時廣記[A].叢書集成初編[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11](宋)劉昌詩.蘆蒲筆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2]駱婧.再議“潮泉腔”與宋元戲文的傳播——從饒宗頤、龍彼得戲文研究說起[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
[13](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4]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蘇軾詩集校注[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5](宋)邵雍.擊壤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16](宋)吳之振.宋詩鈔[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17](宋)周密.武林舊事[M].李小龍,趙銳,評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