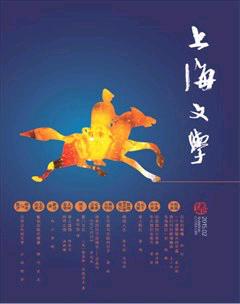新年的氣球
陳文芬 馬悅然
一百年前常務秘書維爾森的圣歌
2015年新年看電視,美國導演提姆·波頓的《艾麗斯夢游仙境》,錢寧戴普飾演制帽匠,他的表演技巧真好。電影早在戲院看過,只想隨意看看,忽然瞥見少女艾麗斯見了紅、白王后以后,扮起挽救城堡的大英雄,身穿盔甲持劍拿盾,登上高山,大戰屠龍。這一幕原著的英國數學家劉易斯先生沒寫,故事由編導續寫加柴添料,電影的艾麗斯不是兒童,而是已有婚約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少女,她一頭栗子色飄逸長發,斯文秀麗的面部表情,像極了斯德哥爾摩老城大教堂的圣悅然木雕彩繪座騎像,這雕像自中古以來成為瑞典人的國家浪漫主義的象征。大教堂是瑞典王國的宗廟,就在瑞典學院(諾貝爾博物館)的旁邊。這座木雕圣像有一種樸實寧靜的神情,瑞典語的名字悅然G?觟ran與英語的喬治George是同一個字。歐洲傳說圣徒喬治拯救的是一座城市或一名處女。把艾麗斯扮演做圣徒喬治與龍的比擬,是導演頗具靈性的神來之筆,處女挽救了城堡,成為基督信仰傳奇的外一章故事,塑造女性主義版本艾麗斯的新形象。
很少有人知道圣徒喬治的生活背景,只知他出生于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亞。他在羅馬皇帝戴克里先軍隊擔任軍官,以虔誠的信徒教養影響朝廷對信仰的看法。過了不多久皇帝壓制異教徒,殺了許多信徒,喬治最終遭受死難,寧死不屈的表現傳聞連皇后也佩服他的勇氣,愿意信基督。喬治的故事后來跟一則阿拉伯民間傳說連起來,在利比亞的一個城市有一條大龍占據了水源,每天居民來挑水得獻上兩匹綿羊,沒有牲口就得送人,居民互相抽簽抽到公主,國王束手無策,忽然出現一名勇士喬治身穿戰甲持劍騎馬與龍搏斗殺死了龍,解救了城市與公主。喬治屠龍的浪漫傳說在整個歐洲、俄羅斯廣泛成為文明底蘊的象征,所有的城市建筑文化、匠人的藝術、書籍印刷文獻充滿喬治斗龍的形象。英國王室尤其喜愛喬治的名字,喬治的名字日四月二十三日是公眾的節日。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地區在喬治日那一天,女人送男人一本書,男人送女人一枝玫瑰花,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此一傳統獲得靈感,指定四月二十三日為“世界讀書日”。
每當瑞典王儲大婚在大教堂贊詠吟唱一首維爾森(Carl David af Wirsen,1884—1912)寫的圣歌《華美綠意的衣衫》,這可能是現代瑞典文化最為愉悅神圣的時刻。一般瑞典人已經不大信教,宗教也非生活的主要依據,可是這首圣歌的音調輕柔和緩,曲調莊嚴宜人,描述風景悠閑豐美。歌詞頭一段描敘夏日風景,旋律容易記住,后段詮釋宗教的意涵比較深邃,今人有時略去不唱。演唱這首詩歌時,圣悅然木雕像與他的坐騎寶馬寧靜神思的神情就不斷出現在電視上。
華美綠意的衣衫
蔥綠的草木美麗的衣著
裝飾了山谷和草原。
現在溫暖的清風撫摸著
優美的花床。
太陽的光,
樹林的颾聲
與河水楊柳中的潺潺
預示夏天的來臨。
維爾森1901至1912年當了十二年的瑞典學院常務秘書,他開啟了瑞典學院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機構的時代。1896年火藥發明家諾貝爾的遺囑希望瑞典學院承擔文學獎評獎任務,大部分的瑞典學院院士缺乏意愿,有兩位院士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反對的兩點理由:認為十八個人的能力不足夠做這件事,他們還擔心一評選諾獎,人們不會重視他們歷來對文學語言的愛好跟研究任務,只記得他們是一種帶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學判官。維爾森使出了所有的力量說服院士們承擔諾獎責任。“要是退回諾貝爾已捐贈的每年有六萬克朗的文學獎獎金,等于剝奪了給歐陸的文學大師們享有榮譽跟利益的機會,現在與后世的瑞典學院都會遭受貪圖安逸的罵名。”
維爾森出身貴族,父親是階級很高的軍官。他研究法國17、18世紀的文學,在烏普色拉大學當文學副教授,在高中教過拉丁文跟瑞典文。瑞典學院里最大的敵人曾形容他還是他們當中讀書最多的人,一個勤奮用功的學者。維爾森還擔任諾貝爾文學獎小組的主席十年,常常為推薦提名的作家寫長篇報告。維爾森篤信宗教,他對諾貝爾遺囑“具有理想主義傾向”解釋為“高尚和純潔的理想”,這也差不多成為諾貝爾文學獎頭十年頒獎評選的主旋律。維爾森在瑞典學院的報紙《內政與郵政公報》和著名的刊物《吾國》寫文學評論,他批評斯特林堡、易卜生、拉格洛夫跟托爾斯泰的著作,換言之,當時最應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師都受過他的批評。
諾貝爾文學獎頒發頭一年1901年,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沒有得獎,引來軒然大波。瑞典有四十二名作家、藝術家、書評家為此發表公開的抗議信,第二年托爾斯泰以公開信作答,感謝瑞典學院沒有頒獎給他,避免他自己為了巨額的獎金感到困擾。
托爾斯泰一直視金錢如無物,感謝信寫得語言懇切,十分誠摯。回顧維爾森書寫的諾獎小組報告,他對托爾斯泰的評價:《戰爭與和平》是敘事的著作、很重要的史詩作品,托爾斯泰最重要的著作實屬《安娜·卡列尼娜》,但他批評著作《黑暗的權利》有一種敵視文化進步的態度,他也批評托爾斯泰對國家的態度。
維爾森有時展露“獨裁者”表里不一的手段,他不喜歡猶太人,當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歷史學家、文學家)亨利克·畬克由院士們投票入選學院院士,維爾森給國王打報告,第二天國王召見學院的一名院士到王宮,告知否決畬克選進學院,這是唯一的一次國王召見常務秘書以外的院士到王宮。院士們在一個罐子里投小球,同意票投白球,否決票投黑球,表決只有一顆黑球,大家知道黑球是誰的。維爾森不喜歡畬克,我們不急著把維爾森劃進現在的極右派“種族歧視”那種概念,那時候瑞典公民社會的意識還沒興起,瑞典女人1921年才有公民投票權。2014年秋天大選剛落幕,瑞典議會還鬧過某議員說猶太人不算瑞典人的話語,一時喧騰起來,事后那位議員矢口否認他這樣說過。歷史的發展也很奇妙,維爾森辭世以后,畬克不只選進了院士,還成為諾貝爾獎小組的主席。
幾年前我在國立美術館看過19世紀報刊新聞漫畫展覽,其中有一幅畫諷刺的新聞主人翁就是維爾森,畫上有許多大文豪跟批評家各自拿了不同的可笑的武器,揮劍一般舉向維爾森,其中有嘴角兩撇胡須的斯特林堡,更有長發高綰的女作家拉格洛芙,不知是誰用一支鋼筆做成的劍刺中了維爾森的心臟,不過,維爾森就好像一個永遠不會倒的大力神翁,神情莊嚴肅穆,對眼前的混亂不為所動。我雖然不能記住漫畫是哪一年的,但肯定是1909年拉格洛芙得獎以前。
拉格洛芙最終如何能在維爾森的法眼底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擺脫托爾斯泰、易卜生、斯特林堡的命運?1903、1904年還有人推薦托爾斯泰,1905年拉格洛芙上了推薦名單,1907年兩名瑞典學院院士、隆德大學教授推薦她。1908年推薦名單十六人,她在第五個(順序可能按推薦書收信時間記錄)。兩個學院院士、哥德堡大學、芬蘭學者推薦,小組報告是維爾森給一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寫的一篇好長的報告——維爾森會使勁兒給一個他希望得獎的作家寫報告,也確實寫得好。1909年二十一個人獲得推薦,許多人推薦拉格洛芙。1909年的小組還是五個人,維爾森寫報告總結:“雖然只有兩個院士支持她……”他談到:“推薦最強力的支持來自瓦博教授(院士),不能相信他講的話。拉格洛芙比過去八個得獎的作家都好,這是不能相信的。”(引述自悅然查閱瑞典學院已出版的諾獎記錄書籍)
這是不能相信的,但成為事實,1909年拉格洛芙成為首位獲得諾獎的女作家、首位獲諾獎的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大史詩小說《古斯泰·貝林的故事》描述她的家鄉韋姆爾蘭農莊許多鄉野之間不平凡的人物,這是一部魔幻寫實主義小說。華人談到2012年諾獎得主莫言作品時,常會拿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小說來比較,瑞典學院院士提到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寫實主義小說跟莫言寫作的背景與心態,有些可相比擬之處,但來自中國自身傳統文化《聊齋》才是作者“幻覺寫實主義”美學的根源。瑞典文學家常常提到,從莫言作品看很像是拉格洛芙《古斯泰·貝林》那種深刻于莊園鄉野的傳奇敘事的大力量。
思想史與學術史專家雷登(Per Ryden)2010年在瑞典學院的小天井舉辦新書發表會,他撰寫常務秘書維爾森的評傳《成功的失敗者》,七百頁的巨著描述維爾森將瑞典學院推向諾獎這條卓越的歷史航線的過程。維爾森的唯心論觀點,致使諾獎與托爾斯泰等幾位大師失之交臂。瑞典學院在20世紀上半葉的選擇受到的批評較多,戰爭以后急起直追,1945年以后赫塞、紀德、艾略特、福克納、馬爾克斯等許多得主都有新文學里程碑的意義。雷登認為要不是維爾森一個人打定了主意,堅持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理想,以當時學院的情勢,肯定把獎推向門外。維爾森開啟了諾獎的關鍵之鎖,奠定百年的基業,蓋棺論定以“成功的失敗者”來描述維爾森的時代,成功與失敗各半,即使文學觀點敗陣,輝煌的那一面也不可勾銷,應該表揚。這一天悅然跟我參加了雷登的發表會,雷登結語說,“我聽說這兩年瑞典學院開會時,有人主張院會結束時,所有的院士合唱維爾森的歌《華美綠意的衣衫》,成為學院新的禮儀與傳統。”雷登為現在的院士們對維爾森的評價有所改變感到欣慰。
提議唱歌的那位輪值院長這時望著我微笑。喜歡《華美綠意的衣衫》的院士不只有悅然。當時的常務秘書賀拉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1948年生,1997年選入瑞典學院,1999—2009年擔任常務秘書)也十分欣賞這首歌,他說,“一個人能寫出這么好聽的歌,也值得原諒。”
前任常務秘書恩達爾的歌《新年的氣球》
恩達爾2014年秋天第一次到中國南京訪問學界,我讀到中國媒體幾篇精彩的訪談。私以為恩達爾可能是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常務秘書,他擅長文化批評,面對爭議的媒體議題,恩達爾不僅樂于面對,三言兩語就說得層層在理,也常以幽默的比喻吹破媒體表象的牛皮。他在中國回答村上春樹年年成為諾獎熱門人選:“他是否得獎一直是個虛假的新聞議題,那是賭局的猜測,無關乎討論文學。我們希望制止博彩賭諾獎,可惜我們無此權利。媒體猜測各種人選名單也都自陷于這種虛假議題的陷阱……根據諾獎評選的要求,我不能告訴你名單上有哪些作家,不過我在賭局名單上看到了那位作家。”
恩達爾會五種語言,瑞典語以外,俄語、法語、德語、英語都極流利,他宣讀得主時五種語言都派上用場。恩達爾做18世紀浪漫主義的文學研究與批評,外界有時以為他是一個新派的文學理論家,這可能跟他涉獵的文化范圍太廣泛有關。這里不談他對文學的看法,介紹他對大眾文化更為廣泛的影響,比如一篇微型散文《夢》,以及他獲得歌唱大獎的一首歌。
收錄在散文集《流星》的《夢》篇幅短短,由一群年輕動畫藝術家繪成藝術動畫影片,我在電視上看過這則影片,非常感興趣。動畫描繪恩達爾的真人形象,他的身形高大,一天早晨在臥榻夢醒之時沒有戴上他那副著名的橢圓框眼鏡,眼睛睜得大大,倒有幾分卡夫卡小說主人翁起床的氣氛,夢里夢外這人的思想產生了變化。瑞典學院初夏莊園晚宴跟恩達爾坐在一起吃飯,我問起來,他告訴我這是一個真正的夢,他非常享受夢里他得到那么大的自由,完全解脫了外界給予他的責任感,他的夢境散文跟我寫微型小說有一系列從真實的夢而來有些相像之處,他的散文體又多了一份意在言外的開闊感。花園開滿丁香花,夏天的黃昏晚來,九點多鐘彩霞滿天,我跟恩達爾對窗而坐,斯德哥爾摩城市派拉蒙式長幅條三百六十度的海港景象就在眼前,彩霞絢爛的天邊忽然飄來一只紅艷艷的熱氣球,慢慢由西邊飄到東邊。回家以后我翻譯《常務秘書的夢》寄給臺灣報紙:
“我夢見我瘋了。我正要到一個城市參加一個宴會,我甚至相信那個宴會就在我家。我到的時候,宴會已經開始好一陣子。衣帽間掛滿衣服跟鞋子,一堆一堆的,像我以前南區的家。老遠聽到房子里頭的人們好熱切的談話聲。我知道那些人我認得,都是很可愛的不會傷害我的人,可我沒法叫自己走進去。我站在半開的門外,感覺我全然確信不可能進去跟他們談話,再也不能夠。我沉默地走下樓梯走上街。街上空空的,早晨五點鐘。我開始走在19世紀成排的樓房之間,察覺到某種轉變。一種瘋狂的進駐,把我解放開來免于談論的責任,我不再懂得一間‘房子是甚么,一天‘早晨或者一條‘狗是甚么。一道光線落下來,鉻黃色的,那斜斜落下來的光輝,又可怕又美麗,屬于另外一個世界。我起初感覺到我瘋了的驚嚇,變成一種上升到天空之底部的安靜。我慢慢走下人行道的斜坡,一點都不慌忙,心中充滿極樂的感覺,就像初次接吻那么幸福。”
恩達爾在2009年做滿十年的常務秘書,由歷史學家彼得·英格倫接任。恩達爾卸任以后曾隨妻子到柏林居住一年,在咖啡店寫出一本散文集《以后,來一支煙》,立即成為暢銷書。恩達爾的妻子艾芭(Ebba Witt-Brattstr?觟m)是一個名氣很大的女性主義者、文學評論家,兩人做了二十五年的夫妻,常一起出席各種文化活動,2014年離婚。同年春天瑞典電視臺策劃一個節目,邀請十位文化界名人寫歌,恩達爾作詞的《新年的氣球》獲得首獎,歌詞優雅美麗,傳唱動人。相隔一百年以后,又有瑞典學院的常務秘書寫作大眾喜愛的歌。
新年的氣球
傳來新年
鐘聲的半夜,
我們把愿望
放進這紙做的許愿燈。
許愿燈的微弱的光輝
望天空上升時
我感覺得非常自由:
所有的成就都毀壞了。
我的心一碎了
立刻就輕松了,
帶著我的愿望
樂意地上升、
像個熱氣球。
離開地球,故鄉和家園,
像個光點逍遙。
我得跟隨風向笑聲笑。
離開我幸福的世界,
信任許愿燈的旅程,
因為什么都丟失之后
天空和黑夜就敞開了。
沒有目的的旅客
此刻會碰巧了,
因為那小小的許愿燈
飛往無所在之處。
會上升么
或者下降?好緊張!
那愿望的重量
發愿望的人還稱不了。
好!許愿燈上升了!
此地沒有什么
能把它留著,
沒有問題,沒有回答,
只有沉默……
我悲哀中所寫而
放進許愿燈里的愿望
消失如水蒸發了。
離開我幸福的世界,
信任許愿燈的旅程,
因為什么都丟失之后
天空和黑夜都敞開了。
(馬悅然譯)
兩百年來的第一位女性常務秘書
莎拉·丹紐爾(Sara Danius)2013年12月20日在瑞典學院年會宣誓就任院士,從2014年新年坐上瑞典學院第七把椅子,巧合的是一百年前的1914年拉格洛芙成為瑞典學院的第一位女院士,也是第七把椅子,先得諾獎再選入院士,人們說拉格洛芙是“幸運七號”。丹紐爾的身材挺高,幾乎跟賀拉斯·恩達爾一般高,2014年12月20日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彼得·英格倫宣布卸任,院士們選出的接任者是剛做滿院士一年的丹紐爾。英格倫于2009年上任時聲明僅做五年。丹紐爾成為瑞典學院第一位女性常務秘書。
丹紐爾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文學教授,《每日新聞報》的書評家。她研究的文化批評議題往往以小見大,觀察入微。去年秋天她最新出版的一本書《龍蝦之死》,悅然隨身攜帶于飛回臺灣講學途中閱讀,不時發出贊美之聲。封面很吸引人,兩只有如芭蕾舞姿態的手腕,一只按住龍蝦,另一只垂握住一把尖刀刺向龍蝦的眉心。書名來自其中一篇散文《家庭主婦的死亡》。
她說,文化批評的方法再簡單不過,把1960年跟2010年瑞典最大的潑尼爾出版社出版的兩本食譜拿來做比較,就知道什么是文化批評;當然也可以把1983年跟2002年做個較量,不過這樣太嚴肅了,挺像歷史學家,我們倒不想做歷史學家而想做文化批評家,別只顧著計算碗底的飯粒,我們應該數一數天上的星星。所謂的“自然知識與文化”,在烹調這一方面可以直接指出屬于文化的領域。廚房有沒有“性”這回事?有的,至少有男女之分。歌劇院地窖餐館的大主廚是寫食譜的名家,他為家庭婦女寫食譜先教女人怎么洗爐子,可用肥皂跟水,千萬別用干粉的洗劑,那會損害了爐子。丹紐爾挖苦這些男廚教婦女做些簡單的活兒,接下來,卻教極端復雜的殺生烹調法,如何在廚房殺一尾形似長蛇的黃鱔魚。需要的工具有橡膠手套、榔頭一把、木槌、釘子兩三只、快刀一把。剝除鱔魚皮的步驟,在墻上敲進釘子固定住,像把衣服掛進釘子,一手握緊固定好墻上的魚,快刀切撕開魚皮,夾起、挑皮,然后迅速撕開皮面扯下來,完整剝除鱔魚皮。書上重現食譜剝皮圖解步驟,可以想見婦女的圍裙沾滿了魚皮的黏液跟血滴。再比如殺一只龍蝦得趁它活蹦亂跳時,舉刀正面刺準了眉心,龍蝦方才切得齊整,蝦膏形狀油亮美麗,鮮味欲滴。剝一只兔子皮的方法是倒吊在墻上掛好,用尖刀起子從兔腿兩手往下緊拉剝剔下皮來,書上附有早年的食譜剝兔皮、殺蝦、剔魚皮的相片。
悅然讀完文章想起自己的媽媽,所幸爸爸從不讓媽媽做這樣的事情。圣誕夜我們一大家人與姻親團聚吃飯,老二媳婦卡琳的媽媽芭玻今年也有八十五歲了,她聽完《龍蝦之死》就說她的丈夫要求她殺一條鱔魚剝除魚皮,她拒絕。丈夫說:“可是我媽媽就是這樣做的。”卡琳的父親原籍挪威,挪威的家庭主婦萬應皆備,德國波蘭的婦女也相同,記得讀過德國留學生的文章,半夜在寄宿的家庭醒來打開冰箱,一只剝過皮的大兔子正貼站在冰箱里。奇怪的是,使用潑尼爾版本食譜的家庭婦女都是中產階級,芭玻的丈夫是個名醫,大可雇個阿姨長工做事,不像現在勞工也得繳百分之五十的稅金,薪資很高,除非是特別闊綽,一般中產階級誰也請不起一個每天來做飯的阿姨。為什么連醫生也認為剝鱔魚皮是家庭主婦的責任?悅然很快就證實這一點,像他的爸爸是一個中學老師,即使薪水微薄,家里一年兩季請人來煮沸大盆蘇打水洗衣服曬床單,廚房里做菜烹調“有文化”的活兒還是家庭主婦的責任,傭人不做廚房的文化,他們有自己家里的事要做。灌香腸、腌咸魚,樣樣都是媽媽自己做。曾聽悅然說起媽媽的溜冰技術絕佳,冬天兩只手交疊袖進皮袖筒,從不拿出來。男女冰鞋有別,男鞋鞋頭尖形,可像松鼠輕跳冰地前行,女鞋鞋頭圓形,只能不停滑前移動,身形款款,隨袖筒交疊的手臂橫向平衡支點,左右滑動前行。要這樣優雅的一雙手殺生是不能想像的。兩相比對六十年后的食譜書籍,廚房的屠殺技藝終止了,丹紐爾寫著:“‘家庭婦女(的精神)死亡了。”
莎拉·丹紐爾成為古斯塔夫國王三世1786年創建瑞典學院以來的第一位女性常務秘書。2015年10月第二周的星期四下午一點整,她將推開那道門宣讀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世界將會注目這一刻。我不會忘記她介紹剝魚皮的方法,就像我不會忘記艾麗斯代替圣喬治殺了一條大龍。而人們依然喜愛圍在大教堂圣悅然的木雕像前唱頌那首旋律優美的圣歌,甚或在新年想望一只有如夏天飄來的熱氣球,都使人感覺無比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