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堂散記(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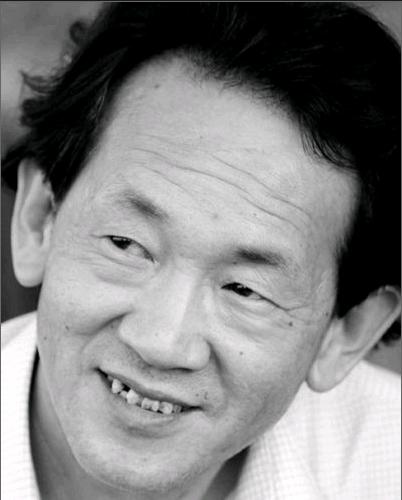
002
讀鐘嶸的《詩品》,對一段話感受頗深:“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映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籍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竊以為,此乃全書立論之基石也。
? 詩,一定要有“氣”。
?我對一首詩的判斷,首先看其是否氣韻貫通,氣勢靈動;然后再看其“氣”之落腳處以及方向,至于溫婉或磅礴則屬詩人個體特征。
“氣”是詩人外化的情感,“氣”要動,動才是創造。詩人“氣”動,才能讓天地、鬼神動。當然,“氣”與“動”要匹配得當,就是敘事與抒情的平衡,是詞語在表達現場隱身而彰顯趣味與意味。
?外表的建筑無論多美,沒有內在的詩人自己的感情貫穿,也是豆腐渣工程。
009
天氣悶熱,心情也煩悶,很想找個通道釋放。酒不敢喝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我就鼓動自己寫詩,要表現什么沒想好,憑著語文經驗就一行一行地寫了。寫完我發給一個朋友,問:此詩如何?朋友回了兩個字:“裝怪。”我猛地覺得這兩個字恰切。沒籌劃好要表現什么,卻要用一行一行的文字當詩,這是裝,裝腔作勢的裝。前言不搭后語,意象、具象紛亂,這是怪,怪模怪樣的怪。
此詩改過三次,最終被扔進廢紙簍里。“詩改三遍始心安”,是指本質上是詩的文字。用烹制紅燒肉的方法烹制土豆,無論外表和味道怎樣接近紅燒肉,根本上還是裝怪。
011
魏晉時期多文人閑士,但有骨氣的不多。名貫天下的曹植,不過是用八斗之才作了一首“七步詩”,救了自己一條小命,讓詩歌的社會功能發揮到了極致。當然,我絕不相信那首“七步詩”是現場即興所作,他怕被“煎”的情緒已經醞釀好幾年了。
我很欣賞晉代的陸機,他在面對死亡時的從容、淡定,顯示出了文人的風骨。司馬穎要殺陸機,便寫一紙密令給牽秀,牽秀率兵到了陸機的營中,陸機知道是來殺他的:“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臨死之前,首先把軍裝脫了,換上文人的服飾,要以一個文人的身份去死。這既是對司馬氏的嘲諷,也給天下文人樹立了榜樣。
《晉書·陸機傳》這樣評價陸機的換裝:“白帢乃清簡之物,陸機著白帢,是以明志,表明自己一身清正,一片冰心。”
曹丕不殺曹植,絕不是因為那首“七步詩”,有幾個政治家會被一首詩感動?曹丕是覺得文人都是軟骨頭,成不了大事。
012
第二遍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時,就像洗澡一樣,把身體上角落旮旯里的污垢找出來,搓掉,很是神清氣爽。這樣說,可能有些大不敬。
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貢獻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被奉為經典是實至名歸的。但是,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一定要警惕,儒家思想里的等級秩序、倫理道德等禮教,都是讓人墨守成規、亦步亦趨的,是在壓制人的想象力。想象力受壓,創造力必匱乏。
由是,我想到了我國現當代的小說,有的淪為政治工具,有的一心要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評判準繩,有的只是輕淺地娛樂大眾。近些年,又大有成為賺錢機器的趨勢。我姑妄言:現當代中國的小說對中國文學的發展貢獻實在是有限。當然,我也不能說,現當代小說家讀《四書五經》讀的沒有了想象力。
相對地說,詩人的想象力很難受到限制(混在詩人隊伍里的偽詩人除外),除了詩人先天的無羈性格外,真正的詩歌很少成為“載道”的工具。
《四書五經》一定要讀,也一定要搓掉它的泥巴。
013
到某地出差,想起當地一老朋友多年未見、也無音信,便問身邊當地的友人:“某某近來怎樣啊?”
友人說:“這哥們幾年不出門,電話也很少接,什么活動也不參加。我們幾個約他出來喝茶、曬太陽,他都不出來,說是在家寫東西。”
聽罷,我就給那個朋友打了一個電話。半晌,他接了。我說:“我是商震,昨天來的,你要不要出來見一下。”
他猶豫了一會兒:“我這些年也沒寫出啥好東西,有點羞于見人。這次我就不出去了,下次吧。”
我接著說:“你小子天天悶在家里,連太陽都不曬,小心身上長蘑菇。”
他笑了,身旁的友人也笑了。
幾年不出門,就是幾年不沾人間煙火氣,能寫出好東西嗎?我懷疑。悶在家里寫詩,可能會寫出莊嚴的道德立場,不會寫出鮮活的生活現場。詩歌離開了鮮活,就只剩僵滯的文字了。
014
又有幾個寫詩的朋友練毛筆字,并寄來給我看,我真是欣喜過望。
用毛筆寫字原本就是詩人的基本能力,就像吃飯要會使筷子一樣。時代的發展,使社會分工過快,詩人僅會寫詩,用毛筆寫字的成了書法家。
古時,所謂“才子”,一定是詩人,而詩人必備的幾樣功夫是:刃、酒、琴、棋、詩、書、畫。現在這七項,已經是七種職業了(也造就了這七種“產業工人”)。這七項,現在的詩人會幾項?我覺得,未必都樣樣操作,但樣樣了解是應該的,了解、認識這些是借力,借力意在得巧,而非使用。
唉,我常譏諷好為人師的人,這不,我就好為人師啦。人的弱點之一,就是評判別人容易評判自己難。
文房四寶中,詩人最像筆,毛筆的特點是:尖、圓、齊、健。這四項內容矛盾著也協作著,有對立但不可分。筆之心,當有萬般風云。
好的筆,腰的彈性要好,要健,只對紙墨鞠躬。腰挺住,筆鋒就能立住。筆鋒立,墨就實,氣就貫。字好不好看,是后人去說的事。
這不是詩人嗎?
016
讀一篇閑文,《世說新語》載:“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曬書。”此郝隆君雖有賣弄炫耀之嫌,但也足夠引起我羨慕嫉妒恨了。
我也算讀書人,家中藏書亦是幾千冊。但與郝隆比,真實羞愧難當。我的書一部分是工具書,一部分是“學以致用”的書,一部分是買來擺在書架上裝潢的,或者告訴自己這本書我有了,有而已。我肚里那點為了用而讀的書,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出肚皮曬嗎?盡管我很瘦,露出來的贅肉也肯定比書多。
讀書如吃飯,有人長贅肉,有人長力量。我是兩樣都不多,空費了許多糧食。
一位老師告訴我:讀十萬字可寫一萬字。我試過,不靈。后讀百萬字寫一萬字,方有幾分自信。
020
祖上有遺訓:“半部《論語》治天下。”
想“治天下”的人讀“半部”就夠了,像我這樣只讀字詞句章的人,把整部《論語》讀完了,也沒看出“治天下”的道道兒來。孔夫子說了很多“治國齊家平天下”的道理,卻對文學創作說得不多。那么,是不是在“治國平天下”這件事兒上文學創作并不重要呢?
如果這樣認定,似乎對孔老師有失公允,他老人家雖然對文學方面說得不多,但說起來也是一句頂一萬句的。比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多精辟,多確定。后世無人批《詩經》,再批就是反孔圣人,反“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思想。孔老師說得最好的關于文學創作的話,是下面這一句:“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這句話對文學創作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應該是“文質彬彬”。現在,很多人寫文章是“文勝質”,生活不真實,情感不真切,卻能寫得絢爛、宏大,像一件豪華、昂貴的服裝穿在稻草人身上。
孔老師要求寫文章要像做君子,表里如一,內外和諧。兩千多年了,其難甚矣。
024
到“魯院”給幾個青年詩人開研討會,說實話,這幾個詩人的作品還真是當下優秀之作。但我一開口就說:“我是來挑毛病的。”接著,就一個一個地批評過去,估計這幾位聽了都不太高興。
研討會嘛,就是要說“好。真好。確實好。”而我生來就不會偽抒情。我的職業是編輯,編輯就是從桌上的一大堆稿子里,把有大毛病的一篇一篇地挑出去,剩下有小毛病的留下刊發。有沒有完美無缺的作品,也許、大概、可能有;但沒有完美無缺的編輯。
無論作品還是人,至萃無瑕僅是理想化的概念。
再說,當下人評說當下的作品肯定帶有局限。幾個當下的評論家、編輯說某人某篇好,即使不含任何盤外招也未必是真好。金子要淘洗,作品要經過時間的冶煉。
前年,一個朋友和我說:今年所有“年選”都有某人的名字,卻實在看不出其作品的好。我心亦然,只能一笑。
有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永垂不朽,便把作品雕刻在金屬、石頭上,或找大批評論家、編輯、甚至官員來譽美,我認為這是在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是自己給自己挖的陷阱。
027
詩人王燕生先生去世,有近二百人自發地去殯儀館給王先生送行。王先生百日追思會亦有百人主動前來。我欣慰。大家不僅是對王燕生先生的熱愛,還有對詩人、詩歌的熱愛與尊重。一個對詩人、詩歌尊重的民族,是有文明前景的民族。
有人說:詩人愛扎堆兒,蓋因數量少。我覺得此言欠慮。詩人見面三言兩語便如故交,是詩人心底干凈,至少詩人見詩人時是如此。我這般說,并不是說不是詩人就不干凈,此概念是不可偷換的。
這些年,詩人的數量增多且質量普遍提高,其中因素諸多,最重要的是現在的詩人起點高了,從認識到心靈更純凈了。
一位希臘哲學家說:有花兒開的地方就會有詩人。那么,現在的生活已是“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詩人呢?百步之內應有一二吧。
029
因了陶淵明先生的《桃花源記》,去桃園縣游覽“桃花源”。究竟有沒有“桃花源”?這個問題就像問有沒有神仙和妖怪一樣,說有者必有,說沒有者必沒有。
桃源縣的人乃至湖南省的人都一口咬定:“桃花源就在湖南桃園縣。”
我也希望有個“桃花源”。陶淵明先生設定了個理想國,我應該去看看甚至想我為什么不可以設定一個呢?理想國是生活的動力,主要是能洗去紛亂和疲憊。人人都有個理想國,將何其幸甚。
理想國是個“不知有漢”的慢生活。傳說中的神仙過的都是慢生活。“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這種慢是寧靜,而強大的力量都是來自靜穆。
我曾試想躲到一個地方,沒電視、電腦、電話,關掉手機,一包茶、一把琴、一本閑書地過幾天寧靜的日子,但也只是想想,無法實現。不是我做不到,是我已被紅塵染透。
我走到桃園縣的“桃花源”洞口,有幾位抬滑竿的師傅在叫賣生意:“坐滑竿吧,三十元到世外桃源。”我看著他們,就笑了。三十元就能去的桃花源,肯定不在世外。還有,理想國是不能用錢買的。
030
找不到北了。四個詩人在一起找不到北,這是真的。
在青海貴德黃河邊,白天在橋上看,黃河水清澈碧綠,流速湍急。夜晚,皓月當空,繁星滿天。看到這透亮的黃河水,我懷疑曾受到的教育:黃河是“一碗水,半碗泥”。這里的黃河,可以清晰地看到河底的石頭。
都說中華文化就是一條長河,我想過不敢說的是:“我們的文化就是一碗水半碗泥?”當我看到這么清亮的黃河,方悟:我們的文化原本是源清流正的,只是中途有些支流強行加入主流,才使得河水渾濁不堪、泥沙俱下。
在貴德這個夜晚,我們四個詩人在黃河邊找北,結果找到了荒謬。
韓東和胡茗茗在河邊找北斗星,各執一見,我和孫磊加入,也各執一見。
孫磊說這組是北斗星,你們看那顆亮晶晶的星不是北極星嗎!而我們看到的是漫天亮晶晶的星。
我調侃地指著頭頂上方的一顆亮晶晶的星說:這顆是北極星,上北下南嗎!大家笑。
孫磊說:這個建筑(對不起,我忘了這座當下人的仿古建筑的名字),應該是坐南朝北的,北應該在這邊。
我說:不對,月亮正照著大門,此時,月亮應該在西邊,月亮是從西邊出來的嘛!
大家稍一靜默,接著就是一陣狂笑。
翌日早餐,韓東、孫磊和我坐在一桌,相視而笑。唐曉渡、歐陽江河問我們所笑者何。韓東說:昨晚我們在青海的天空找到了四組北斗星,月亮是從西邊出來的,黃河水是清的。
唐曉渡、歐陽江河聽到有這等反常識的論調,立刻像扎了興奮劑一樣準備給我們普及天文知識。
韓東說:我是在寫詩。這兩個理論家不無失望地和我們一起吃著一樣的早餐。
032
現代文明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科技的進步上,也就是技術的發達。技術能力作用在自然環境上,是進步性的開發,也是滅絕性的破壞。我們常說創造力與破壞力同在,是否有利于社會,就看怎樣把握創造與破壞的比例。
詩歌寫作也是一樣。
前些日子,一個朋友給我一些詩歌,我看了就皺眉頭。意象之密,技術手段之全,一首詩就可以開個技術博覽會。技術手段用得過密,看上去很新奇,但幾乎把詩意破壞殆盡。一首詩從你的筆記本走出來,就是要給人讀的,是要傳達藝術感染力的,達不到感染人的效果,這首詩就失敗了。當然,我指的是好詩。至于眾口難調,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由是,我又想到了我們的評論家們。好多評論文章洋洋灑灑都是在賣弄術語,或可稱為技術手段大觀,這些文字只對一(首)部作品進行技術拆解,絕不談優劣,不談文學創造與藝術性。讓我生出:技術有時是遮羞布,有時是妓女立的貞潔牌坊。
我覺得,詩意能順暢表達時,最好就別去用技術手段。“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即直接又樸素,更能直抵心底。
其實,好作家(詩人),技術手段早已溶解在樸素之中了。
033
一個小兄弟寫了一首詩,亢奮地給我打電話,要在電話里給我朗誦。恰巧,我正和幾個外地的朋友談事情,我就簡短地說:發郵箱吧。這個兄弟等不及開電腦,就用手機以短信的形式把那首詩發給我了。
所謂好兄弟,就是在第一時間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告訴你;好詩人,就是能為一次寫作的完成而得意忘形。
第二天,這兄弟給我打電話,問:詩如何?我答:不是好詩。接下來無聲,掛電話。讓這兄弟興奮的是詩中的一句:“不愛烈酒和美女的人,絕不是正人君子。”我本想告訴他,這是常識,不是詩。
近兩年,我常在各種場合借用一位詩人的句子:“我只能用我的靈魂擋住我的身體。”這是詩人大解在他的寓言集《傻子寓言》中的一句。
035
看到一組愛情詩,一個朋友問我:這組詩好不好?我看了看,說:不好。扭捏作態,只注意詞語的絢爛,不坦誠地表露真情,詞語的游戲而已。愛是神圣的,當神圣性不在時,必然會墜入世俗化的語境中。穿著華麗外衣的,常常是肥皂泡。
愛情詩大概是詩歌品種里產生最早的,但一直都少見精品。當下的所謂愛情詩,我看不出來是僅為了寫一首詩而借用愛情,還是為了向所愛的人表達情感而借用詩歌。因為,過于膨脹和夸張,弄巧或裝扮,其真實性就顯得可疑。不僅是愛情詩,那些宏大題材的作品,更是如此。
我覺得愛情詩一定要實,要傳達到你要傳達的地方,要延長接受對象的感受時間,要增加接受對象的情感難度。當然了,按教材的說法,愛情詩亦可分兩種:一種是流氓型(單相思)的,即:我愛你、想你,不管你愛不愛我、想不想我。另一種是呼應型,是互傾心境。我們看到的作品大多是單相思的。
我想講兩個故事。一個是《西廂記》里,張生夜半偷看鶯鶯小姐燒香,春心蕩漾,隨即吟詩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鶯鶯也正是花期盎然,隨即和了一首:“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這對鴛鴦就因為這兩首好詩而成了千古絕唱。
還有一首是挽救愛情的詩。曾讓“洛陽紙貴”的司馬相如到京城當官了,就想換個老婆,可又不好意思開口,拖了五年給卓文君寫了一封信,只是一些數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這十三個數字的家書,卓文君反復看,明白丈夫的意思了,數字中無“億”,表明已對她已無“意”。卓文君知其心變,悲憤之中就用這數字寫了一首詩:
“一別之后,兩地相思,說的是三四月,卻誰知是五六年。七弦琴無心彈,八行書無可傳,九連環從中折斷。十里長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萬般無奈把郎怨。
萬語千言道不盡,百無聊賴十憑欄。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圓人不圓。七月半燒香秉燭問蒼天,六月伏天人人搖扇我心寒,五月榴花如火偏遇陣陣冷雨澆花端,四月枇杷黃,我欲對鏡心意亂;忽匆匆,三月桃花隨流水;飄零零,二月風箏線兒斷。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為女來我為男。”
司馬相如對這首用數字連成的詩,越看越羞愧,覺得對不起對自己一片癡情的妻子,終于用駟馬高車親自把卓文君接往長安。
如果說詩歌的社會功用,愛情詩表現得是十分突出的。敢愛,能寫,會寫(有感染力),何愁不讓愛人動心動容,何愁不被我等叫好。
044
自認為我是有些模仿能力的人,比如我可以學說幾個省的地方方言,有時還可以蒙混得以假亂真。蒙混,就是裝腔作勢。我學方言,是為了好玩,為了和說這種方言的朋友調侃。只蒙聲音、腔調,不蒙事兒。
近些年,我發現身邊多了許多好蒙混者,他們不是為了好玩,是為了真蒙事兒。這些蒙混者,有裝大款的,裝領導的,裝大師的,不一而絕。
我一直認為,不會有人裝詩人,因為裝詩人很難獲得什么利益。更重要的是:詩人不好裝。不是花錢印幾本詩集,就是詩人;不是會寫幾行假大空的抒情文字,就是詩人。詩人是玉,坐在那里一言不發,也會釋放出通透的、溫潤的硬朗。
有裝詩人的么?有!大有人在。在這里,我真心地勸那些端著架子裝詩人,甚至裝詩歌大師的人,要裝也到沒有詩人的地方去裝,別往詩人堆里扎。面對李逵,李鬼只有挨打的份兒。
045
有一幼童名喚:王奕仁。兩歲半時便聰明可人,尤其是口齒伶俐,記憶力超群。他父母教他背古詩,不久,他便可以背出幾十首且能學著講解。
一日,其父領他到我書房,指著我說:“奕仁,這就是個詩人,你給他背一首詩。”他看著我,眨了眨眼睛,開背:“鋤禾——午,汗滴——土。誰知——餐,粒粒——苦。”
他爸爸很高聲地說:“平時背得滾瓜爛熟,怎么到這兒就忘了?”
我說:“他沒忘,他給改了,而且改得好!”
好詩都是三行刪去兩行后,改出來的。詩,不是說明文,不必把時間、地點、來龍去脈介紹得十分清楚,應該留下些空間給讀者。任何一首好詩都是詩人和讀者共同創造的。詩若偉大,讀者也要偉大;讀者若偉大,詩才能偉大。二者缺一不可。再說,詩的語言一定要有限制,不懂得語言精煉的詩,就是一灘爛泥。我看到現在的很多詩,言詞散亂,甚而無際無涯,這種隨意性會傷及詩歌的本質,掩蓋詩中應有的詩性意義。
詩寫完了,再讀幾遍,若有還能切割的就要毫不惋惜地切去,留下的空白,可能會產生更悠長的回響。
簡明、利落和通玄達幽并不矛盾。
我就認為王奕仁小朋友把這首膾炙人口的詩,改得好!
047
一些人寫了同題詩,朋友拿來讓我評評。我就言無忌諱地說了甲優乙劣等等。友問:“同題,因何差距這么大,難道是觀察的角度問題?”
我:“不是寫什么,是誰來寫。詩人的能力、境界決定詩的品質。觀察的角度當然很重要,有多少種觀察的角度,就有多少種生活的現實。角度會決定視野。”
同題詩,我建議不要做。每個詩人的生活經歷和情感經驗不同,駐扎在每個人身上的現實也不同。寫同題詩時,名為同題,詩人寫的還是自己的經驗,所選的觀察角度也必然受到自己的經驗限制。于是,同題詩出來,必有離題之人之詩。評判起來,難免失準。
再者,一旦設定同題,就事先給詩歌施加了重量,讓詩歌的翅膀有了束縛。寫起來,要么為了貼題而使詩歌滯重,要么浮光掠影。
詩人寫詩,要像鳥兒飛翔那樣輕盈,不能像企鵝那樣笨拙(絕無詆毀企鵝之意),也不能像羽毛那樣輕浮。
任何事物都有重量,看誰能掌握輕快的秘訣。詩歌輕盈的秘訣是,寫自己想寫的,愛寫的。
051
寫詩近三十年,編詩近二十年,如果現在讓我必須選擇一項,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編詩。
一個編輯,當他發現一組好的詩歌稿子時,完全可以得意忘形,而且會一生銘記。面對一摞詩稿,像面對一個個陌生的世界。一首好詩讀下來,好像正與朋友半醺而談。即使有些不是很好的稿子,讀下來也會讓我感受到一些人間的冷暖善惡。
好詩讀多了,編發多了,對自己的創作也形成了壓力。我常常對自己說:一定要寫得比自己斃掉的那些稿子好。因由這個自律,一段時間里竟羞于動筆。
后來,自己慢慢體會到,賞花和種花完全是從兩個不同的地方發力。于是,我又開始寫,雖然寫得不多,卻對自己的作品要求苛刻了許多;但,我在種花的時候,尤其是面對自己種的花時,還是無法完全回到我賞花的狀態上(看來孤芳自賞是通病)。相反,在賞花的時候,卻常常想到自己是怎樣種的花。好在我是常賞而不常種,不至于讓自己常常處于暗自神傷的境地。也好在我從寫詩那天起,就沒想過要用寫詩來追名逐利。我一直把寫詩當記日記,求真而不苛求精彩。
工藝精良的假花可以騙過一般人的肉眼,絕對騙不了蜜蜂。編輯就應該是那個可以甄別真假花的蜜蜂。
近些年,我對寫詩下了一些功夫,也是編輯這個身份的壓力所致。可是,“詩有別才”,寫詩肯定不會像種花那樣,有好種子、合適的土地、充足的陽光雨水、適當的養料,再加一點經驗,就能種出好花來那樣容易。(我絲毫沒有低估種花的技術含量,此處只是借來一比。)所以寫出來的詩歌,自己沒看出多好,也感覺不到多壞。
我一向認為詩歌不是去尋找讀者,而是去尋找知音。可是,作為詩歌編輯又必須爭得讀者。所以,我在寫詩的時候就可以率性而為;在編詩的時候既要考慮詩人的號召力,又要看作品的藝術質量,還要顧及讀者群。詩人是我們的上帝,讀者更是。我寧愿一萬個人說我寫的詩不好,不愿意有一個人說我們編發的詩不好。就像我自己的孩子長得丑俊,不會影響整個中國人的面貌一樣。
我編詩很自信,寫詩也不自卑。面對一些詩稿,我會編出我們刊物需要的好詩;當然,我們沒法要求聽慣了美聲唱法的人,一定要他說通俗歌曲好聽,就像不能要求愛吃粵菜的人去贊美川菜。我寫詩時不會考慮美聲、通俗,粵菜、川菜,只想表現真我。
詩歌編輯不可能沒有詩人朋友,但一個好編輯的詩人朋友基本都是出色的詩人,所以有人說編輯只編發朋友的稿子,這種論斷基本是盲人摸象。我的經驗恰恰告訴我,越是好朋友的稿子要求越嚴格。我每每把我的稿子給一些雜志的編輯朋友時,都要說上一句:“可用便用,不好,棄之便是。”至少也要附上一句:“畫眉深淺入時無”。
編輯有編輯的操守,與推杯換盞時的哥們兒間交流不能等同。哪個編輯拿自己的職業、聲譽當鼻涕亂甩,他的編輯職業一定干不長。
我是編輯時,只看稿子,不看“英雄出處”。我寫詩時,不會考慮這首詩給哪個編輯。我也寫過“命題作文”,但我基本不把“命題作文”當作自己的作品。
053
有人說:鏡子是最真實的。
我不這么認為,鏡子里真的是你嗎?你看見你的靈魂了嗎?如果詩人都以鏡子為榜樣,那么,完全可以取消詩人這一稱謂,有攝影師就夠了。
詩人的真實是靈魂的真實,感受的真實,是鏡子無法折射的那一部分。
表象常常是假象。只對著事物的形狀、色彩發感慨、抒感想,是浮光掠影。
重要的是:感想,感慨,都不是詩。
055
魯迅先生曾寫過一首《自題小像》的詩,詩中有一句是“靈臺無計逃神矢”。許多解釋、尤其是教科書上都說:靈臺是心,神矢是丘比特的愛神之箭。魯迅先生這首詩是表達心屬家鄉、祖國,表現出誠摯的愛國情操。
我不能說這種解釋是錯的,但我更愿意按自己的方式解讀。一首詩,若只有一種讀法、一種指向,一定不是好詩。至少是“烏托邦”的單面人。
好詩都是多棱鏡,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會有不同的風景。
某個子夜,失眠。我給一個朋友發短信:“魯迅說,靈臺無計逃神矢。靈臺者,俗世也。神矢者,你也。中箭者,自投羅網者也。”友回:“篡改大師的詩意,有罪。”我真的有罪?人類若不是不斷地犯罪,現在可能還在樹上靠摘果子活著或刀耕火種呢!
記得魯迅先生在“五·四”時期寫有一首白話詩《愛之神》,寫到 “愛神”在射箭之后,被“一箭射著前胸”的人問他:“我應該愛誰?”他回答說:“你要是愛誰,就沒命的去愛他;/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我覺得,這首詩頗像《自題小像》的白話體。
詩人寫詩時,審美方向未必是解讀者的審美方向。說《自題小像》是愛國的讀者,一定是帶著愛國的情緒去讀的;說這是首愛情詩的,也一定是帶著愛情的情緒去理解的。決無孰是孰非之別。詩歌不是紅頭文件,不是法律條文,不可能有非此即彼的規定。
056
參加一個人的作品研討會,我一言未發。友人問:“你怎么不表態啊?”我說:“我表態了啊!”友人:“我怎么沒聽到?”我說:“一言不發,就是最恰當的態度。”
有時覺得嘴真是無用之物,若不是為了活著要吃飯。
常去開這種會,介紹我時,主持人會隆重地說我是“什么什么副主編”。這樣我就理解成,這個會請的是副主編,而不是我商震。可是,我不在辦公室,也不在工作時間內,我憑什么還要替副主編這個職位干活兒?我一直的理想是:我的職務只在處理公務時生效,其他時間,我是媽媽的兒子,女兒的爸爸。或者是個詩人。
我是個自然人,所有的職務都是臨時的附加。
開一些人的作品研討會,我不愛說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實在不想和一些所謂評論家同臺發聲。有些人對作品發言時,感覺是作者拿錢雇來的傭工。那一番滔滔不絕的贊美,大有不把這部作品說成“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誓不罷休的氣概。嗚呼!真是上帝不在場啊!
其實,當那些把尊嚴、敬畏都豁出去,并感覺不到上帝還活著的人講話時,其話語也就和狗屁一樣,瞬間一臭了之。
057
一個大型的詩會,有百把十號人。這時,你就能體會出“人以群分”這一定義的準確性。我仔細觀察了一下,基本上是按著寫作能力和水準分成若干小群體的。像水里的魚,深水魚、淺水魚、珊瑚魚、灘涂魚,絕不混居。
那日,有幾人圍在一起高談闊論某某詩人寫的詩,其中一人高聲說:那個題材,我早就寫了,而且那年就在我們市文聯的刊物上發了。我恰巧從他們身旁走過,距他們還有兩米遠,他們看到我過來就集體啞言。我們相互打了招呼,我接著走,走出距他們五米遠,他們聲浪又起。我很納悶兒,為什么不讓我聽聽他們的高見?怕我偷藝,還是自知淺薄?
真實的情況是,他們清醒地明白:我和他們不是一個水域的魚。
058
很喜歡郁達夫。他有一首詩和一副對聯,我時常背誦,講詩歌課時也常講。詩如下:“猶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輕薄一分狂。只愁難解名花怨,替寫新詩到海棠。”對聯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真誠,坦率。有鐵骨,有柔情。盡管這一詩一聯能有許多話題可談,這里都不贅。關鍵是他用詩歌定義了那些可能瞬間即逝的感覺。
詩歌若不能定義那些轉瞬即逝的感受,詩有何為!
062
十年前,我們幾個作家、詩人在騰沖閑聊,聊百態人生,聊飲食男女。徐小斌問我:“商震,諸子百家,你喜歡誰?”我不假思索地說:“莊子!”在場的人都說:一看你就是喜歡莊子的人。
莊子確實是我的偶像。莊子出身低微,最大的職務也僅是個縣級園林局的管理員。百家爭鳴時,也是亂世,諸子百家都在搶話筒,大家都生怕自己的聲音低了,別人聽不到。更有甚者,或在重要場合發布奇談怪論,或把母牛的生殖器吊在房梁上蹦著高兒吹。莊子不干這事。他不運動社會,不高聲批評他人,只躲在陋巷里讀書著述。他不想影響當時的時政和人生觀、價值觀。他懂得“文章千古事,為官一時榮”這個道理。于是,布衣草鞋,糝湯野菜,與安靜為鄰,與寂寞為伍。幸運的是,這份安靜與寂寞讓莊子的精神是得到了大自由。只有精神自由的人,才會做出大文章。一部《逍遙游》足以讓諸子百家羞愧,更別說《齊物論》、《養生主》等篇章了。
莊子不是靠批判社會的污濁來張揚自己、炫耀自己,他愿意我口問我心。他對神秘的大自然很感興趣。一草一木,一山一川,風吹云起,鳥鳴獸吼,在莊子眼里,都可關情,也都可疏離。探則有幽,不探則皆是身外之物。社會上可以有我這個人,我可以沒有這個社會。其超拔脫俗之至矣。
超拔脫俗是需要強大的內力,不是喊幾句憤世嫉俗的口號,罵幾句社會的不公,喝幾場醉酒,放浪幾次形骸,就算超拔脫俗了。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都是俗人罵別人俗的“賊喊捉賊”。
愚以為,莊子的重要貢獻是他的文章,千百年來安慰了太多的失意文人。
063
常看到一些寫東西的所謂作家、詩人自己撰寫簡歷,洋洋灑灑,千言之巨。簡歷的文字極為炫彩,甚至超過正文。每見如此,我便大為不快,并斷定:這一定是個不自信的人。簡歷嘛,要簡,說明你是誰就行。
我又要說莊子。司馬遷寫《史記》時,對莊子之介紹只有五條:
一、莊子者,蒙人也,名周。
二、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三、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
四、故其著書十萬余言,大抵率寓言也。
五、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堂堂的莊子,僅五行字簡歷,夠簡的吧?有沒說清楚的嗎?沒有!來龍去脈明晰,評價客觀中肯。
今天,我們寫簡歷時,能不能用五行字?能不能自信地再減到兩行或三行。
作家是靠作品介紹、推銷自己,不是靠有吹噓色彩的說明文。虛假廣告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069
莊子的老師是道家鼻祖老子。但莊子不是把老子的“道”全盤接受。老子主張“入世別染塵”,莊子則一邊拒絕塵世,一邊偷偷受用。
老子說:“什么是君子?它山有金礦不采,別海有珠蚌不撈,手不摸觸他人錢袋。心不牽掛烏紗帽,壽高不辦喜筵,命短不須哀悼,闊綽而不矜驕,貧窮而不潦倒。”(老子的這段話,很像現在“反腐倡廉”的要求。)
老子的“君子”原則,不難做到,自律就是。而莊子則遵從另一套“君子”的原則,即孔子的處事方略。“我愛吃牛肉,我見不得殺牛。”
莊子認為,人是由兩方面因素決定的,一是自然界屬性,二是由社會性賦予的。那么,莊子怎樣做“君子”呢?
他說:我有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在社會生活中,我有立場。二是,有立場,我也無為,就是什么也不說,什么也不做。三是,我有理想,我喜歡山水云霧,花鳥蟲魚。我要離現實遠一點兒。四是,我要修心養性,兩耳不聞窗外事。我覺得,莊先生這四項基本原則之后,還有一句潛臺詞,恕我給補上吧:有好吃的我就吃,有好用的我就用,過好自己的日子,不管他人是與非。
這就是莊子的“君子”之德。有逃避之嫌,有軟弱之弊。但在,亂世之中,也是難能可貴。
如今,做到老子之“君子”者,鮮。做到莊子之“君子”者,亦鮮。
070
一個朋友,拿一組愛情詩給我看。他一臉的喜氣,不是他有了愛情,而是他認為寫了一組美妙絕倫的愛情詩。我看了半天,也沒讀出美妙絕倫來,便說:這是一組很一般的詩啊,你怎么這么高興啊?他不服,說:你看,我把愛情寫成了生命的戲劇,不新奇嗎? 我說:不新奇,早已有之。況人生本來就是戲劇。你寫的僅是詩歌和生活的普通意義。
其實,我還想說:抒寫生活的普通意義,是詩歌創作的最大障礙。因我們的私人關系沒到非常好的程度,當時不好過重地打擊他。
愛情只是人的許多激情的一種,它對人的生命影響因人而異各有不同。但是,詩人在面對愛情詩創作時,絕不能憑空想象。沒親身經歷做底的想象,就難免會滑入普通意義。
都知道,愛情可能是幸福或災禍的緣由,但是,只有那種幸福和災禍真的落到你頭上,你才能體會到是怎樣的幸福與災禍。有了體會,再去想象,才可為詩。
愛情詩的寫作要離智性稍遠一點,要聽從肉體、本能、情結、傾向、被壓抑的想象和愿望的指揮,或由創傷性回憶所構成的一個緊密的、獨立存在的整體前意識。一句話,是你親歷的事和你在親歷后所暢想、幻想、聯想、夢想的事。
詩歌,只有在事實和想象之間的距離中,才產生魅力。
071
說:詩歌是詩人的心靈秘密。我認為:此話確鑿。
我常說:詩人別撒謊,除非你不寫。只要寫,并寫得好,一定會暴露心底的秘密。說明一下:秘密并不等同于隱私。
那么,詩人是否是探尋秘密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不懂得探尋秘密的詩人,其作品的力量是有限的。當然,探尋秘密不是在誰的臥室里裝個攝像頭等那樣下作。我說的秘密,是事物的根本、真諦,是根源性意義。
只關注事物的表面,就無法探尋事物的秘密的。當然,有些事物的秘密可能無法探究。但是,任何事物的秘密一定會在事物的表面留下痕跡。一個好的詩人,會在這些痕跡中找到探究秘密的通道。有道是:曲徑通幽。
詩人的任務,就是要打開那些沉默的、不易被傾聽到的東西,應該對一些事物的秘密做自己有力的發現和見證,呈現社會經驗里更為真實的景象。
074
詩是寫給自己看的,還是寫給別人看的?這個問題還真難回答。
只給自己看的詩是日記,日記記錄的是真情實感。給別人看的是藝術品,藝術品就要有美學意義的感染力。我認為:詩歌是二者兼具的。沒有真情實感的不是詩,沒有藝術感染力的也不是詩。
那么,究竟詩是給誰看的?先自己看,自己看著是自己的真情實感,再給別人看是否有藝術感染力。
真情實感是自己可把握的,感染力是自己創造力的體現。創造力不夠,真情實感表達的也不會充分。所以,詩歌僅有真情實感不行,僅有技術手段也不行。只有依靠技術手段將真情實感有效地呈現,詩才完成。
詩,作為文學式樣,最終還是要給大家看。
075
我曾多次在講課中強調:寫作,尤其寫詩,要使用自身的直接經驗。這是必須的。但是,我也一再強調:寫詩要和事實有距離。這個距離是用你的想象力來填補。
后來,這個問題讓許多學生課后糾纏我。他們問我,究竟是使用直接經驗還是使用想象。我真想當面告訴問我的學生,你太無才了。
詩人寫詩,不能只表現已發生過的事件、記錄已逝去的時間,就是不能完全使用已有的經驗,要在審美中表現出一些超現實和超經驗的東西來。這是詩歌最具魅惑的力量。
忠實于事實和合理使用想象,都是詩歌創作的必須。
076
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寫詩?我脫口而出:人難過了才寫詩。
問我的人聽了,自然是一頭霧水。那么,我是不是故意裝腔作勢呢?當然不是。詩人若過著飯來張口水來洗手的日子,精神萎靡,肌肉松弛,四肢慵懶,大概是寫不出詩來的。就算是寫了,也不會是好詩。文本經驗不能產生感情,沒有詩人自身感情的加入,詩便會是只具其形而無其內核者也。
詩人寫出好詩的秘密只有一個:保持對環境的陌生,保持對身邊人和事物的敏感。
能保持天天在已熟視無睹的生活環境里的陌生和敏感,是件痛苦的事。可是,離開了陌生和敏感,詩人又何以為詩呢?
寫詩或詩人,不是個社會職業,但一定要有職業病。這個職業病,就是讓自己的精神世界不和身邊的人與事,絕對茍同。詩人一旦對身邊的世界產生懷疑,能問幾個為什么的時候,詩就悄悄地走來了。
一個人若總在懷疑和自問的狀態下,這是不是一件難過的事?難過了,就想傾訴,傾訴得透徹,傾訴得有美感,傾訴得讓他人感動,這就是詩了。
詩歌與宗教有所不同。詩歌常常表達對當下幸福的不信任;而宗教則是在來世給你一個幸福的許諾。
有一句話詩人應記住:俗常的世界,總是暗中與詩人為敵,不警惕,就是把自己廉價地賣給了俗世。
這下該難過了吧!
077
詩歌的社會功能,是多少年來討論的話題。此話題不會有絕對準確的答案。一首詩能安慰一下正在寂寥的情緒,這肯定是功能,但這個功能還沒有實現完全社會性,還不足以強有力地說明詩歌有社會功能。
有這樣一個故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一家很大的電子公司中國公司要在中國找一位高管,當時的年薪是30萬。乖乖!那時,我們的月工資最多不過一千多塊。可想而知,全國來報名的青年才俊有多少?經過一層一層地選拔,最后只剩下兩個人。各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了。這兩個人真是優秀啊!可人家只要一個人。怎樣來取舍呢?考官們也技窮了。這時,英國的老板出來了,他用英語對這二位說:“請用英語默寫一首莎士比亞的詩。”有一位小伙子勝出了,另一位不會默寫莎士比亞詩歌的人出局了,其沮喪之沮喪是可想而知的。當眾多考官疑惑時,這位英國老板主動說:“在英語世界里的白領,不會背誦莎士比亞的詩歌,是不可信的。”
看看,詩歌的社會功能很強大吧。還有一個故事,就是最近發生的事。
北京某大學的美國留學生,告訴他導師一個秘密:“老師,我知道怎樣讓我的中國同學們看著我就望風而逃的辦法了。”他的導師說:“你是怎樣辦到的?”這個美國留學生說:“我只要從書包里拿出《唐詩三百首》讓他們給我講講,他們就都跑了。”他又接著說:“可他們講起美國來,好像比我還清楚得多。”估計這位導師當時是欲哭無淚。當中國的學生們認為《唐詩三百首》無用時,美國人卻用來羞辱我們。
我不知道,那位導師后來是自殺了,還是辭職了。反正,詩歌又一次證明了它的社會功能。
我想說詩歌的社會功能是:如果我們不借助詩歌來談論世界,世界就不會這般真實。
079
大學中文系的《文學概論》中說:詩歌,一定要形象思維。我上學時,深信不疑。真的只有形象思維一條路通向詩歌嗎?現在我才敢說:未必。當然,我不想在這里討論詩歌的寫作方法,我只想討論,詩歌一定要形象思維這個論斷是怎樣根深蒂固地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骨子里的。
我們的各級學校,多少年來,讓學生讀的詩歌,老師為學生講的詩歌,都是按照《文學概論》的要求來進行的。所以有些中文系的學生,看到現在刊行的詩歌,說讀不懂,或胡批亂談。何也?這些學校里的學生,是在被教學指導大綱和教學參考所規定了的環境里學習詩歌,學到的一定是考試的規定范圍,而不是詩歌本身釋放的要求。苦啊!這個苦,不是學生,而是泱泱詩國的詩歌。
陳子昂寫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首詩里有什么形象呢?難道陳子昂就僅是寫一個老頭在默默地哭?
天下事,都不止有一條路通往成功,何況詩歌!
形象,對詩歌非常重要,那是讓詩歌飽滿、鮮活、生動可感的首要通道。但絕不是唯一通道。
我要說的是:在一個靠拿著《文學概論》的教授來解讀詩歌的環境里,是不會誕生詩人和批評家的。我見過的一些詩歌研究方向的文學博士,畢業后從事批評或理論研究,大多是無才又無能的。我想:他們在天天背誦形象思維的環境中,把自己的形象交給了導師。當走向社會的工作崗位后,不過就是一個穿著衣服的《文學概論》。
080
又要說到詩歌的語言問題。其實,在說詩歌語言問題之前,我更愿意先說說詩人的獨立性問題。
詩人,或一個成熟的詩人,首先是獨立的。其獨立表現為審美判斷的獨立;語言使用的獨立;表達方式的獨立。有了這三個方面的獨立,詩人當是有了品格的獨立。品格獨立的詩人,常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當生命和語言相遇時,詩歌將聽從哪方面的安排?我認為,詩歌在處理語言和生命的關系時,應該讓語言取勝,而不是一味地凸現生命狀態。
詩人與語言建立的關系如何,是詩人表現力、創造力的標識。
不想占有語言,也不會被語言擁有。表層表達用的語言是飯,只能用來充饑,而詩歌所用語言是酒,用來讓人沉醉。
語言未必求新,更不必仿古。求恰切,是詩人一生對語言的追逐。
有人詬病說,今天的漢語新詩用白話文,失去了詩意的韻味。我不敢批評有此說法者是一葉障目或無知無畏,只想試問:杜甫先生的“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不是和今天一樣的現代漢語嗎?李煜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不是現代漢語嗎?漢語一定是用上“之乎者也”時才有韻味?
好詩人,都會把語言的運用看作是詩之本,承載生命之本。
081
我喜歡郁達夫。他直截,明確,簡潔。重要的是,在直截、簡潔之后,能繞梁三日余音仍在,能觸動“人人心中有,大多筆下無”的情愫。詩人把自己的生命狀態、情感狀態隱藏起來,用什么花哨的語言也不是詩。“猶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輕薄一分狂。只愁難解名花怨,替寫新詩到海棠。”還有:“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這兩首詩,真夠那些天天哼哼唧唧、淺吟輕噓著寫愛情詩的人,學幾輩子了。
詩人的語言是用來表現生命的,不是用來吹成炫彩的泡泡取悅他人或自己的。
詩人首先應該是醒著的人,醒著的人就別說夢話。
我覺得讀郁達夫,比讀《紅樓夢》詩詞過癮。
083
我很喜歡一個美國人,叫愛默生。他是個思想家,但不是個思想傳道者。他可以受邀去演講,就是不收學生、門徒。這和中國的思想家等“大師”大有不同。咱們的思想家都是“弟子三千”。
近些年,出現了許多偽思想家,他們是門徒、食客眾多,有些人還特意在簡介和名片上赫然印上“某某弟子”。而那個“某某”,我也沒看出有什么獨到的思想。不僅是思想家,藝術界更甚。我甚至懷疑,這些門徒、食客是這些“大師”請來發小廣告的。
張愛玲這樣評價愛默生:“他并不希望有信徒,他的目的并不是領導人們走向他,而是領導人們走向他們自己,發現他們自己。”
向愛默生學習!向愛默生致敬!
084
沒有哪一個詩人說:我就是不讀書,生而能詩。都在讀書,可所得到的結果卻是大不相同。就像我們看到一段躺在工廠里的木頭,有人看到的是修行的樹,有人看到的是家具。
書如太陽,若把自己當作成年人去讀書,太陽只能照亮了你的眼睛;若把自己當成兒童來讀書,太陽可能就會照徹心底。所以,讀書時,把自己以往的經驗先清空。在學習新東西時,成熟是最大的障礙。
只被照亮眼睛的人,是固執的、不太喜歡接受新東西的人。固執的人為詩,能走多遠,可想而知,現實中這樣的人常見到。
我喜歡這樣一句話:要學習大人物的本領,要保持小朋友的心情。
欲與詩為伴的人,切銘記。
089
一個詩友拿著一首詩來給我看,并信心滿滿地說:我這首詩,對今天的社會有著強烈的批判作用、驚醒作用、指導作用等等,說著說著,好像他寫的不是詩歌而是拯救社會的法律文本或政府施政大綱。我拿過來仔細看了看,藝術能力姑且不說了,僅就內容而言,不過是把社會丑陋現象絕對化,孤絕地認為這個社會沒救了。況且,他好像是站在火星上看地球,或是在美國、法國等地兒看中國。我笑了笑,簡單敷衍幾句,對他這首詩沒再說什么,就把話題岔開了。這種人的自信來源于固執,甚至是偏執,對他進行理性的說服,可能是做無用功。他走后,我卻內心悲涼。
我們的社會確實有陰暗的、丑陋的現象,但也不至于暗無天日。重要的是,一首詩會有那么大的拯救力量嗎?面對社會問題,喊著詩人何為或詩人無為,都有些極端。生于此時代,就負有此時代的使命。詩人也不例外。
詩人不能與時代為敵。要以原諒自己的姿態,原諒身邊的人和一切看不順眼的事物。或者再寬闊點兒說:愛自己就要愛身邊的一切。
詩人可能有時是身處時代的背面,保持著凝視自己內心幻象的權利,或像在夢中一樣觀看社會事物。但,你無法永遠活在夢中,無法不走出內心幻象。你有萬種風情還是千仇百恨還是要落到地面上,還是要與人訴說,與人了結。
詩人的獨立,不是與世隔絕。
話說回來,社會丑陋現象,古今中外皆有,從來就沒滅絕過。這也是社會豐富性的體現。無惡哪有善,無丑哪有美。
丑惡現象是蟑螂,用什么辦法殺戮都僅僅是控制它發展,而不能把它滅絕。詩人或詩歌也僅是滅蟑螂藥中的一種成分。
093
閑翻《東坡文集》,看到東坡先生《送安節》詩之十,有這樣兩句詩:“應笑謀生拙,團團如磨驢。”看完我就笑了。一是笑,過去咋就沒讀到這兩句大白話呢?二是笑,這是說誰呢?蘇東坡這等骨硬氣豪的人,一生坎坷,但都是樂觀地對待生存現實,他怎么竟也發出這般慨嘆!不想說蘇先生了,他的故事都是耳熟能詳的。我讀了這兩句詩后,竟幻覺地認為蘇先生是寫給我的。于是,也感慨良多。
一位頗懂星座的朋友說我是毛驢座,開始甚為不解,十二個星座,怎么到我這就多出一個毛驢座來?讀了蘇先生的這兩句詩,才算明白。原來毛驢就是“謀生拙”,就是要圍著一個大磨盤,一圈一圈地負重勞動。我在農村見過驢拉磨,還要蒙上眼睛。蒙上眼睛是給毛驢一個錯覺,腳步不停地走,好像是在前進,其實是原地轉圈。毛驢的工作態度是極好的,屬于埋頭苦干型的。但,實在累了,心情不舒暢了,聞到異性驢的氣味主人卻不讓見面時,也會伸長脖子嚎叫幾聲。盡管驢叫很有穿透力,噪音分貝很高,有時能嚇跑老虎,卻嚇唬不了手握鞭子的主人。嗨,所謂嚎叫,不過就是發發牢騷而已。牢騷發過,照樣一絲不茍地干活,眼睛依舊乖乖順順地被蒙上。
我是毛驢座,是不是“磨驢”呢?我“謀生拙”嗎?我還真得好好逼問自己。
095
前些年,一個詩友用短信給我發了一首詩,是一首愛情詩。問:“此詩如何?”我看了一遍,以為是他剛寫的,就回復:“很熱烈,有頓悟,但說教性強。重要的是內涵不足,不是好詩。”
我這段短信,招來他對我的嚴厲批判,甚至斷定我是個偽編輯。他說,這是中國最好的詩。
我自然是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了。一段時間里,這位朋友和我沒有任何來往。后來,才知道,他發過來的詩,是倉央嘉措寫的。我一方面譴責自己的閱讀不夠、孤陋寡聞,一方面對這位朋友肅然起敬。他對倉央嘉措竟如此堅貞,竟不惜與我決裂!
當然,我也不會向那位朋友道歉。在這里,我也不想討論倉央嘉措的詩歌成就。或者直接說:用職業詩歌編輯的眼光去評判倉央嘉措的詩歌,是對倉央嘉措的不公平。倉央嘉措是個有詩性意義的高僧,不是詩人里的和尚。還有,倉央嘉措是用藏文寫作的,我們看到的是被譯成漢文的作品。看翻譯成漢文的倉央嘉措的詩,其實大部分是看翻譯者對詩歌的理解力和兩種語言的使用能力。所以,僅我看到的譯成漢文的倉央嘉措的詩,就非常值得尊重,也理解了那位為了維護倉央嘉措而和我生氣的朋友。
后來我買了倉央嘉措的幾本詩集,認真讀過后,我對倉央嘉措也敬佩有加。倉央嘉措先生有信仰、有血肉,具備了詩人應具備的素養。我敬佩他詩歌中的感悟大于理性。
我一直記著倉央嘉措的一句詩:“一個人要隱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過一生。”這句詩,太直觀,也太豐富,會觸動每一個人的心底,會讓每一個人在這句詩文面前沉默一會兒。
097
孔圣人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可孔圣人沒說,《詩》三百,放之四海而皆準,任何時代都正確。于是,用《詩經》里表述的義理來衡量今天的事,就不好說了。比如那首《氓》。詩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這里的“說”是通假“脫”,即“脫離”之意。用白話解釋就是:男人陷入感情糾葛,很容易解脫出來,因為男人的排遣方式多;而女人陷入感情糾葛就不易解脫出來,女人總是圍著鍋臺轉,炕頭到院門是最遠的活動距離。于是就“獨念深居,思蹇產而勿釋,魂屏營若有亡,理絲愈紛,解帶反結。”這個描述在當時或在封建社會里基本沒錯,而且中外亦然。一個歐洲的作家也曾這樣描述:“愛情于男人只是生涯中的一段插話,而于女人則是生命之全書。”
這個觀點,我是十分認可的。無論在古代還是在近現代,男女的社會分工明顯,社會地位差距較大,《氓》所述的那種情況是正常的。就像流行的一句話:男人是要征服世界,女人是要征服男人。可當下呢?
現在好像沒幾個人再說: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啦。為啥?簡單地說,沒有女人配合,男人跟誰壞去?夸張地說:男人還有什么資格和能力保持壞的榮譽?
我就看到幾個大男人被女人耍了,還為情而癡而不能自拔的。還看見有些女人換個男朋友或情人比換件衣服還容易的。不是物極必反,不是矯枉過正,是男女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地位趨于平等了,是女士們在證明“誰說女子不如男”。如果還用老觀念去對待情感上的事,男人就只能陷進泥沼而無法自拔了。有一句話似乎過于偏激,但可作為警示語:現在的女人都是可愛不可靠的。
《氓》中的“士”與“女”是不是可以對調了?我看也未必。
無論如何,男女平等是好事,是社會文明的標志。平等才能互相尊重,尊重才能熱愛。但我擔心現在的女士們沒有改變“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價值觀。常看到、聽到女士們選擇情侶的對象是金錢和權力的擁有者。這種情況,如果有愛,愛的也肯定不是那個男人。
都說:感情的事,最難說清楚。我覺得:愛,是件簡單干凈的事。說不清楚的感情,一定不是真感情;是脫離了愛,而為了其他利益。政治、軍事、商業都可以有秘密,感情不應該有秘密。有秘密的事,才說不清楚。
愛,只能一往情深。愛,絕對不能等價交換。
098
一段時間里,一些青年女詩人遭到猛烈攻擊。網絡、短信、匿名信滿天飛。什么某女詩人和某某評論家、某某編輯好,所以才發的詩,等等。故事編的不新,所用詞語除尖酸刻薄外無一長處。我就想問問:為什么總要質疑女詩人的身后一定會站著一個強大的男人才能寫作?古今中外,那么多優秀的女詩人都是身后站著一個強大的男人?優秀者,必然出色;笨拙者,身后站著誰也不會優秀。當然了,這些非議并不新鮮,古來有之。關鍵是現在有那么一些人,大有哪個女的寫詩且寫得好、發得多,好像偷了他家的東西一樣,就立刻給她編排一些歪的邪的故事。真乃怪哉!若要我解釋,那就是一些心底齷齪的人,用齷齪的眼光去看一切。或者是自己寫不出好東西來,誰也別想順溜地寫出好東西。有一兩個齷齪的人,是正常的,若齷齪之人太多了,就不正常了。不能把詩壇當名利場來對待。詩壇在任何社會形態里都不會是強大的陣地,所以,別把發幾首詩、得個什么獎看得太重。詩歌,除了能安慰自己,其它功能都是有限的。
我肯定承認有些女詩人利用一些手段刊發一些作品,但是,凡是使用手段發作品的人,一定是三流以下的詩人。這種人發點作品也不會有什么大影響,最多像得了感冒,幾天過去,不醫而愈。
還有一甚者,某某人不斷地用各種手段說某女詩人抄襲了他的作品,并把兩個人的詩作呈給大家看。不看則罷,一看,怎么也找不到抄襲的痕跡。這就是某人的心態出了問題。若果真有抄襲的事,肯定是可恥的,是萬劫不復的。要說明一下,偶爾的借鑒,不能劃歸為抄襲。
我來舉個例子。“九葉”詩人里曹葆華的代表作《她這一點頭》:“她這一點頭,是一杯薔薇酒;傾進了我的咽喉,散一陣涼風的清幽;我細玩滋味,意態悠悠,像湖上青魚在雨后浮游。”大家看著熟悉吧?曹葆華就是借鑒了徐志摩的《莎揚娜拉》寫的這首傳世之作。但比徐志摩寫得好多了,徐志摩的《莎揚娜拉》最多是首三流詩作。能說曹葆華是抄襲嗎?絕不能。
簡而言之,靠非正常手段和抄襲的詩人,無論男女,都不可能是好詩人,最多制造點非詩的事件。好詩人,在起步時稍有借鑒也是在理解范圍內的。
詩人,無論男女,滿腹詩書下筆有神時,有點兒流言蜚語就當是另類廣告吧。
099
一次大型的詩歌活動,近結束時,主辦方在一個大會議室擺放許多桌案,請來參加會的詩人給留“墨寶”。許多人都紛紛拿著毛筆寫字,凡是能拿毛筆寫字的,好像主辦方專門安排一些人在旁邊高呼:“好,這是真書法家!”當然,現場就有人對“書法家”這個稱謂洋洋得意。一個朋友對我說:“現在被稱作書法家的人,有一億。”我聽了當時就一驚。一億人是書法家?全國的十三分之一!若果真如此,國家之大幸焉!
我也時常用毛筆寫字。我只是覺得一個中國的詩人,不懂得用毛筆寫字是缺憾。掌握漢字的間架結構和書寫的速度是寫毛筆字的要義,也是寫詩的要義。更重要的是體會“歷史感”。沒有歷史感的詩,會無根,會淺表。所以,詩人寫毛筆字,是詩歌創作的重要補充,而不應該向“書法家”進軍。“書法家”是因社會分工而蓬勃壯大的,但,不懂詩情畫意的書法家,也僅是個匠人。
說句大不敬的話:有些人是不敢去制作人民幣,才去制作書畫的。所以,有人一旦背上“書法家”、“畫家”的名號,好像已看到身后滾滾的人民幣了。
我想起讀過的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當時是按文學作品讀的,近日又重讀一遍,覺得社會意義更強。我把這篇文章常年放到我的書桌上,以便時時看看,讓老舍先生時常對我耳提面命。這篇文章的名字叫:《寫字》。
100
某日,一群朋友在曬自己聽到、看到的民間反腐段子。說實話,有些段子編得真是有才,常常讓我們這些靠寫東西吃飯的人自愧不如。當然,更多的段子是借殼生蛋。比如借用婦孺皆知的古詩詞來填新詞,很機智,很風趣。其時,一個朋友說:“某縣的一面醒目的墻上,老百姓用特大的字抄寫了《水滸傳》里的一首詩:‘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全縣的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有關部門也不好給涂去。”我們心里都清楚,把這首梁山泊最初起事時的詩寫在墻上的寓意。民怨近沸啊!
后來,大家散了。我突然想,這首“赤日炎炎似火燒”的詩是誰寫的?當然不是書中人物白勝所寫,是施耐庵寫的嗎?我依然存疑。因為許多小說中的詩是借來的。《三國演義》的開場詩就是借楊慎的,盡人皆知。那么這首詩究竟是借的,還是施耐庵自己創作的?我一點兒也不懷疑小說家會寫詩,只是對小說中那些寫得非常好的詩生疑。此疑,一直被我埋在心中。
一日,翻閑書,突然翻到了這首詩的原型。晚唐大和年間有位名聲不大的業余詩人,叫顏仁郁,是個小企業家,官職是福建泗濱陶瓷場的場長,業余時間喜歡寫點兒詩。他的原詩如下:“夏日炎炎如火鉆,野田禾秀半枯干。皇天不雨農家望,何恨龍神不我看。”這首詩,確實有點兒業余,無論如何也不能和施耐庵的那首詩pk,但施耐庵借用的痕跡也相當明顯。施耐庵是抄襲嗎?非也!能說施耐庵是創作嗎?亦非也!第一,小說家在書中借用他人的詩詞,或稍加改動,嵌在書中是在不成文的允許范圍的。情節、人物都能虛構,何況借用幾首詩詞?只要對小說的故事發展有利,“拿來”就是。第二,施耐庵也不完全是借用,而是進行了再創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施耐庵并沒有把借用或再創作的作品,寄到《詩刊》來投稿,僅是作為小說故事發展的一個小細節。不當原創的詩歌發表,就等于承認不是自己原創。
現在,許多詩歌作品涉及到如何界定是否抄襲的問題,不知以上我對施耐庵那首詩的解讀,是否有幫助。
101
近年,在魯迅文學院帶詩歌組的學生,指導詩歌創作。我常問自己,用教學手段來培養和教育能不能誕生詩人?
這個問題,應該是沒有定論的。即使名牌大學開設一個詩歌系,請名教授來教授課程,也未必能培養出好詩人來。大多數詩人都是自己“悟”出來的。那么,我面對學生時,能做什么?我要做的僅是增強他們的詩歌寫作知識,給出一個盡可能正確的創作方向。
我謂詩人,大概有三個層次:知識型,智慧型,天才型。
這三個層次又是階梯狀的。沒知識,不可能有大智慧,沒大智慧,就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寫作。
占有更多的知識是詩人創作的底蘊,是使作品豐富飽滿的基礎,詩人的知識量就是作品中的文化信息量,知識是基本技能使用的保證,是人生價值觀的判斷依據。智慧是境界,是參透和頓悟的能力。天才是有知識、有智慧后的火山爆發、瀑布奔瀉和海闊天空。李白、李清照是天才;杜甫、杜牧僅到了智慧這一層;至于孟郊、賈島這樣的“郊寒島瘦”,也就是有知識的詩人。
于是,我對學生做的是:讓他們補充知識,啟發他們的智慧,激勵他們挖掘自身的天才潛能。
詩人不是手把手、耳提面命就能教出來的,更不可能“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溜”的。石頭蛋無論怎么加熱,也不會孵出小鳥來。
105
我很喜歡看練太極拳的,一次,在一個廣場看到幾十個人在練太極拳,我定定地從他們開始練看到他們收式結束。
我覺得,打太極拳和寫詩相通之處很多。比如:要靜。靜,才能讓五臟六腑歸位,才能詩思萬千。要腳下有根,頭上有天。要柔中帶剛,綿里藏針。要密處不透風,疏處可放馬。等等。
腳下有根,是生活的扎實、具體;頭上有天,是文化境界、審美趨向。
寫詩,不是孤立的事,是和生活中的林林種種息息相關。生活中的任何一種事物、現象,須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諳熟了,參透了,必有頓悟,必得詩歌之營養。
永遠不會相信,一個“宅”在家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人,會寫出好詩。
翁同和先生說:“每逢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先賢。”
106
常聽到一些詩歌寫作者說自己的生活環境惡劣,并因環境不好而寫不出作品來。我覺得,詩人不該埋怨環境不好,不該謾罵或憎恨生活環境,更不該靠大聲譏諷和謾罵來尋找自己的存在感。每個人的生存環境都大同小異,不可能有一個特別適合寫詩的環境,有陽光、空氣和水的地方,都是適合寫詩的地方。
詩人不能只享受生活,而不去適應環境。智慧的詩人會使環境和事物適應自己的思想,會在環境中汲取營養和力量。抵觸,是拒絕;拒絕,就是孤立;孤立就無法獲取營養和力量。失去了環境的營養和力量,自然就不會有詩歌產生。
說句實話吧,在生活中,常以詩人自居者,都是孤立的人,無為的人。
再狠點兒說:那些一事無成的人,一定是一身無能的人。
107
一直想談談當下詩歌批評的狀況,一直都懶得去說。就像我們經常看到有人當街扔垃圾、吐痰一樣,因司空見慣而認可。我這樣說,并不是當下沒有好的詩歌批評和好的詩歌批評家。而是好的批評和好的批評家太少。
有一個現象是奇怪的,這些年都想當批評家,竟使得批評家多如牛毛。批評家多不是怪事,自詡是批評家者太多,就是怪事。最怪的是:只會膚淺地表揚也自稱是批評家。為啥都想當批評家?不言自明:有利可圖!騙錢者有;騙色者亦有。沽名釣譽者多;無知蒙事者多。具體例子我就不舉了,給那些假批評家留點兒面子,也給自己積點兒陰德。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詩歌批評家?當然是有知識,有個人見解,有自己主張的思想者。思想者是永遠醒著的人。那么,批評家應當是經驗的,還是理性的?
我想:沒有理性支撐的人難為批評家,同樣,沒有經驗的人也難稱批評家。經驗和理性不是一對天敵,對批評家來說是“人”字的一撇一捺。一個批評家,首先要對文本提出“為什么”,并能回答這個“為什么”。要在理論的范疇里自圓其說,要能征服作者和讀者。不是把書本里的專業術語堆砌在一起嚇唬人,也不是對作品中的字詞句進行反復推論。我想大膽地說:詩歌評論絕不是科學范疇,或絕不可能成為一門科學。
首先,詩歌批評一定要具有強烈的個人性,失去了個人性的批評,就是對以往理論的總結和歸納。其次,詩歌批評所關注的價值是情感,而情感恰好是科學要忽略的價值。若像分析天文、地理那樣去分析詩歌,像辨析石頭的紋理、植物的葉脈那樣去辨析詩歌,詩人還能是感情動物嗎?
詩人是感情動物,詩歌作品也是感情的產物,在感情世界里,怎樣產生科學?
詩歌批評只能是對所批評的作品,給批評家的感受做推理論述,而這個論述的檢驗標準是感情,不是宏大理論的賣弄,不能用一種道德代替另一種道德,更不能用書本理念代替感情。
至于那些打著批評家的幌子,挪用一些貌似高妙理論來蒙事的人,就不多說他們了。因為,他們只能蒙低俗的人。
108
做了二十幾年文學編輯,最怕的事就是走到哪兒都躲不開文學。上班讀文學稿子是職業需要,可是和朋友吃個飯,也要有人和你談文學,喝個茶也有人和你談文學,游山玩水時,也會有人跑過來和你談文學。真煩!我當然理解那些不失時機來找我談文學的人,可就是沒人理解我這個想不失時機躲開文學的人。
能正身修德的是世道人倫;能滋養心脾的是風花雪月。所以,我從事了大半生文學,還是關注世道人倫,熱愛風花雪月。
110
杜甫的《絕句》四首之一:“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應該是盡人皆知,這主要歸功于歷代書法家。書法家不斷地抄寫、懸掛,使之傳播有力。當然,也不能抹殺課本的力量。在中學課堂上學這首詩的時候,我的記憶極為深刻。老師講的是:這首詩,寫出了杜甫當時的復雜心情。大意是:詩人對絢麗多彩的早春圖像,分別從視覺和聽覺兩個角度進行刻畫,尤其是門外泊的船,來自“東吳”,此句表明“安史之亂”的戰亂已平定,交通恢復。詩人睹物生情,想念故鄉,并強調用一個“泊”字,有其深意。
許多年來,我一直不敢對老師的講解生疑。可是,我的職業要求我必須把這首詩的真正意義解讀出來。我反復地讀,也查閱了一些資料。像我的中學老師那般解讀的占大多數,合我意者幾近于無。我只能憋著。大有在朝堂之上有人指鹿為馬,我卻不能說真話,還得“諾,諾”。現在我想大不敬了,這首詩,就是老杜做的對仗練習!他同時寫了四首絕句,唯這首是寫著玩,或唯這首是為了炫技而寫。
這首詩表現的是四個獨立的圖景,誰也不挨誰!對這首詩的其他解讀都是牽強的,或是讀者自己的再創作。如果這首詩還有什么具體意義,那就是對仗練習的范本。
這首詩寫于公元764年的成都草堂,“安史之亂”已平定一年多了。杜甫此時正是消遣悠閑的時候。我們可以看看他同時寫的另外三首。
一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
梅熟許同朱老吃,松高擬對阮生論。
二
欲作魚梁云復湍,因驚四月雨聲寒。
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三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
苗滿空山慚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讀了這三首詩,足見杜老先生正在飽暖生閑事。
悠哉悠哉的杜老夫子想寫詩,又無事無激憤無牽掛,可是春天來了,還是要寫點啥,就提筆練習一下詩歌對仗中的字對詞對句對音對色對等,“兩個黃鸝”對“一行白鷺”,“千秋雪”對“萬里船”吧!哪里有“戰亂平定,交通恢復”和“思念故鄉”的感慨!再說:“安史之亂”根本就沒影響過長江流域的交通。不知今天的課本還有沒有這首詩,不知道今天的老師們怎樣講解這首詩?真替學生們擔心!
我還要說的是,不是詩人寫的每首詩都一定具有深度解讀的意義。無論李白、杜甫,還是誰誰。
111
有一句近乎俗語的話,叫:一字之師。這句話聽起來像玩笑,像戲謔。而在詩歌創作中是常見的事。一首詩中,一個字的改動常常可以讓整首詩鮮活起來、生動起來、遼闊起來,此類事例很多。但改動的這個字,基本是動詞或名詞。比如:“大江日夜流”不是詩,是自然狀況,可改動一下動詞的位置,變成:“大江流日夜”就是詩了。這一改動,使得時間、空間強行并置,歷史和當下同步運行,互相映照,互相滲透,意味悠遠。
“一字之師”是存在的。真有為自己改動一字而成好詩的人,應視為一生之師。
有些人寫了詩,不喜歡別人改動。好像他寫的詩是金鑄的鐵打的。除了“敝帚自珍”值得尊重外,其余就是自戀、自閉、固步自封了。
好詩是改出來的。此類事例就不贅了。
寫詩,千萬不要被自我感動所欺騙。
112
詩歌被誤讀是經常發生的事,而且是正常的事。
詩人寫詩,是想讓感動自己的情緒在另一個或另一些人身上再震動起來。甚至,有些詩人在作品中設定了特指物象,試圖引導讀者解讀的方向。但是,讀者在閱讀時是自由的,是詩人不可限定的。其實,詩歌創作,不可太用心機,只管忠實創作時的情緒,任何多余的想法都可能是鐐銬或通向死亡谷。
讀者怎樣去讀,不是詩人要擔心的事。許多偉大的作品都是被誤讀出來的。最典型的就是卞之琳先生的《斷章》。這首短詩,本是一首長詩的一節中的幾句,發出來后,被讀出了偉大。卞之琳先生寫這首長詩到截取這首短詩時,一點兒也沒想過會偉大。
誤讀,不是錯誤地讀,是違背詩人原意地讀。最典型的例子是,一首詩被作為考試題去考學生,而作者本人卻目瞪口呆地一道題也答不出來。
讀者讀詩,無論喜愛還是憎恨,大多都會違背詩人創作時的意圖,因為讀者都是從社會屬性的角度出發,從自身的文化修養、生活經驗出發,而不是從詩歌本身的要求出發。那些年的“梨花體”、“羊羔體”也是這么誤讀出來的。
《增廣賢文》有這樣的話,叫:“不是才子不獻詩”。才子者,詩人也。
就一首詩的社會性而言,詩人創作出來的詩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是由讀者來完成的。什么思想性、美學意義、文學價值、修辭力量、生活本質、社會反映等等等等,都不是詩人創作時刻意設定的。
說到末了,一首詩一定要經過讀者“誤讀”的再創作,才算徹底完成。當然,有的詩被讀成了偉大,有的詩被讀成了垃圾。
114
詩人一定要天真。天真不是幼稚,不是簡單,是有天地之真氣,天地之真心。《易經》復卦中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爻辭解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我更愿意把它解讀為:詩人應具備的天地之心,或詩人應具備愛憎分明的立場。
天地之心,是明月耀蒼茫,桃花笑春風。
詩人是最該明確地分辨忠奸、善惡、美丑,最該旗幟鮮明的。對文要細辨優劣,對人要判善惡。詩人可能找不到終極真理,但要找到一個能安放個人身心的有天地真情之處。
好詩人之間大多是好朋友,像李白和杜甫,年齡相差很多也能“遇我宿心親”。一個好詩人遇到另一個好詩人,未必要事事合二為一,但是觀點、立場一定是同一的,有點兒像一加一大于二。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形容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系時說:他們兩個“像是兩塊對立豎放的鏡子,無限地反射對方、深化著對方”。古今中外,此類例子甚多,此處不贅了。
我一向認為,天下最牢固的友情是好詩人之間的友情,澄明、透徹、肝膽相照,沒交易紛爭,沒利益糾葛。文本上可以有分歧,審美立場一定趨同。
當然,不是所有的好朋友一定會同仇敵愾。但是,態度一定要明確,在關鍵問題上含糊、曖昧,做好好先生,估計,與好詩人成為好朋友也可疑。
有天地之心者,真情真意不會稍縱即逝,而是生生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