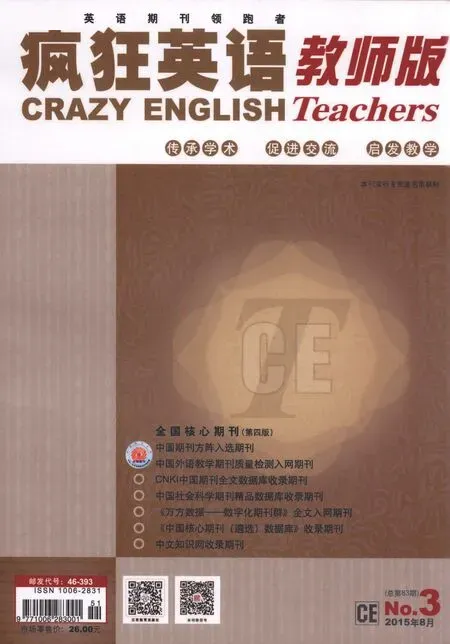翻譯特性視域下的漢語文化詞語英譯探析
摘 要:以翻譯特性視域下的翻譯文化特征之社會性、文化性、符號轉換性、創造性和歷史性五大特性為視角,以著作、新聞用語等為語料,分別從幾個特性出發,探討分析漢語文化詞語的英譯特征。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5)08-0141-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3.036
收稿日期:2015-7-8;修改稿:2015-7-24
1. 引言
語言是什么?各國學者定義不一。
漢語之所以稱之為漢語,是根據語言的特點來決定的。在語言結構內部各要素之間,詞匯是語言的基礎,是記錄文化的主要載體。常敬宇在其專著《漢語詞匯與文化》中明確提出了文化詞語:“是特定文化范疇的詞語,他是民族文化在語言詞匯中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如何更好地解決漢語文化詞成功的英譯呢?以往的作者只是就翻譯特性的某一方面對漢語文化詞的英譯進行分析,我們需要從翻譯的基本特性來總體分析文化詞的英譯,從而有助于漢語文化詞的成功英譯。
個性和共性是文化的兩個特有的表現,民族性說的就是文化的個性表現。不一樣的民族擁有不一樣的歷史環境和人文環境,這就造就了不一樣的文化差異,他們不會通過統一的角度來看待同一件事,他們也具備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就有著很大的差別。語言和文化是相輔相成的,他們的關系密不可分。文化是翻譯過程中特別重視的一種底蘊乃至技巧,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翻譯出來的語言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翻譯也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平臺和視角。這一平臺卻受到了文化背景因素影響,它撿起來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是有一定價值的。
2. 翻譯之文化特性
許鈞在《翻譯概論》里說過,翻譯并不僅僅是一種純語言層面的活動,更是一種文化實踐(2009:4)。在這個基礎上,許鈞總結了翻譯一共有社會性、文化性、符號轉換性、創造性和歷史性五大特性。
第一,翻譯是具有社會性的,翻譯理論家讓·皮特斯指出,作為一種人類特有的現象,翻譯活動理應被包括在對于社會運行的整體研究之中(張露,2001:2)。所以翻譯這項活動是需要與社會生活、文化聯系起來的,共同討論社會環境對翻譯活動的影響。第二,翻譯是有文化特性的。民族文化的一個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語言,語言能夠影響到一個民族的社會習俗、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因素,然而翻譯作為不同語言間進行交流的載體必然會含有文化性。第三:翻譯具有符號轉換性。新的詞匯具有某種意思,那么它就是“符號”,開始融入本民族語言的符號系統中。每種語言都是一個符號系統,然而原文在被翻譯成譯文的時候就是在解碼和重新編排的過程,這就是符號的轉化特性。翻譯首先要正確理解原文的意思,然后才能通過另外一種語言來表達原文的意義。理解錯誤,譯文不可能正確。第四,翻譯具有創造性,也就是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譯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在眾多的表達方式里面挑選一個最合適的表達方式,然后通過原文的構架等盡可能再現原文的意境、風貌和內容等。第五,翻譯是有歷史性的,受歷史和時代的限制,不同譯者對同一文本的翻譯是不同的。譯者需要顧及翻譯的歷史性,把當前的歷史環境還原到原文中,盡量做到不讓譯文與時代脫軌。
3. 漢語文化詞語英譯
3.1 社會性
翻譯是具有社會性的,翻譯理論家讓·皮特斯指出,作為一種人類特有的現象,翻譯活動理應被包括在對于社會運行的整體研究之中(張露,2001:2)。所以翻譯這項活動是需要與社會生活、文化聯系起來的,共同討論社會環境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譯例一:
“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幺愛三四五’了”。史湘云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譏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才現在我眼里”。
楊憲益譯文:
Naturally I’ll never come up to you this life time, I’ll just pray that you marry a husband who talk like me, so that you hear nothing but “love” the whole day long. Amida Buddha! May I live to see that day.
霍克斯譯文:
I shall never be a match for as long as I live. Xiang-yun said to Dai-yu with a disarming smile,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 marry a lisping husband, who that you have “ithee-with” “itheewith” in your every minute of the day. Ah holy name! I can see that blessed day already before my eyes.”
原文反映黛玉和史湘云之間的斗嘴,整段話俏皮活潑。楊憲益先生事先有對“愛”和“二”作過標注,對這一段的翻譯偏向于中規中矩。而霍克斯的譯文用了一些咬舌音,較好地反映了原文的諧音特點與當時社會的說話方式,二者的翻譯都是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的結果。
譯例二:
民俗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是傳統文化的積淀,是代代相傳的文化現象。肢體語言是民俗的具體表現形式,它同民俗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民俗對應不同的肢體語言,雖然歷史逝去,卻不會阻止那個歷史背景下的肢體語言流傳下來并為人們使用。他們從民俗中累積而成并存留了下來,即使很多使用他們的人并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起源。例如“matzo”這個詞,指的是張開手掌,伸向其他人的臉的姿勢。這個姿勢在中國人看來沒有惡意,但是在Achaean人眼里是一個極其無禮的侮辱的手勢。它起源于拜占庭時期,人們在犯人臉上扔污物的侮辱動作。現代希臘人做這個動作來表示一個張開的空的手掌,但是侮辱性的含義沒有改變。
3.2 文化性
翻譯是有文化特性的。民族文化的一個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語言,語言能夠影響到一個民族的社會習俗、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因素,然而翻譯作為不同語言間進行交流的載體必然會含有文化性。
譯例一: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譯文一:窮得像教堂里的老鼠
譯文二:窮得像叫花子/一貧如洗
在中國,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較少,對教堂的了解也不多,如果把“church mouse”直接翻譯成“教堂里的老鼠”就不能讓讀者明白其中的意思,而譯成“叫花子”才是中國人了解的意向,使讀者明白其表達的窮的程度。
譯例二:
歐美信仰的是基督教,所以有不少詞匯包括他們的節日都與《圣經》和基督教有關,如a covenant of salt(不可背棄的盟約),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家徒四壁);較之,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佛教和道教是分不開的,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佛法無邊。再有一些如“武術”wushu,“功夫”kung fu,“扭秧歌”yang ko,這些都是具有民間的特色文化。
譯例三:
“童養媳”
“child wife: girl raised from childhood to be wife of son of family”
童養媳,又稱“待年媳”“養媳”,就是由婆家養育女嬰、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結婚。童養媳在清代幾乎成為普遍的現象。童養的女孩年齡都很小,有的達到了清代法定婚齡,也待在婆家,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習俗,翻譯的時候就加了一個注釋去解釋child wife以便更好地去對這個詞語進行理解。
3.3 符號轉化性
新的詞匯具有某種意思,那么它就是“符號”,開始融入本民族語言的符號系統中。每種語言都是一個符號系統,然而原文在被翻譯成譯文的時候就是在解碼和重新編排的過程,這就是符號的轉化特性。翻譯首先要正確理解原文的意思,然后才能通過另外一種語言來表達原文的意義。理解錯誤,譯文不可能正確。
譯例一:
“兩岸關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aiwan Straits”
“兩岸關系”這個新詞實際上指臺灣海峽兩岸關系,也就是大陸與臺灣間的關系,故英譯時,不能只簡單地譯為“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而應稍作解釋,補譯為“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aiwan Straits”
譯例二:
“要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he real economy”
翻譯語言的符號轉換性需要重視的是民族習慣,盡量做到不讓讀者誤會。虛擬經濟是個新的概念,國外的經濟學家實質上并不太認可把虛擬經濟用在金融體系或者金融活動中去。在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之后,國外的新聞報道也經常提到the real economy(實體經濟),但是像紐約時報和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等權威媒體從來沒有出現ficticious economy的提法。因為在紐約和英國,the financial sector金融部門才是和實體經濟the real economy相對應的。the virtual economy在英語里面確實是存在的,但是這個是跟虛擬經濟沒什么關系的一種說法,而是用來形容網絡游戲里面虛擬世界的經濟的。所以,在提及或者翻譯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提到“要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就應該是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he real economy而不是the relations between virtu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這樣的話主要使用英語的讀者就不會困惑,網游里面的虛擬世界中的經濟怎么會對現實世界影響如此巨大。
3.4 創造性
翻譯的創造性,即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譯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在眾多的表達方式里面挑選一個最合適的表達方式,然后通過原文的構架等盡可能再現原文的意境、風貌和內容等。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指出:“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者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包惠南、包昂,2004:9-13)。
在西方,所謂的“創造性的青春期”說的就是翻譯。翻譯人員的創造性叛逆是語際轉換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實在難以進行直接的語言轉換或者文化傳遞的條件下,翻譯人員根據翻譯的目的,超脫語言的制約,突破歷史文化差異造成的隔閡,實現對原文的高度重視的一種翻譯策略(張德鑫,1999)。
譯例一:
“A beautifully situated park on the lake’s shore provides a perfect spot to savor an ice cream while watching the boats darting about on the bay or the exciting arrival of the famous M/S Mount Washington as she docks nearby.”
“公園坐落在湖邊,風光秀麗。在那兒,你可以一邊品嘗冰淇淋,一邊觀賞湖灣里的游艇飛也似地穿梭往來;當著名的華盛頓山號游輪剛剛在附近的碼頭靠岸時,你會看到那些興奮的游客熙熙攘攘地上岸。”
譯者將這個句子的主句A park provides a spot提出,把其他修飾語譯成5個獨立的主謂結構句,既符合漢語的語法規則,又使讀者明白易懂,不失為一個佳作。
譯例二:
“Ulvi is a young, cinematically handsome man.”
“奧爾威年輕、英俊,賽過電影明星”
普通讀者根據字面翻譯得到的是“奧爾威很年輕,而且如電影里的演員般帥氣”,這樣的譯文未嘗不可,但卻不免顯得啰唆,就不如譯者的翻譯:奧爾威年輕、英俊,賽過電影明星。這樣一來,讀者是不是更能體會到奧爾威有多么英俊帥氣呢?
3.5 歷史性
受歷史和時代的限制,不同譯者對同一文本的翻譯是不同的。譯者需要顧及翻譯的歷史性,把當前的歷史環境還原到原文中,盡量做到不讓譯文與時代脫軌。
譯例一:
“Queen’s English”——《麥田的守望者》
“標準英語”
意譯法的特點是以目標語為導向,用規范的目標語語言將原文本的意思表達出來,注重譯文的流暢,意譯法不再像直譯法那樣極力地保留原文本的句子結構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了更符合目標語的語言習慣而改變原文本的結構和修辭手法。Queen’s English如果直譯就是女王的英語的意思,這樣會有些不妥而且也使得語句上下也不順暢,所以就采取了意譯法將其譯為“標準英語”。
譯例二:
“It was cold a witch’s teat”——《麥田的守望者》
“天氣冷得邪門”
由于21世紀的讀者已經對美國的社會文化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就偏向于閱讀的流暢性。
4. 漢語文化詞語英譯的意義再生
文本的多義性或歧義性,對原文中的言外之意或言外之味的傳達之難做了簡要分析,歸納起來有兩點:原文的多義、韻味、情調創造了一個寬闊的閱讀空間,它給譯者提供了多重的閱讀和闡釋的可能性,這種多重的可能性的存在正是文學作品的價值之一。譯者的任務是要調遣譯入語或目的語所提供的語言手段,著力去建立一個相應的閱讀空間,但從實踐的角度看,這種閱讀空間的重建有著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對原文可能提供的眾多意義,譯者出于表達的需要或由于多種原因的局限,往往選擇其中的一種意義,即他自以為準確的意義加以傳達。這樣一來,在理論上便縮小了原文本的閱讀空間。在事實存在的這些困難面前,到底如何既傳達原文字句的意義,又傳達原文含蘊未吐的意味呢?應該說,作者有意識地創造元文本豐富多義的想象空間,本身是一種創造,每一個多疑的詞句的聚合、每一個留給人以豐富想象的情景的創造,也是非常困難或具有挑戰性的,且這種創造是因人而異、千姿百態、變幻無窮的。我們在此不可能為傳達原文所創造的“義”和“味”提供一個萬能的方法,只能基于我們對意義的理解,再借助一些卓有成就的翻譯家在處理有關意義問題的實踐中所總結的經驗,提出以下幾點原則:
4.1 去字梏
如果我們在理論上明白了意義不是確定與唯一的,并認同維特根斯坦“意義即用法”的觀點,那么我們就會進一步領會到薩特所說的文本的意義不是每個詞的意義的簡單相加的深刻道理。在翻譯中,要正確把握每個詞的意義,必須細心地揣摩作者的意圖,全面地把握上下文的關系。總之,要在動態的語境中正確領悟字詞的意義。學外語者習慣了依賴字典,從開始學習外語就習慣于從課文的詞匯表所列的母語解釋中去理解外語字詞的意義,往往誤以為詞匯的意義是固定的。要破除字的桎梏,首先要破除流行的逐字對譯的習慣。去字梏,并不是去破除字的存在,相反,字詞的意義是一部作品意義的基礎。同樣的字和詞,在不同的作家筆下,通過不同的組合和上下文,會賦予他們不同的色彩和生命。
4.2 重組句
去了字梏,就必然涉及原文的句子。
楊絳認為:“翻譯包括三件事:選字,造句,成章”。選字需經過不斷的改換,得造成了句子,才能確定選用的文字。成章當然得先有句子,才能連綴成章。所以造句是關鍵,牽涉到選字和成章。”
傅雷特別重視翻譯中“重組句”這一環節。在《致林以亮論翻譯書》中,傅雷就明確談到了短句與長句的翻譯問題。他認為短句的翻譯難在傳達原文的語氣、情調與氣氛,而長句的翻譯難在“重心的安排”。要解決這兩難,就應該依靠句法,多加句法的變化。
楊絳在《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一文中對組句的理論依據、困難及方法作了系列的分析與介紹,尤其是她根據實例將組句的機理、步驟和效果作了透徹的揭示,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4.3 建空間
在翻譯特性視域下漢語言文化詞語翻譯中,譯者不但要著重將原文的意義確切地表達出來,還要考慮讀者能不能通透地理解原作的深層韻味,通常譯者需要把原文中隱含的意義也要直接地表露出來進行傳達,所以原文的立體結構空間就變成了平面的結構空間,原文中隱晦復雜的意思也就變得更加透明,這樣一來,譯文往往就沒有原文立體豐富,讀者的想象空間也大大縮小。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譯者怎樣克服這樣的障礙呢?只有通過智慧地翻譯而不是去復制原文,機械性地翻譯原文,譯者需要了解原文的歷史背景和文化關系,在此基礎上再把原文放入這個語言關系空間中,找出原文的主旨,在翻譯的時候,重組這些語意并進行和諧的空間改造,既表達出了原文的含義也把蘊含在文章中的深層意義也表述出來,重新賦予譯文生命。
5. 結論
通過從翻譯的五個特性:社會性、文化性、符號轉化性、創造性和歷史性入手,本文采用舉例證明的方法來探討英語文化詞語的漢譯。本文發現翻譯是受到社會、文化、歷史、譯者主體性等條件制約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因此,我們進行翻譯活動時,一定要注意以上幾方面的影響,使翻譯真正發揮其跨文化交際的橋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