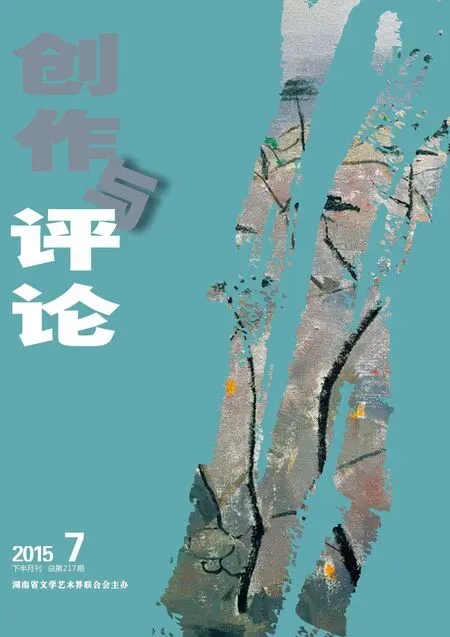“濰河灘”的蒼茫世界
○ 王士強 韓宗寶
“濰河灘”的蒼茫世界
○ 王士強韓宗寶
主持人語:
韓宗寶是70后詩人的重要代表。這些年他通過詩歌建構出一個重要的意象:“濰河灘”。濰河灘可以是實寫,有著宗寶家鄉的影子,山水、人事或可坐實;但濰河灘又是宗寶的精神寄托之地,好比藐姑射之山和桃花源。王士強于詩歌素有研究,也非常了解韓宗寶的創作情況。在這篇對話中,王士強居于提問者,他圍繞著宗寶的經歷和創作情況發問,循此可了解韓宗寶的創作情況和志向。
李德南劉濤
韓宗寶
1973年出生,山東諸城人,現為山東膠州市文聯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著有詩集《一個人的蒼茫》《韓宗寶的詩》等。曾參加詩刊社第25屆青春詩會、第七次全國青創會、《人民文學》第二屆新浪潮詩歌筆會。

王士強:宗寶兄好,我們聊聊你的詩歌創作。地域和地域文化對于個人的寫作來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你的出生地有著怎樣的地域文化,這種文化對你的個性、性格有怎樣的影響?
韓宗寶:山東是孔孟之鄉,禮儀之邦,號稱齊魯大地。齊魯文化淵源流長,齊文化兼容并蓄,以儒、道、陰陽家學說為主,遵天時,尚功利,重形勢。魯文化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家文化,孔子“仁者愛人”的命題,突破了階級的、種族的、國家的、地域的局限,他的“愛人”說的是“人類之愛”。
我的出生地是山東的諸城。春秋戰國時期,諸城恰好處在齊國和魯國的交界之處,有時屬齊國,有時屬魯國。因為地理位置的關系,諸城人兼受齊文化和魯文化兩種文化的影響。諸城這個名字,起源于虞舜生于諸馮,因地處魯國之東,所以也被稱為東魯。孔子弟子和女婿公冶長就是東魯人,傳說他懂鳥語。孔子卒后,公冶長回到故里,在東魯一帶繼續傳授老師孔子的儒家學說。漢世瑯邪諸儒、唐宋密州名賢,皆承其志而大興講學、治學、讀書之風。儒家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開始在諸城占據上風。蘇軾任密州太守時,在這里寫下了《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江城子·密州出獵》等千古名篇。因為蘇公的倡導,當地讀書求知之風更盛。蘇轍到密州看望蘇軾時感慨地寫下“至今東魯遺風在,十萬人家盡讀書”這樣的詩句。
應該說是這種“東魯遺風”,培養了諸城人尚仁、尚禮、尚義、尚信、尚學的品質,形成了諸城人淳樸厚道,與人為善,自強不息的鮮明個性。“東魯遺風”后來逐漸在當地成為了讀書之風、治學之風和文藝創作之風。《水經注》中提到的濰水,流經諸城,在濰河的兩岸,受“東魯遺風”的影響,涌現了宋代《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李清照的丈夫、金石學家趙明誠,清代東閣大學士、書法家、宰相劉墉(劉羅鍋),《續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四庫全書》總裁竇光鼐,現代文學史上的世紀詩翁、新詩的巨擘臧克家,著名作家王統照、王愿堅、王希堅、陶鈍、孟超,導演崔嵬、演員李仁堂、中共一大代表王盡美等一大批的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
我們村叫韓家莊,濰河從我們村東經過。小時候我經常隨父親去濰河網魚,摸蛤蜊,游泳。我們村向西南五里的地方,發生過歷史上有名的濰水之戰。當年韓信打敗楚將龍且的地方,現在修了一個小型水電站,叫韓信壩。韓信壩旁邊的村古縣,是我母親的村子。當代作家峻青就是在這條濰河邊寫出了他的名作《黎明的河邊》。朦朧詩人顧城童年時隨著父親顧工下放到山東農村,也是在濰河邊的河灘上邊放豬,一邊寫出了很多早期的詩歌。作家莫言多次到過諸城,他的高密東北鄉,與濰河相去并不遠。在諸城大地上,“東魯遺風”是一種開放式的文化傳遞,這種傳遞不是雞生蛋,蛋生雞,而是融入到了濰河兩岸的山水大地和風土人情之中,它無形有靈,就像濰河之水,生生不息,綿綿不絕。我個人在性格和創作上的成長,就得益于在故鄉大地薪火相傳的“東魯遺風”這種文化根脈。
王士強:應該說你是從關于“濰河灘”的書寫而廣為人知的,濰河灘差不多成了指代你詩歌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符號。你是怎樣形成塑造這個詩歌意象的意識,并使它逐漸清晰、成形、成長的?
韓宗寶:1990年代末,在小城膠州,以臧彥鈞、宋方金和我為主,有一個小小的文學沙龍,2000年后張銳強也加入進來,那時我們幾個文學青年,聚在一起,談論的最多的一個作家是莫言。莫言讓我們在寫作上,有種親近感,那是一種地域和文學血緣上的親近。莫言的作品如《透明的紅蘿卜》我們很容易地就可以進入其中,轉而在自身的寫作中進行效仿。當時還有一個我們都喜歡的作家是陳忠實,他的《白鹿原》我們推崇不已。我當時曾立志要寫一部類似的長篇小說,名字就叫《濰河灘》,為了向陳忠實的《白鹿原》致敬。因為我的這個想法,很長時間里一直受到他們幾個的揶揄。事實上我豪情壯志要寫的長篇小說叫《濰河灘》,最終也只有一個幾萬字的開頭,就再無下文。小說沒有寫成,但是我寫下了大量關于濰河灘的詩歌。
我當時在詩歌中開始寫濰河灘,現在想來應該是受到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和陳忠實的《白鹿原》的共同啟示。濰河灘,第一次讓我有了一種野心。我一直以為,在生活中不應該有野心,但一個優秀的作家,在寫作上,必須要有自己的野心。建立高密東北鄉王國的野心,成就了莫言,一部《白鹿原》成就了陳忠實,而建立濰河灘世界的野心,則成就了作為詩人的我。
濰河灘第一次面世,是2005年《歲月》雜志的潘永翔老師在第1期發表了我的組詩《濰河灘》。隨后,2006年《花城》雜志的朱燕玲老師在第3期大篇幅地推出我的濰河灘系列組詩《一個人的蒼茫》。2007年《詩刊》的李小雨老師在上半月刊第2期的頭題發表了我的組詩《一個人的蒼茫》。2008年《詩刊》上半月刊又在第2期發表了我的組詩《濰河灘》。2009年11月我憑借組詩《一個人的蒼茫》參加了詩刊社的第25屆青春詩會。《星星》詩刊的梁平老師,《天涯》雜志的李少君老師、還有楊克老師等也陸續對我的灘河灘系列作了重點推介。從此我的濰河灘漸漸為人們所知。濰河灘也成了我寫作的根據地,成了我現實和精神的雙重家園。
我一點一點地在紙上勾勒濰河灘的蒼茫和它廣闊的氣象。說實話,我并不是有計劃地或者預定地去寫濰河灘,我沒有設置它。我在寫作中不由自主地向著濰河灘靠攏,更多的是源于一種召喚,一種牽引,一種莫名的沖動。對濰河灘的寫作,是出自本心。我是無意中來到了我的濰河灘的。它似乎一直在那里等著我,等我擦去它身上的遮蔽與灰塵,走近它,擁抱它,與它融為一體。我個人內心的蒼茫,從此和整個濰河灘的蒼茫交織在了一起,變成了一種更大、更厚重、更復雜的蒼茫。
王士強:“濰河灘”對你而言可能是和過去、童年、個人經歷相聯系的,有很多美好、值得珍惜的東西存在,這也是能夠喚起很多人的共同經驗、記憶的,體現了一種緩慢、美好、自足的美學形態。對你來說,“濰河灘”意味著什么?
韓宗寶:從2004年夏天開始,我瘋狂地寫關于濰河灘的詩作,我打算把我自己的生命、才華和感情,全部用在對濰河灘的不斷的重寫中。面對濰河灘,我時常覺察到自己的某種難以言說的孤獨。也可能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我才想通過對濰河灘的一次次的書寫,尋找一種靠近母性的東西。濰河灘讓我獲得了深深的寧靜感和安全感。關于濰河灘的詩歌是我對生命和生活的切身體驗。地理意義上的濰河灘,是我最熟悉的土地,現在它也成了我個人的精神家園。有的讀者,在我的詩歌中看到的更多不是濰河灘,而是我的形象和身影。這樣的讀者會讓我覺得親切。事實上,不是我在寫“濰河灘”,是“濰河灘”在一遍一遍地寫著我。“濰河灘”給了我底氣,讓我變得堅定和強大起來。現在對我而言,“濰河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濰河灘”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母親,是我的情人,也是我的愛人。濰河灘甚至就是這個世界。它已經完全超越了某個具體的地域。不但是一個巨大的實體存在,也是一種精神的形而上的隱喻和象征。
王士強:不過,關于“濰河灘”這一類鄉村、鄉土意象的書寫可能也會有讓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比如說,它和現在的生活是一種什么關系?它能否與現實發生有效的關聯,產生實際的作用?“濰河灘”及其美學形態在未來的可能性前景是怎樣的?關于這些問題你有怎樣的思考?
韓宗寶:現在好像有很多詩人,已經羞于繼續提出自己早年的詩歌印記,從此避免被歸類。確實有一段時間,這類標簽在詩歌里非常泛濫,大家一哄而上,大量的雷同和模仿,消解、敗壞了讀者的胃口。就我有限的視野,江非是比較早地在詩歌中提出一個地理意象的,他的平墩湖現在已經廣為人知。我知道他的村莊名就叫平墩湖,另外他還有向梭羅致敬之意,不過在他那里,平墩湖并不是一個湖,而是村莊和土地。后來有更多的詩人命名了自己的故鄉、出生地或精神家園,給自己貼上了一個標簽。良莠不齊的標簽式地域寫作,成為了中國詩壇近幾年一種獨特的現象。但我至今覺得,命名并不重要,一個意象本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意象的挖掘和深度呈現,用自己的生命全力赴之地,在不斷的書寫中一再地刷新這個地理意義上的名詞和概念,賦予它更多更豐富更新穎的含義,從而不落窠臼地和別的地理名詞與概念區別開來。
事實上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在描繪自己所最熟悉最熱愛的地方或者故鄉。梵高的阿爾,史鐵生的地壇,賈平凹的商州,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的馬孔多小鎮,梭羅的瓦爾登湖,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蕭紅的呼蘭河,孫犁的白洋淀,那是他們精神的根據地。沒有精神根據地,盲目地胸懷世界,表達的可能就只會是一些蜻蜓點水一樣零碎而浮泛的公共感嘆。好的作家,必須有一個用一生來持續地辨析和陳述自己的地方。這個地方要能真正容納他的智慧、情感和心靈,能讓他激動,讓他愿意付出時間、精力、智慧和愛去書寫。可能因為屬牛的緣故,在寫作中我經常像牛一樣對往事和過去的經驗、記憶不斷地進行反芻。我一直避免空泛的寫作,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接地氣,有生活,是我對自己最基本的寫作要求。我詩歌中的很多比喻其實并不是修辭,而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確鑿聯系。
優秀的詩人腳下應該有一個深厚的根系,內心應該有一個強大的詩歌之胃。我一直努力讓自己的寫作從日常生活、從故鄉和故土得到確切的支持。我從來沒有在詩中外在于自我,我所寫下的詩歌作品是從我血管里流出來的鮮血,是從我眼眶里流出來的淚水。它們帶著我個人的體溫、指紋和嗓音。我一直以最個人的方式,接近著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實。
我從未從技術上考慮過“濰河灘”及其美學形態和它的前景。我只是本著自己的內心,同它相互印證。寫作的過程,是返鄉的過程,也是自我認識的過程。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對自己所知甚少。而我要做的,就是寫出自己,寫出“濰河灘”的過去,現在的萬事萬物,寫出它在漫長的時光和廣闊的時代中與眾不同的樣貌,為人們認識它、理解它,提供一份個人意義的切片和樣本。
王士強:從你之前的文章知道,你開始寫作的時間是比較早的,閱讀也比較廣泛。那么,你覺得自己從一開始的模仿性寫作到真正自主性、創造性寫作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在寫作過程中你受哪幾位詩人的影響比較大?
韓宗寶:說到我最初的文學創作,要提到我的一個詩歌兄弟宋永亮。我和永亮的相識和友誼要上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那是1988年,對于中國的文壇和詩壇,那是最熱鬧,也是最有活力的年份。先鋒小說家和先鋒詩人們,用他們的作品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學風暴。而永亮和我,正是在這種影響下,被一種巨大的力量裹挾著懵懵懂懂地走進了文學。永亮家中的藏書甚為豐富,在永亮的家中我讀到了《詩刊》《詩神》《詩歌報》等這些中國一流的詩歌期刊,也是在永亮的家中我知道了北島、顧城、舒婷、楊煉、歐陽江河、昌耀、于堅、韓東、海子、西川等這些中國詩壇上非常耀眼的名字。也是因為永亮,我得以認識了當時在諸城現代詩歌寫作最前衛的青年詩人韓宗夫。我的寫作得益于永亮和宗夫甚多,應該說是他們讓我對詩歌有了一個不同于當時的教科書的全新的認識,讓我一開始就接觸到了現代詩歌最本質也是最內核的那種東西,這為我的以后的詩歌寫作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后來,就是到膠州之后,同詩人、小說家宋方金我們兩人有很多在創作和思想上的交流。方金的很多觀點和觀念至今讓我受益匪淺。我一直把他視為我的良師益友。現在他在北京,但基本上每年,我們都會聚一下。喝著茶或者酒,談論這個世界和我們熱愛的文學。
在我的寫作過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詩人有李白、杜甫、王維、蘇軾、昌耀、海子、于堅、歐陽江河、西川、江非等,國外的詩人有博爾赫斯、里爾克、布羅茨基、希尼、史蒂文森、特朗斯特羅姆、沃倫、默溫、弗羅斯特、斯奈德等。
王士強:你的詩有著比較明顯的抒情性特征,以情感的真摯、深沉、感人而取勝。抒情作為一種藝術手法由來已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抒情、言志一直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重要傳統。但是現在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抒情”的現代性不足,更多的是表達一種古典式、明晰、單一的情感,己不足以表達現代社會、現代人的復雜境遇和復雜經驗?你怎么看詩歌中的“抒情”,它有怎樣的長處和不足?你在自已的詩歌寫作中持怎樣的抒情立場?
韓宗寶:屈原的《離騷》是抒情,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抒情,杜甫的《春望》是抒情,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也是抒情。我不以為這些抒情是單一的,簡單的。古典式抒情同樣是可以很復雜的。李商隱“滄海月明珠有淚,只是當時已惘然”描述的情感足夠復雜。詩歌的現代性和抒不抒情,并沒的必然的聯系。再現代的詩歌,也要表達情感、愛恨和立場。現代人復雜的人生境遇和人生經驗,同樣可以用簡單的抒情來表達。相應的復雜能表達復雜,但是簡單也同樣能表達復雜。而且用簡單來表達復雜,從技術和難度上,要比用復雜表達復雜難的多。
抒情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一個詩人把抒情看成簡單的事,那他就是小瞧了抒情。汪曾祺的小說里的抒情,看似平平淡淡,但卻體現和傳達出一種更加復雜的人生況味。現在很多人,對抒情有偏見,以為抒情就是一個拖長調的“啊”字,就是對祖國,對母親,對故鄉,對愛情的單一歌頌。其實遠遠不是。抒情,有時候并不在抒,而在于隱忍,有所謂不抒之情。克制,沉默,內斂,以及古人的“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是抒情比較高的境界。還有一種重要的抒情是借景抒情,只說景,不說情,但情全在景中,像錢起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我認為抒情無關乎詩的現代性與否,關鍵看你是如何抒,抒的是怎樣的情。
我認為一個優秀的詩人不但要有良好的對語言的控制力,更要有對內心情感和寫作的語調的控制力。詩人,必須懂得控制,精于控制,善于拿捏語言和情感的分寸感。一個詩人如果能控制了自己的情感和語調,就能做到在寫作中收發由心,收放自如。我渴望那種如魚在水,如鳥在空般自由自在的寫作。
我在自已的詩歌寫作中的抒情立場是誠懇,自然,率真。
王士強:你關于過去、關于鄉土、關于農業文明的書寫讓人印象深刻。不過,在詩歌的及物性、現實性方面可能也會讓有的讀者感到不太過癮。你有沒有更多地面對“現在”,對現實、對時代進行“正面強攻”的想法?你認為詩人與他所處的時代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韓宗寶:我以為一個優秀的詩人應該具有良好的處理當下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能不能處理日常生活題材,也是檢驗一個詩人能力的試金石。城市化進程中,很多通過各種方式涌進城市的人們,往往羞于承認自己的鄉村背景,煞費心機地擦去腳上的泥土,身上的泥土,讓自己也成為一個“城里人”。這是骨子里的自卑。由于我寫了大量的關于濰河灘的詩歌,以致于很多人將我稱為一個鄉土詩人。其實我從來沒有用鄉土限定自己,寫鄉村也好,寫城市也好,都一定有當下意識才算好。我有的作品雖然看似寫的不是當下,但里面有著深刻的當下意識。《一頭蒙昧無知的豬》和《樹林》是我鄉土詩歌中,對現實和當下正面強攻的。我也有很多鄉土之外的,另一種對現實、對時代進行“正面強攻”的作品比如《出獄》《審判》《夜鶯》《廣場》等。可能我寫作中的濰河灘的體積偏大了一點,很多讀者忽略了這一類詩歌。當然也有人注意到了這些“另類”作品,好心地提醒我,暗暗為我擔心。對此我心存感激。但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定要有敢于“冒犯”時代的勇氣和膽識。杜甫所倡導的批判現實主義詩歌精神,永遠不會在當代詩人身上萎縮。
詩人與他所處的時代,要有一種適當的疏離感,不盲從,要保持自我的清醒和人格的獨立。詩人要遠離被動和妥協。一個好的詩人,應該獨立而不是附庸于時代,詩人應該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堅忍的擔當意識和真正的悲憫情懷。
王士強:你都做過什么工作?你現在的工作具體是做什么,這是詩歌帶給你的回報么?你的工作和詩歌寫作之間有怎樣的關系?
韓宗寶:我的經歷很簡單。高中畢業后參軍入伍,當時在農村的孩子,除了考學,就只有當兵這一條出路。我在部隊呆了十三年,是炮兵,干過炮手、瞄準手、司務長。2004年所在部隊撤編,就轉業到了地方。因為喜歡文學被分配到膠州市文聯。至今我還在文聯。這個工作談不上是回報。因為轉業時大多人想去的單位是公檢法這類有著實實在在的行政執法權的單位,也只有我這樣癡心于文學的人,才會選擇文聯這種清水衙門。我現在的工作和詩歌寫作之間,關系不大。詩歌寫作主要還是用業余時間。我們文聯人手少,但下面有20多個文藝家協會。作為政府聯系藝術家的橋梁和紐帶,我們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引導組織和協調20多個文藝家協會進行藝術創作、展覽、交流和采風。
王士強:你所生活的膠州是一座怎樣的城市,“膠州”和“濰河灘”是怎樣的關系?你怎么看城市與鄉村的未來發展?
韓宗寶:1990年代我因為當兵,來到膠州。膠州是青島的下面的一個縣級城市,“濰河灘”屬于濰坊。濰坊以前稱濰縣,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曾做過縣令。揚州八怪中唯一的北方人高鳳翰就是膠州人。古有金膠州、銀濰縣之說。膠州的大白菜全國有名,魯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曾提到過。
近二十年來,我一直在“膠州”和“濰河灘”之間穿越奔走。我成了兩地文學的一個橋。濰河灘上的詩人,像韓宗夫、黃浩、宋永亮、管清志、王瑞嫻,因為我在膠州,經常過來喝酒聊天,而膠州的詩人作家也常去濰河灘采風,像張銳強、宋方金、劉棉朵、李林芳、陳亮、王小玲、張金鳳、張書江、魏兆江等。膠州的作家和詩人群非常齊整,已經成為一個現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有6人,參加過青春詩會的有2人,入選過中國作協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有2人,山東省簽約作家3人,青島市文聯簽約作家2人。就一個縣級市來說,膠州的文學氛圍和文學實力,還是值得稱道的。
關于城市與鄉村的未來發展,我以為城鎮化是一個大的趨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農村的空巢現象會越來越嚴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土地,走進城市。在中國農耕文明,逐漸將被工業文明所漸漸替代。
王士強:到目前為止你的詩歌創作有沒有階段性和變化,如果對自己二十多年的創作時段進行分期的話,你覺得應該怎么分?
韓宗寶:事實上,我是一個在寫作的黑暗期呆的特別長的人,大約從1988年到2004年,可以視為一個時期,是我寫作的苦悶期和青春期。2005年到2012年是一個時期,是我創作的高峰期和自覺期。2013年到現在,是一個時期,是我寫作上的沉潛期和澄明期。可以用我的三首詩分別代表寫作的這三個時期,《作為西瓜》《挖土豆》《運草車》。
王士強:作為一名70后詩人,你對“70后”這一詩歌概念有什么看法?70后一代是否面臨著一些獨特的困境和問題?如果和80年代的“朦朧詩”和“第三代”詩人成名時相比,70后的年齡已經不小了,你覺得70后詩人是否已經寫出了他們重要的、足以進入詩歌史的作品?
韓宗寶:70后這個概念,最早是陳衛提出來的。后來黃禮孩、沈浩波等詩人對70后詩人這個概念,又做了很多工作。現在看來,還是頗具意義的。它向前承接了第三代,向后啟發了80后和90后,60后和中間代,也同70后這個詩歌概念的提出直接有關,它讓以年代劃分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霍俊明兄稱70后為尷尬的一代,他在《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一書中,對70后這一代人詩人身上所獨有的尷尬、焦慮、懷舊、感傷和自我救贖的描述,我以為是很精準的。
70后詩人現在和1980年代的“朦朧詩”和“第三代”詩人成名時相比,已經毫不遜色,江非、朵漁、劉春等70后詩人,已經寫出了超越前輩的無愧于時代和自身尷尬境況的厚重而開闊的經典詩歌文本。70后優秀詩人目前已經有了一個長長的名單:江非、朵漁、劉川、劉春、沈浩波、宇向、孫磊、李小洛、燈燈、玉上煙、邰筐、津渡、軒轅軾軻、魔頭貝貝、譚克修、胡續冬、姜濤、盛興、阿翔、馬累、辰水、尹麗川、黃禮孩、徐俊國、李寒、霍俊明、簡單、李潔夫、辛泊平、陳小三、周斌、高鵬程、海嘯、商略、陳亮、張小美、冷盈袖、廖偉棠、蔣浩、王琪、劉棉朵、蘇淺、巫昂、扶桑、余小蠻、夏雨、白瑪、周公度,等等,但目前對70后詩人作品的經典化還遠遠不夠,還有很多優秀的70后詩人,并沒有引起詩壇和評論界足夠的重視。
王士強:寫作其實是一件孤獨、困難的事情,既要避免重復別人,也要避免重復自己,關于以后的寫作你有怎樣的期許和計劃?
韓宗寶:我把寫人作為自己詩歌寫作的唯一目的。寫出人生命的本色和底色,表現出時代境遇中的復雜人性,是我的追求。通過寫人,寫人的生存面貌,內心的面貌,揭示整個時代的面貌和一個國家的集體一代人的精神面貌與生存處境。我最近開始關注在生存處境不斷變化、時光的不斷磨損和世事的更迭中,某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所體現出的那種命運感。我期待自己能表達出在我的故鄉以及中國大地上所生活的人,他們的身心所經歷的內容,以及這內容所包含的歷史感和蒼茫感,我愿意用詩歌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光榮與夢想,樹碑立傳。
責任編輯張韻波
- 文藝論壇的其它文章
- 開放的學術對話平臺——讀“對話臺灣詩人”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