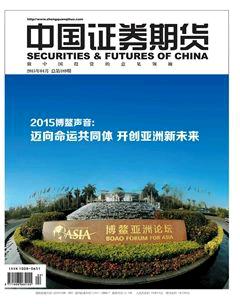揭秘醫療廢物利益黑鏈:護士衛生員參與買賣
魯偉? 高勝科
基層醫療點產生出大量危險的醫療廢物,經非法加工重新流入市場且全國蔓延,其安全隱患難以控制
成箱的注射器、輸液袋等醫療廢物,未經任何消毒處理,通過一套陳舊的加工設備,生產出一堆堆塑料顆粒。2015年3月,在湖南省邵陽市雙清區渡頭橋鎮肥馬石地段,一家非法回收、加工醫療廢物的“黑作坊”將以上情景呈現世人。
作坊位于渡頭橋村村級公路的一側,緊挨著豬圈。露天堆放的醫療廢物中,有的還帶有血跡。
加工廠內污水橫流,排水溝被染成白色,漂浮著不少塑料顆粒和瓶蓋。臨近的井水被污染,經常引發周圍村民的不滿。但作坊在當地已存在一年多時間。
這家作坊涉嫌非法買賣、加工醫療廢物。據《財經》記者調查,邵陽市的醫療廢物處置直到2011年才開始走向正軌,此前違規處置多年——市區的醫療廢物2011年之后集中處理;鄉鎮的醫療廢物遲至2013年才開始著手規范處置,像以上作坊違規處理醫療廢物的情況至今仍是普遍現象。
醫療廢物位居《國家危險廢物》榜首,具有直接或間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因含有害病原體,其毒性是普通生活垃圾的數百甚至上千倍,極可能成為疾病流行的源頭。
醫療廢物無人回收
“觸目驚心!”3月10日,在看到醫療廢物加工現場后,邵陽市雙清區檢察院檢察長張小林感慨道。邵陽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在現場稱重,包括醫療廢物在內的廢棄物超過3.75噸。
“黑作坊”負責人李光星,65歲,當地人,除加工醫療廢棄物外,他還養有約100頭生豬。事發后,李曾試圖通過“關系”,找邵陽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更改稱重數據,將3.75噸改至3噸以下——3噸以上構成嚴重的污染環境罪,最高可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負責督辦該案的雙清區檢察院人員稱,由于區環保局取證能力有限,醫療廢物的來源及加工后的去向等關鍵問題均未查清。李光星在接受調查時說,醫療廢物都是從附近廢品收購站購進的。其子李建國也稱,醫療廢物是以每斤1元錢的價格從廢品站購得。
據記者調查,廢品站的上游即為醫療機構。如果是大型醫院,一些醫療廢物上還會寫有醫院名稱。就在5個月前,山東濟南歷城區村內的多個“黑作坊”被端后,執法部門按圖索驥,根據醫療廢物上面的醫院名稱,鎖定了濟南下轄的縣級市章丘市人民醫院等多家醫院。該醫院負責人在表示要加強管理后,無人被問責。
而小型醫療點和私人診所產生的醫療廢物,溯源很困難。3月17日,《財經》記者在雙清區隨機走訪了三家醫療診所,這三家均存在售賣醫療廢物的行為,可見邵陽鄉鎮醫療機構的醫療廢物流入廢品站的現象極為普遍。流入廢品站的醫療廢物有針管、注射器、輸液袋等塑料制品。
醫療廢物被列為危險廢物,位居《國家危險廢物》榜首。在國外,它也因“頂級危險”被稱“致命殺手”。國內科研文獻顯示,上世紀70年代,中國曾發生醫療廢物處置不當引起乙肝傳播流行事件。
2003年“非典”后,國務院出臺《醫療廢物管理條例》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買賣醫療廢物。要求各地專人負責制,對收集、貯存、運輸、處置全程嚴格監管,建設集中處置中心無害化處置,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買賣、加工醫療廢物。
但《財經》記者在當地的調查發現,醫療廢物的買賣、加工已經形成一條地下利益鏈。
廢品回收者一般按月到診所收購醫療廢物,針管和注射器的收購價約為1.2元/斤,輸液袋的收購價約1.6元/斤。鄉鎮醫療機構大多為私人所有,埋掉嫌麻煩,焚燒又怕影響自己健康,送到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處理需要花錢,而賣到廢品站卻能獲利,因此鄉鎮醫療機構售賣醫療廢物的情形普遍發生。
另一非法途徑是醫療廢物混入生活垃圾,經拾荒者之手,進入廢品站。河北秦皇島市創業者協會2008年曾對主城區海港區68家社區醫院、學校醫院、廠礦醫院和私人診所調查3個月。結果顯示,對醫療廢棄物的處理方法56%是“放置門口”,99%的醫療點沒有專人監督、負責醫療廢棄物的處置;98%的醫療點反映沒有專門機構對其醫療廢物回收。
“社區診所多把醫療廢物放在社區垃圾箱內,沿街的診所則使用黑袋子交給環衛工人。”該協會會長周健說。
更直接的渠道是醫護或勤雜人員參與買賣。邵陽市一家大型醫院的內部人士透露,一些有“銷路”的輸液瓶、注射器、塑制品,是經由護士轉交給衛生員,再賣給廢品回收人員,最終進入非法利用體系。衛生員每月有固定“補貼”。據其透露,這種事情在2011年之前的邵陽各大醫院屬普遍現象。
基層廣泛的盲區
《醫療廢物管理條例》規定,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應在一年內建成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8年后,邵陽市才建成該中心。
此前,一直是大醫院利用自有設備焚燒,小醫院深挖填埋。這兩種方法早被明令禁止。
按規定,尚未建立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之前,地方政府應制定過渡性處置方案,確保醫療廢物妥善處置。“邵陽這塊工作(醫療廢物處理)啟動較慢,以前做得確實不規范。”邵陽市衛生局黨委委員李邦銀表示。
2015年1月5日,環保部首次公開發布《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2013年261個大、中城市,大部分城市的處置率達到100%。
這一數據顯然不能反映基層醫療點和私人診所的現實。2011年之后,邵陽市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建成,日處理醫療廢物能力8噸。市環保局數據顯示,在2011年至2013年間,該中心處置率分別為72%、72%和78%。這意味著在邵陽市本級及各縣市有20%-30%左右的醫療廢物未被規范處理。
而全國97.8萬個醫療衛生機構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占93.9%。醫療廢物買賣失控的問題可想而知。
《財經》記者調查發現,很多偏遠鄉鎮上的私人診所將使用后的醫療廢物隨意丟棄;在部分農村,一次性注射器、輸液袋和針頭被四處丟棄,成為農村垃圾,甚至被兒童拾撿后當作玩具。
對醫療廢物的監管,主要與兩大體系有關:各地政府的衛生部門負責監控醫療機構的廢物收集、貯存以及相應管理制度實施。環保部門負責醫療廢物的運輸和集中處置的跟蹤監管。
但在邵陽,面對《財經》記者采訪時,雙清區環保局局長王鴻毅表示,不清楚該局在醫療廢物處置上有何種職責,“以前的重心都放在了工業污染的監管與防治上,醫療廢物不是重點”。
邵陽市、區兩級環保、衛生部門多位主管領導,對鄉鎮醫療機構的處置方式也多以一句“燒了吧”或“賣了吧”回應。
危險換來的利潤
一些非法加工醫療廢物的“黑作坊”,實際上是由廢品回收點直接變身的,因為粗放加工后的塑料顆粒售賣到塑制品生產企業,利潤更高。
邵陽市一位熟知塑制品市場的人士介紹,醫療廢物從源頭如按1元或1.2元/斤計算,加工成塑料顆粒賣給塑制品企業,每噸產品可獲利約4000元。山東濟南一批“黑作坊”在2014年10月被查獲時,每天可粉碎規模達30噸。
一些具有資質的地方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也參與了這種“不合法的生意”。2015年3月初,濟南歷城區環保局發現,濟南市集中處置中心的委托運營方——濟南瀚洋固廢處置有限公司未經任何環保許可、環評手續,從2013年起,私自將醫療廢物分揀,非法粉碎、加工成塑料顆粒,再賣給下游的塑制品加工者。
這些塑料顆粒最終可能制成塑料片、編織袋、玩具、瓶蓋、塑料盆等,并流至全國各地市場。這些未經任何衛生消毒處置的產品中,可能殘留大量的病菌、病毒,甚至放射性物質及化學毒物等,具有交叉感染、潛伏傳染、生物病毒性和腐蝕性。如果重復使用或再生利用,在人體毫無防備的情況下,會傳播攜帶病原菌,可能導致傳染性疾病的產生、流行,直接危害人體健康。這也是很多醫療用品均為一次性用品的根本原因。
作為醫療廢物流通鏈條的源頭,醫療機構為何不嚴格把關將其送入處置中心呢?
送入集中處置中心,醫療機構需要支付處置費。按邵陽市物價局規定,全市集中處置價格為每天1.9元/床。一些地級市更高,比如湖北襄陽市對有固定床位機構收費每日2.5元/床。很多醫療機構認為收費較高。以邵陽市第一人民醫院為例,2011年該醫院480張床位,當年處置費32.8萬元,此后床位逐年增加。2014年,該醫院與處置中心發生糾紛,處置中心一度停收醫院的醫療廢物,直至主管部門出面協調。
類似事件在邵陽時有發生,原因就在于很多醫院不愿按逐年增加的床位數相應增加這筆“需要醫院自行承擔”的費用,結果造成處置中心在邵陽各大醫院,實際只能收到50%-60%床位數的費用。
基層醫療機構更不愿也無力支付這筆費用。雙清區衛生局衛生監督所所長龔建軍估計,一個村的衛生室,如果將醫療廢物都交給處置中心,一年的費用在1500元左右,一個床位在20張左右的鎮衛生院,一年交給醫療廢物處置中心的費用要1萬元左右。
邵陽醫療垃圾集中處理中心,委托一家企業進行運營,該企業租賃處置中心花費了1276萬元,若足額收費,每年投資回報率在12%~13%之間,但實際根本達不到這個投資回報率。這家企業內部人士說,公司前幾年都是虧損狀態。
與集中處置中心簽訂合同的邵陽三縣鄉鎮衛生院,是由主管部門“強壓”的。為保障收費到位,鄉鎮衛生院在每年年檢時,就把費用先交給轄區的衛生主管部門,由后者轉交給處置中心。
依靠行政強制手段來推進鄉鎮醫療廢物處置,非長久之計。然而,邵陽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
收費價格與末端處置方案直接相關。國內處置基本全是焚燒方式,因此收取的床位費,就是根據焚燒技術測算的費用。
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介紹,末端處置的技術多樣化,可降低處理成本。在德國,對于感染性與非感染性的醫療廢物分類后,以高溫蒸煮和焚燒等多方式結合,可以實現更大的經濟性和環保性。其實,高溫蒸煮在醫療界已長期應用,但要在國內實施,首先必須在源頭上實現精細垃圾分類。
作為唯一合法出口的集中處置中心,也常常曝出環保問題。比如,山東濟南的處置中心自運行后煙氣排放長期超標,2006年被市環保局測出二英超標。一位廢物處置領域專家分析,自2003年起各地陸續建成的處置中心,設備簡陋,技術簡單,大多數無法達標處置和煙氣排放,成了“集中式排放的污染源”。
當年處置中心未能完全“放開”引入市場機制,是考慮到醫療廢物的危害性,不敢放松行政許可,而且當年涉及該領域的公司偏少。通常獲特許經營的企業有兩類:政府部門特別是環保系統內部退休人士或嫡親,以及政府下屬的事業單位新成立公司接盤;通過一定關系和資源介入并獲取壟斷經營的公司。一位專家分析,現在該領域公司數量激增,有放開市場的條件,這樣才能在處置價格和技術規范達到雙重優化。(本文來源于《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