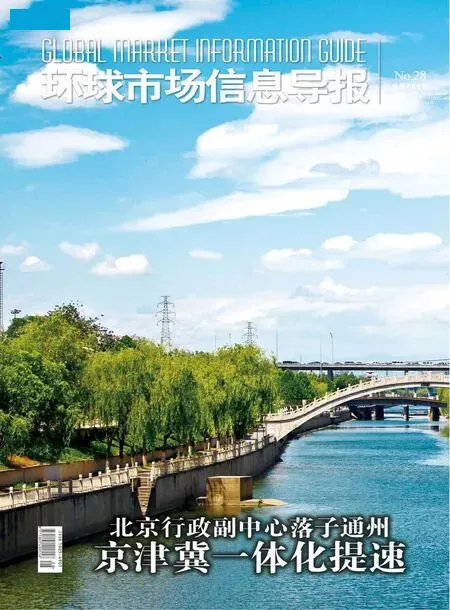所有人都在等樸樹的演唱會
所有人都在等樸樹的演唱會

十二年太長,樸樹新專輯第一支曝光的單曲終以“君歸來”開場;一個輪回太久,瞬間勾引出寵溺他多年的歌迷的淚水,再現了去年《平凡之路》的狀況。關于《在木星》,樸樹說,“意象、歌名2003年就有了,旋律2007年就寫完。當時是幻想一個沒有生老病死,愛恨離別的世界”。而現在他相信有這樣的世界:“我們所有人都會去那兒。這些年一切都是老天爺安排的。每一天都在我承受力的邊緣,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我寧可早點結束這種折磨,有時它并非那么好玩。”而抑郁的時候,樸樹在想什么呢?

一
當年抑郁癥發作時,他每天什么都不干,只去坐地鐵,從起點坐到終點,再從終點坐到起點。
見樸樹之前,我對他助手說采訪需要大約兩個小時。他的助手擔憂地說:“看情況吧,他特別不能說。今年做采訪只有一次破了紀錄,聊了近一個小時。”
見到樸樹是在北京三里屯一個臨街的酒吧。晚上7點,樸樹架著一副太陽鏡,戴一頂帽子,左手一支煙,右手一把叉,抽幾口煙,再吃一口蛋糕。
為了有一個比較安靜的采訪環境,我們打算另換一個地方。等著結賬的空檔,他有一搭無一搭吃著面前據說是晚飯的那塊蛋糕。我們都不說話,都扭頭看著窗外華燈初上的街道。我有些擔心,想象著這次采訪的失敗。
我決定打破沉默,話一出口竟是:“我有點緊張,你好像不太愿意說話。”
樸樹愣了一下,隨即笑起來:“你們這種工作天天跟人打交道,怎么還會緊張?”
他很詫異。“我現在鍛煉得已經好多了,現在面對采訪也沒以前那么抵觸了,起碼表面上能過得去了。放心吧,我是一個挺溫和的人。”
樸樹笑起來的樣子像一個孩子,他的聲音溫和,音量很小,這讓我一直擔心錄音效果。他的話很少,要不停地追問才會有完整的答案,但言語間卻充滿叛逆,就像他自己所說是溫柔的瘋狂。他語速偏慢,有時會顯得有些結巴,習慣說完一句話后,再補充個“對”字,好像在進行自我肯定,又像是在鼓勵自己。采訪時樸樹一直戴著眼鏡,他說:“昨夜沒睡好,戴眼鏡純屬生理上的需要,這樣眼睛特別舒服。”
二
最早知道樸樹是因為《白樺林》。樸樹用自稱有些脆弱的聲音演繹出懷舊的色彩,這首原創歌曲讓聽者動心,樸樹也一炮走紅。
對這首讓他一夜成名的歌曲,樸樹的態度有些絕情。他說:“我絕對是耍了一個小聰明,編制了一個讓自己感動的東西,其實我不喜歡那首歌,我覺得無論是從投入的感情還是技術層面來講,這首歌都不是我理想狀態中的東西。”
樸樹只唱自己寫的歌,沒想過給別人寫歌,按他的話說:“寫得不好的歌,不愿意唱給別人聽,不愿意讓別人知道;寫好了,又舍不得給別人,寫好就意味著你投入了很多很多感情。”
現在的樸樹,在大陸,港澳臺,甚至東南亞的任何音樂大典上都能見到他的身影,絕少說話,大多時候戴著一副墨鏡。樸樹是一個缺少安全感的人,戴眼鏡可以不必把自己心靈的窗口暴露在別人的視線之下。
樸樹得的獎項,連自己都記不清有多少了,對于那些獎項,他一點都不謙虛,他認為都是自己該得的:“這些名利,對于中國歌壇來說也是一件好事,會刺激更多的人用心做唱片。我敢說,我比別人更專注,更投入感情。沒有人像我這樣認真這么狂熱地做一張唱片。”


在歌壇,樸樹是個異類。他不熱衷宣傳,對媒體的采訪是眾所周知的不配合。
在一些公眾場合,他充滿棱角的個性讓活動的主辦者大傷腦筋。早前,他在上海“華語榜頒獎典禮”上摔獎杯,最近參加“第四屆金鷹節”,在一個現場直播的節目里又將了主持人一軍。已經很疲倦的樸樹被主持人問及何為“酷”字,樸樹一語驚人:“酷”字是個屁,主持人立馬傻眼。到了這個節目的另一環節,主持人問樸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樸樹直言:“離開這個節目現場”。
傳言中的樸樹:冷酷、孤傲、不善言辭、不善解人意、不與媒體配合、我行我素,曾有過抑郁癥史。甚至有人說樸樹走過的地方,空氣中都會飄過一種不快樂。
三
1999年夏天,樸樹過得特別開心,那些沒有壓力的日子,讓他感覺所有的日子都金光閃閃。
在這樣的日子里,樸樹接拍了他的第一部電影,也是唯一的一部電影《那時花開》,和周迅的戀愛也是在那部電影中開始的。
和周迅談戀愛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樸樹從不否認那段時間的美好。現在,兩個人雖已各有所愛,但并不影響他們成為好友。在樸樹新專輯《生如夏花》的一首MV中,周迅不避嫌地客串了一個角色,和樸樹飾演一對戀人。
“我覺得她也是個性情中人,特別有才華,所以有的時候我也覺得她不太適合這個圈子。她是個特別好的演員,但是能發揮她自己才華的機會還是太少了。前一陣子她跟男朋友分手之后,情緒比較低落,而那一陣子媒體對她缺乏善意,作為一個好朋友我覺得這挺不應該的。”

樸樹欣賞現在的女朋友,她是個承受力非常強,非常有能量,生命力旺盛的人,性格上天生亢奮。這些剛好和樸樹的抑郁互補。樸樹說自己不能給女朋友安全感,也不愿意給。
當年抑郁癥發作時,樸樹每天什么都不干,只去坐地鐵,從起點坐到終點,再從終點坐到起點,和那么多人在一起,他才會有安全感。現在,樸樹說,“我不想要安全感。當人依賴于安全感的時候,人就不會進步。”
記者:你給人的感覺好像不是那種開朗的人?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樣的狀態?
樸樹:對。沒有人要求我做出一副特親善的樣子,我自己也特注意在公開場合不要把我特抑郁的那一面露出來就足夠了。作為一個人,這應該是被允許的。我在生活中什么狀態都有,常常心不在焉,有時上臺都是。前兩天在上海時,被喊上臺的一瞬間我知道我走神了,別人沒發現。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覺得人在那種時候就應該專注。
記者:你評價一下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樣的?
樸樹:分裂,極端分裂,總體來說,很溫和。我挺喜歡一個詞叫溫柔的瘋狂,我覺得形容我比較貼切。
記者:你不愿跟人交流,是覺得別人不會欣賞你,或是不配和你交流?
樸樹:一方面這么想,另一方面是自己特別自卑。人應該把自己打開,現在我也沒有說這點做得有多好,但我覺得比幾年前進步很大。2001年,有一段時間我突然覺得人干癟了,因為我老把自己關在一個小地方,就看日記,已經特空洞了。我覺得我應該沖出去,然后過了快兩年多的夜生活,天天在外面混,混得特別爛。
記者:爛到什么程度?
樸樹:要多爛有多爛,經常被別人早上背回家那種。逼自己跟陌生人說話,故意裝作一副大大咧咧的樣子。其實就是這樣,人如果把自己放在很卑賤的位置就好了。畢竟歌手這行業容易弄得人覺得自己特別牛,有時候會被架起來,你會覺得高高在上,其實什么都不是呀。
記者:你這種抑郁跟你的性格有關,還是跟生活有關?
樸樹:基因里頭有一些特別陰郁的東西,另外跟生活狀態也有關系。抑郁是階段性的。過一段,然后又會好,跟潮汐似的,經歷多了,情緒起起伏伏多了,就不會再有那么擔心了。當你最難受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靠,熬過了今夜明天就會好,就慢慢知道規律了。生來為人就是要吃苦的,吃夠那苦就好了。
上個月有一天快崩潰了,我就上網,把所有關于我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標題是夸我的看,一看是罵我的,去你媽的(笑)。這些文章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讓我成功地度過了那個晚上,成功地度過了一次危機。
記者:有過想用極端的方式解決心理問題嗎?
樸樹:應該有,但我真的是忘記了。六七年前就是開車往特遠的地方,到南戴河,北戴河,然后再開回來,剛到家又想開車往那邊去。好多時候人是處于那種失控狀態,就是停不下來,就逼著自己停下來。我覺得有時候人得控制自己,人走下坡路最簡單了。

記者:你最抑郁的時候做過什么樣的事情?
樸樹:幾年前的事情忘了。現在這幾年就是把那種情緒全部轉移到我女朋友身上,因為她是生活中離我最近的人,她會為我受苦。那時我會六親不認,不會打她,不會罵她,就是原封不動把那些壞情緒轉移到她身上。
記者:看過心理醫生嗎?
樸樹:小時候看過,三年前我又偷偷去看了一下,就是想找原來吃過的藥吃,但后來就覺得應該自己去承受。
記者:為什么是偷偷地看呢?
樸樹:那個心理醫生是北大的一個老師,是我爸媽的朋友,我怕我爸媽知道我那個時候的狀況,怕他們擔心,我還試圖偷偷地問我爸,我媽把我上高中時吃的藥藏在哪,我想偷出來。
記者:醫生給你什么建議?
樸樹:醫生也沒什么建議,見了醫生,我就什么都不想說了。然后慢慢開始相信所有人都一樣,所有人都承受著很多東西,人的忍耐力無窮大,憂郁實際上跟寒冷和饑餓一樣,就是人應該承受的,而且人的那種求生的能力非常非常強,那種承受力是沒有邊際的。當你走到你臨界點,就會好。
記者:你到了那個臨界點了嗎?
樸樹:不知道,有時候覺得我已經到了,有時候覺得我永遠不會,但我現在對這個不關心了,覺得無所謂。我心里能夠接受這個現實,我是一個特擰巴的人。我覺得有時候我享受這種狀態,就夠了。哪怕有時我對生活充滿了恐懼,我還應該享受這個狀態。
記者:你有音樂上的天賦嗎?
樸樹:沒有,但是據說我爸爸年輕的時候曾經有過當音樂家的夢想。應該說在我選擇要去做什么的問題上,父母對我的影響不是特別大,他們都是北大教空間物理的,可以說沒有給我太多營養,他們那代人在我看來對于生活的認識太單調了。但是我的父母給了我善良,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很善良的人,還有就是對于奢侈的生活沒有興趣。
記者:你爸說你不想上大學?
樸樹:不想上,就是不想上學了,我那會兒老跟圓明園畫家村的那幫孩子一塊玩,我就特想過那種生活,把頭發留得長長的,必須長到讓大家一看就知道。可以到處耍流氓,欺騙各種文藝女青年,特別牛。但是我爸跟我說,上大學跟上中學完全不一樣,大學非常自由,全是選修課,你可以挑你愛上的課,說大學的女生特好看。這么一想,不上不行了。他們是知識分子,他們不能承受的是,這孩子沒考上大學,他們會覺得在他們那個環境中沒臉生活下去。
記者:你父母知道你心里想要什么嗎?
樸樹:我想他們應該沒有了解過我,他們試圖理解我。
記者:第一張唱片出來以后,你說過你覺得一夜成名對你來說是一個錯誤。給你帶來的壓力,還有你被迫過的生活,包括你賺到的錢,得到的榮譽,都承受不了,為什么?
樸樹:當你沒做好精神準備的時候,你得到什么東西,都會變成負擔,名和利都會變成負擔,它只會給你一瞬間的快樂。但是,沒有東西是沒有代價的,那種快樂過后的失落是我那時候承擔不了的,包括壓力。后來想多少歌手只是在一些酒吧類的地方唱歌,多少做音樂的人名不見經傳啊。想到這些就覺得一夜成名不是錯誤,我覺得我很幸運。
記者:你現在最想過什么生活?
樸樹:簡單,簡單最重要。簡單,從容,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