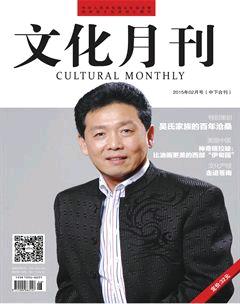“守正”才能“創新”
關峽
陽春白雪的歌劇不應“為了高雅而高雅”,也不應為了政績而辦,想要發展好中國歌劇,要把握好‘守正”與“創新”這關鍵兩點。
所謂“守正”,即歌劇的藝術魅力不能丟,不能為了迎合市場,隨意更改專屬于歌劇的藝術特征,削弱歌劇的核心影響力;而“創新”則意味著歌劇必須要拋掉沉重的思想包袱,在表現形式、表演分寸甚至劇情改編方面,都要有大膽的動作。沒有“守正”的創新,是對藝術的不尊重,而沒有“創新”的守正,是不求進取。如何在兩者之間尋找新的靈感,需要歌劇工作者做一番苦功。
中西方歌劇發展基本脈絡及特征
以戲曲板腔體音樂結合地域性民歌,加之話劇式對白或戲曲式對白結構而成的舞臺藝術樣式,主要演員以民族唱法為標志,習慣上稱之為“中國民族歌劇”。建國后近40年間,以《白毛女》《洪湖赤衛隊》《江姐》及新時期《黨的女兒》等百部以上歌劇走的是一條由某一地域的戲曲、民歌,以板腔體音樂結構而成的路。在音樂與表演上,它與中國傳統戲曲有著直接的血緣關系,加之題材選擇吻合歷史和民眾需求,因而受到普遍歡迎。隨著男、女中音角色的出現,擔任主角的歌劇表演藝術家們才改變了民族唱法一統天下的局面。
這時的編劇在保留戲曲結構中“場”形式外,適時引入了西方話劇某些戲劇原則和對白語言風格,演員表演也從戲曲中吸引了很多程式化表演技巧。其唱段或多或少突破了地方戲曲的唱腔構成模式,旋律的歌曲化特點加上伴奏樂隊表現力的增強,突破了地域范圍,得以更多人接受和喜歡。
反觀戲曲發展現象,中西方音樂文化在戲曲中結合的方式所產生的震撼力是空前的。各種成熟地方戲劇種尤其是京劇,是中華民族經過幾百年逐步確立起的邏輯嚴謹、韻角嚴密、行當清楚、程式化的表演體系,具有多元素混合所產生的特殊美感和魅力。受現代京劇影響,地方戲團將許多歌劇和現代京劇移植成地方戲。程式化表演與戲劇矛盾用各種聲腔夸張的表現力在某些方面趕超原版,給各劇種帶來前所未有的藝術表現。
細論歌劇中運用板腔體音樂的作法,優勢是貼近傳統,有一定群眾基礎,擅敘述、唱段與對白,弱勢是用音樂刻畫人物心理及精神的空間有限,音樂和人物易產生距離感。就劇本和音樂關系而言,音樂處于從屬地位,如何用音樂最擅長的手段來勾畫人物鮮明個性和心理活動,作曲家如何以獨特視角和創作個性運用交響式思維展開戲劇化音樂、在板腔體音樂架構中創作歌劇音樂,還需認真探索、大膽實踐。
傳統力量深入骨髓。毛澤東曾以藝術為例,說:“藝術的民族保守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現代聽眾口味和審美興趣的變化所受的外來影響,多來自西方流行音樂,影視音樂、古典音樂及現代派、后現代派音樂的影響;西方舞臺藝術中的歌劇、音樂劇中的音樂對大眾影響較弱,即使有影響也是最近幾年的事。
以意大利歌劇的音樂結構原則,如宣敘調、詠敘調、詠嘆調來表現中國發生的事情的舞臺藝術樣式,主要演員以美聲唱法為標志,習慣上稱之為“中國歌劇”。1987年《原野》的首演成功,給中國歌劇界帶來不小震動,同時也招來很大非議。這部寫實主義的歌劇走出國門,在歐美等地的演出和學術交流活動中受到很高評價,被譽為“第一部震撼西方舞臺的中國歌劇”。該劇用19世紀后半葉形成的意大利式歌劇音樂結構,描寫了20世紀初中國農村生活中一個以復仇為主題的愛情悲劇故事。充滿了戲劇性音樂、大量宣敘調、詠敘調、詠嘆調與重唱,采用現代作曲技法創作歌劇音樂,主要演員均受過音樂方面的高等教育,以美聲唱法為主。
西方人不明白,一個中國作曲家怎么有能力用意大利式歌劇思維來講述這樣一個悲情故事,一些中國人也弄不清為什么要用那么多不協和音響,一驚一乍的“唱著說事”呢?不管怎樣,拋開聽覺上的無法適應,《原野》中幾段充滿音樂張力的詠嘆調、二重唱、加上了時代鮮明烙印的仇虎詠嘆調《你是我,我是你》,用管弦樂隊刻劃人物、描繪事件及推動情節的巨大動力還是深深打動了許多人。有人喜歡《原野》,有人不喜歡《原野》,這一現象其背后隱藏著來源于兩種完全不同的審美價值取向的相互排斥,是東西方文化在舞臺藝術形式上的劇烈碰撞。我們所處的時代是變化、妥協和融合的,不再僅僅滿足于形式上的借鑒。多層面手法上的借鑒已成趨勢。
時代前進,流行音樂在中國興起,人們的生活方式不斷改變,價值觀念不斷調整,審美趣味一變再變,雖然“中國歌劇”和“中國民族歌劇”被擠至文化邊緣,然而在困頓的大環境中,依然創作出大量作品。1991年《黨的女兒》上演,受到廣泛歡迎,演出達百場以上;1999年,我參與創作的《原野》復排上演,雖票房失利,業內評價卻很高,獲獎無數。
“民族歌劇的觀眾群在哪”成了問題,“在創作新劇目前調整創作思路”,是必須要做的事。
西方歌劇發展概況
歌劇OPERA是OPERA IN MUSICA的縮寫,由16世紀佛羅倫薩的佩里(PERI)和卡奇尼(CACCINI)為當時戲劇配樂而確立。宣敘調在戲劇中占統治地位。1607—1642年間,蒙泰韋爾迪從牧歌和威尼斯華美的教堂音樂中汲取營養,使歌劇得到迅速發展,他用器樂為宣敘調伴奏,使詠嘆調成為歌劇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17世紀始,法國的呂利和拉莫,德國的許茨和凱澤爾積極倡導歌劇事業。到了亨德爾,他大大增強詠嘆調和宣敘調兩種戲劇表現形式,采用意大利“正歌劇”風格,獨唱詠嘆調十分壯麗,為當時國人歌手和優秀的女高音展示輝煌技藝而寫;18世紀60年代的J·C·巴赫在歌劇中恢復了合唱地位,格魯克在1794至1779年間也作出同樣努力,其1762年創作的《奧爾菲斯與尤麗狄茜》是部革命性歌劇,充分表現出音樂和戲劇性的可能性;莫扎特較海頓又進一步,使管弦樂作用擴大,使歌劇藝術增添全新一面;羅西尼在喜劇方面的輝煌才氣、機智和興趣,延續了19世紀初莫扎特創造的輝煌局面,與貝利尼和多尼采蒂合作創作了許多偉大作品。
德國浪漫主義運動對民間傳說和幻想情有獨鐘。韋伯的《自由射手》、《奧伯龍》為瓦格納日后的改革披荊斬棘;瓦格納否定世人確認的“分段歌劇”,將樂隊當作不登臺的角色,使宣敘調和詠嘆調變成延續而無空隙的交響音樂網。他親自撰寫劇本,把歌劇變為集一切藝術的混合體,寧稱“樂劇”而不用“歌劇”,以展現“歌唱者們”為壯觀的歌劇的一處反動;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堅持“分段歌劇”形式,創作出《茶花女》、《阿伊達》等偉大作品;之后的普契尼提高歌劇富有音樂和戲劇色彩的直接感染力,其《藝術家的生涯》《蝴蝶夫人》《圖蘭朵》受到廣泛歡迎,至今仍在上演。endprint
民族音樂歌劇是在東歐發展的產物,自格林卡于1836年的《伊凡·蘇薩爾》始,在20世紀的30年內,亞納切克有影響而獨特的寫實歌劇使這一傳統達到頂點;英、美兩國較其他國家花去更長的時間找到本國歌劇的立足之地。自格什溫的《波吉與貝絲》始,“歌舞劇”風格隨著新的光電技術及機械裝置進入舞臺,電聲樂系進入管弦樂隊,使用麥克風的演唱方法得以應用,最終確立風光無限的“音樂劇”。
音樂在歌劇中是首位的,音樂進入戲劇確立了歌劇這一全新的舞臺藝術形式。隨著交響樂的發展,管弦樂隊在歌劇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聲樂在不同時期起不同作用,交響式音樂思維在歌劇中的極度擴張改變了歌劇的構成模式。宣敘調的作用從“統治地位”降為從屬地位,后又和詠嘆調的地位同等重要,但篇幅在全歌劇中比詠嘆調大的多;詠嘆調從無到有,繼而在歌劇占主要地位,后又讓位于宣敘調或詠敘調。
歌唱家的演唱技能直接影響歌劇作曲家的音樂創作,音樂結構形式的變化構成不同時期歌劇的特征:以莫扎特、羅西尼到威爾第等人的“分段歌劇”樣式,使詠嘆調在歌劇的構成中占突出的位置;以普契尼中后期“音樂及歌唱連綿不斷自始至終的樣式”,但未取消“詠嘆調”,數量上較前者少了許多;以瓦格納管弦樂編織的交響音樂網,是音樂的主要因素,其個性鮮明、有編號、大出風頭的詠嘆調是德國式交響樂,體現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浪漫主義哲學的信仰及新時代交響樂的語言;以安德魯·洛依德·韋伯等“音樂劇”作曲家們一開始就為演出市場設計劇目,不固守傳統,以其綜合性、現代性、多元性、靈活性和高度的商業操作性。這種集音樂、舞蹈、戲劇表演于一身的現代舞臺劇樣式已完全不同于歌劇,盡管歌劇中的一些原則依然存在,但它取悅現代觀眾的心理傾向消解了歌劇中的一些重要原則。
“悲劇審美”與“音樂戲劇”
在悲劇中人物的品質是由其“性格”決定的,而性格的形成有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幸與不幸,取決于行動。
悲劇要描寫殘酷和恐懼,從而引發出的人物的感受,在偶然中寫出必然。其目的在于凈化人的心靈,使情感趨于平衡。車爾尼雪夫斯基講“因為藝術中的悲劇正是在情節或性格的發展中,以激烈的沖突形式將現實的矛盾反映出來,以喚起人們積極的審美感受”。悲劇所以表現崇高,是因為它不是讓人們產生悲觀、失望、消沉頹廢,而是讓人從緊張的沖突、嚴重的抗爭中感奮興起,提高精神,增強意志,高揚倫理,喚起人們的崇高之感。
作為美學范疇,崇高為西方獨有,在中國只有與崇高接近的壯美或陽剛之美這一美學范疇。在近代,隨著西方哲學、思想、文化等逐漸進入中國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人們才慢慢接受崇高這一精神境界。崇高中的痛感與偉大感的合理性,在實際生活中找到原型和動力。
較之民族傳統中的陰柔之美、陽剛之美,朦朧美等審美范疇,與西方悲劇中那莊嚴而偉大的思想、強烈而激動的情感、高雅而宏偉的措辭,給人們帶來的審美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在古希臘的所有悲劇中,音樂作用表現在唱詩班、場景音樂和幕間音樂等方面。
在中國歌劇的悲劇題材創作中將優美、壯美和崇高美溶合在一起用音樂來表現,描繪人物及其事件是必需要做好的事情。而語言表述的方式決定了音樂創作手法的使用。用最恰當的音樂語言和歌劇劇本中文學語言及戲劇性語言相吻合方能造成和諧統一的效果。
歌劇在中國的實際創作中,普遍存在“劇本至上” ,而使音樂是從屬地位的現象,削弱了作曲家的創作個性和應有的或必須的作曲手段的使用。使歌劇應是“音樂的戲劇”這一重要原則無法鮮明體現。
由于板腔體音樂的歌劇是從戲曲(或民歌)音樂中生長起來的,作曲家所創作個性被淹沒是很自然的事,比照戲曲音樂創作中的情況就可明了。曲牌有地方特色約定俗成的曲調根據戲詞嚴格按韻腳譜曲是戲曲音樂創作最基本的要求,唱腔中人物情緒的變化是按已定型的各類板式組合而成。表現人物類型甚至身份都有固定曲牌,所以戲曲界稱此類音樂創作者為“音樂設計”。
歌劇作曲家遇到這類結構唱詞,也需借用戲曲快板、流水、垛板等方式創作,用某戲曲的文武場和相應過門進入共同表現極致的情緒。
劇作家為了結構劇本,從題材、體裁、思想內容、情節、臺詞、唱詞、對情節的精致描寫下足功夫,使人在看本子時就獲得完美感受。歌劇是“音樂的戲劇”、是由充滿戲劇性音樂構成的戲劇。法國劇作家博馬舍在其《塔拉垃》序言中講:“音樂在歌劇中就如同詩句在話劇中一樣,是更加宏偉的措辭,表達思想和感情更加有力的方式”。
其實,歌劇從來以情節的統一連貫或條理清晰而取勝。奧登在1961年時說:“沒有一部優秀歌劇的情節合情合理,因為人們在講理的時候不唱歌”。“對情節敏感”的人來說,有些歌劇故事過于簡單或不合理。
在歌劇中,什么事都可能發生,而我們必須接受這一點。在很多歌劇中,女主人公在沒有明顯理由的情況下死亡了,男主人公由于愛的悲傷和忍受不了的煎熬就徹底崩潰下來了……感人的音樂和詠嘆調、華美的舞臺、優秀的歌唱家動人的演唱表演并不妨礙人們去欣賞歌劇,歌劇藝術表現的最擅長處不是情節的進展,而是心靈的狀態。當聽到親愛的人死去,劇中人的反映是唱一大段詠嘆調,這正是觀眾心理上所期待的。
我們要了解歌劇音樂的力量和局限在哪,并和劇作家一起來構造適合音樂和演唱所表現的段落,給音樂預留出足夠空間。還要和劇作家一起處理好臺詞、歌詞和音樂的關系。由于漢語中的輔音字節太多,做宣敘調時要特別注意,否則會顯得牽強和滑稽,這是漢語發音的特點所決定的。歐洲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西方歌劇中,臺詞必須順從音樂。莫扎特說:“在歌劇中,臺詞是音樂孝順的女兒”,這顯然是基于他們的語言特點之上所作的概述。
中國歌劇的發展進程中,在現階段民族歌劇的音樂創作中,民族和美聲兩種唱法同時出現在舞臺上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就要求擔任角色的演員在演唱方法和聲音的使用上注意以下問題:持民族唱法的演員在保持演唱民族旋律“親切感”的前提下充分借鑒美聲唱法的發聲法,用以增強聲音的張力和威力;持美聲唱法的演員要追求能和觀眾產生“親和力”的聲音,吐字要清楚;要塑造好劇中“這一個”人物的聲音形象,不能走入“以唱法論英雄”的聲樂誤區。
歌劇這種舶來的舞臺藝術形式,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還有很艱難的路要走,能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創作理念進行嘗試,無疑是中國歌劇發展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的必由之路,“守正創新”傳播正能量并能獲得觀眾的喜愛,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
在世界各地除格林達波恩歌劇節和獨立制作的音樂劇外,無一例外全都得到來自政府、企業界、公司及民間的大量資金的資助。昂貴的出資用以扶持歌劇的上演和推廣,才能使被譽為“藝術中的皇冠”——歌劇這一形式得以繼續存在,并在人類的文明中綻放出燦爛的奪目的光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