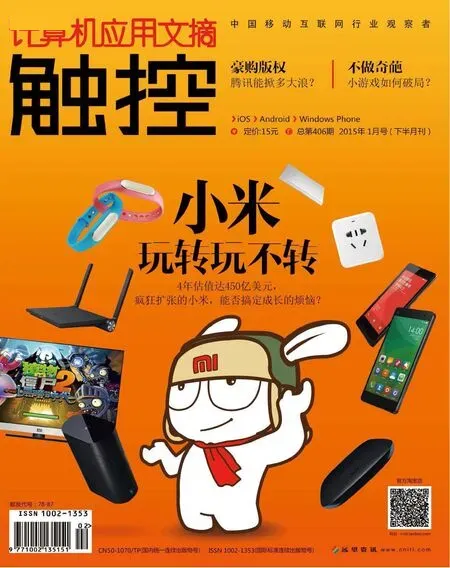開放民資入局,寬帶市場迎契機
蔣舒


一直以來,國內的寬帶市場就為廣大用戶所詬病:接入速度慢(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資費高(與周邊國家相比)等。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問題呢?在國內,所有的寬帶基礎資源都掌握在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兩大國有基礎運營商手中,這就使得競爭并不激烈,問題自然層出不窮。不過,這樣的隋況在去年11月底有了一些變化,工信部的一份文件讓民資全面進入市場成為了可能。
民資寬帶,由來已久
2014年11月26日,工信部發布了《關于開放寬帶接入市場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簡稱“意見稿”),擬在上海、重慶和廣州等16個城市開展為期3年的試點,鼓勵民營企業以多種模式進入寬帶市場,并參與寬帶接入網絡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意見稿”中明確提到,在16個試點城市中,民營企業可以參與寬帶接入網絡設施建設和運營,也可以通過資本合作、業務代理和網絡代維等多種形式和基礎電信企業開展合作、分享收益。同時,擁有互聯網接入服務(ISP)業務經營許可證的民營企業,還可從基礎電信企業租用接入網絡資源,為最終用戶提供寬帶上網服務。
其實,這并不是國家第一次鼓勵民營資本(以下簡稱“民資”)進入寬帶市場。早在2001年6月,原信息產業部就發布了《關于開放用戶駐地網運營市場試點工作的通知》,開放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13個試點城市的寬帶市場,大家平時經常能見到的“長城寬帶”、“艾普網絡”和“方正寬帶”等知名民營寬帶運營商均成立于這一時期。除民資之外,國家電網和廣電也借東風進入寬帶市場淘金,分別成立了“中電飛華”和“歌華有線”等公司來開展寬帶業務。甚至連房產大鱷潘石屹也成立了“世通在線”,為旗下25家SOHO提供寬帶網絡。
2003年,成都泰龍電信通過和成都聯通合作,代為建設駐地網并發展固話用戶,泰龍電信則可以分享月租費、初裝費和通信費用。“泰龍”模式很快就吸引了鐵通和網通的合作,有效挑戰了當時在成都處于壟斷地位的成都電信。但由于這一模式屬于政策監管模糊地帶,泰龍電信很陜遭到嚴厲打擊,寬帶接入市場成為國有運營商的自留地。
“泰龍”模式慘敗,其他民營寬帶運營商的日子也不好過。隨著移動、聯通和電信三大國有基礎運營商的基礎設施和網絡覆蓋基本完成,民營寬帶靠租用基礎運營商的主干網絡在城市中自行進行接入網建設的業務模式也受到了很大挑戰。這種繞不開國有基礎運營商的模式,即便是經營多年的民企也很難在寬帶市場上淘到金。
開放民資入局,一個新的契機
國有基礎運營商之間并不激烈的競爭和民營寬帶運營商的艱難發展,讓國內寬帶市場始終處于一個發展雖快但罵聲不絕于耳的尷尬境地。此次工信部決定開放寬帶接入市場,首次明確了民資經營寬帶接入服務的各種條件,此舉無疑將促使民營企業與三大運營商處于相對平等的競爭位置,讓市場逐步正規化。
“意見稿”中明確提出了關于國有基礎運營商、相關管理機構和民營企業在這輪開放民資的過程中所承擔的義務、責任以及如何界定相關行為。從這些細化條目就可以看出,這次的“意見稿”是一個可執行性非常強,有市場基礎的政策,基礎運營商、民企和監管部門的職能劃分都很清楚。一位接近政策制定部門的工信部人士就表示:“市場催生了許多民營寬帶,也衍生出了多種業務模式。但是,大部分都沒有規范,出現了諸如小區壟斷等問題。這次的‘意見稿明確了業務模式、市場規范,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基礎電信運營商與民企的合作方式,以及監管部門的管理范疇。”
可以想見,在規范了相關的市場規則和相關事宜之后,接入市場向民資開放肯定會催生新一批寬帶運營商,市場競爭格局進一步加大,這對網速慢、收費貴的現象肯定會產生積極影響,用戶也將因此得到更為質優價廉的寬帶服務。而對基礎運營商來說,新興勢力的涌入雖然形成了威脅,但其中也包含著一種救贖。“民企進入寬帶接入領域,反而可以讓基礎運營商騰出手來,有更多精力去考慮如何適應未來物聯網與大數據,甚至工業4.0和整個信息生產力時代的要求。”中國信息產業經濟學會理事長楊培芳如是說。
當然,任何事物都存在兩面性,民資入市也是一把“雙刀劍”。和虛擬運營商一樣,民營寬帶運營商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成為一個尷尬的存在,因為移動、聯通和電信這三大國有基礎運營商在其多年的運營中積累了巨量的資本,從一般用戶的認知角度來說,大多還是會選擇他們的寬帶業務。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競爭主體的出現,首先增大的是低端市場的競爭程度,中小寬帶運營商的競爭無疑會慘烈無比。除了激烈的競爭,“意見稿”中對民營企業也結結實實地存在著諸多限制。所以可以想見的是,未來的民資寬帶,誰有好的合作模式,誰有好的產品,誰有好的服務質量,誰就能站在未來市場的高地上。但是無論如何,“意見稿”的發布都可以算作是在一個原先封閉的地帶中撕開了一個口子,這總比沒有好了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