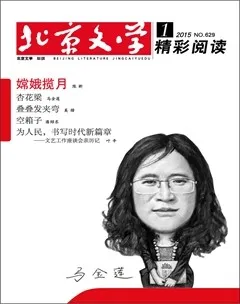馬寶山小小說二篇
親家
青延縣域有山,有河。山是老陰山,河是大青河。
有山,有河,這樣的地方就很富足,也就容易招來匪盜。青延知縣換了幾任,長的三二年,短的也就是年八月,最短的朱縣令只做了四個月就走人。為什么?都是讓匪盜鬧的。
青延縣境里有好幾股匪盜,其中隱匿在老陰山里,號小周天的一股匪勢力最大,有百十號人。匪首周方池,一個四十來歲的陜南人,據(jù)說從匪之前還是位私塾先生,只是不知道這個讀書人為何要做世人不齒的匪事。
清同治三年,上面派來的新縣令也姓周,名先鵬。臨來時,云州知府大人有交代,必須在兩年內(nèi)清除青延匪患,建設(shè)一個清明安寧的新青延。知府是周先鵬的先生,周先鵬說:“恩師,兩年內(nèi)清除匪患,學生心中沒底,可在半年內(nèi)叫青延百姓過上安寧日子,學生還是能做得到的。”
知府允準:那也好哇!
周知縣到任,不忙著清匪,先是整頓治安,興修水利。再就是忙著興教助學,先后辦了兩座學堂,一座叫青延官學,由官家出資辦學。一坐叫青河義學,由地方商賈出資辦學。這個時候青延縣的匪患不斷,時有被劫、被搶、被綁票的事報到縣衙里來,周知縣一一存檔備辦。
也在這時候,周知縣從青河義學領(lǐng)來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住到家里,與他獨生女兒一同上學,有專人侍奉護佑。
孩子姓周,學名一個單字,旻。周旻,眉清目秀,聽說學習甚佳。
知縣到任半年后的一天,讓車夫駕了一輛馬車,拉著師爺坐上去說:咱們進山。
山是老陰山,師爺一臉驚懼說:“老陰山?那可是匪巢啊!”
車夫倒是滿不在乎地問:“就我們?nèi)齻€人去?”
“走吧,別多嘴。”周知縣就坐到馬車上。一條土路凹凸不平,顛顛簸簸來到山前。知縣下了車,手指山腳下一個村子說:“你們就在小村歇腳,明日午時在此等候。”說罷只身進老陰山。
周知縣足足又走了半天,在山澗一片晚霞里東張西望的時候,忽然從樹叢里躥出兩個彪形大漢:“站住,東張西望看什么?是密探吧?”
周知縣呵呵一笑:“你們說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要緊的是兩位兄弟趕緊帶我去見你們當家的。”兩個大漢上下打量,眼前的人不是個獐頭鼠目之人,就把眼睛罩住引進山寨,推到匪首周方池面前,把眼罩取下。
周方池那時正逗弄籠子里的一只畫眉,他頭都不回,問:“帶綹子進山啦?”
小匪答:“爺,不像個綹子,倒像個先生呢。”
周方池這才回過頭來,打量來人:“做甚的?叫什么名字?”
周知縣微微一笑:“與大當家的一個姓,在下周先鵬。”
“哦,周先鵬,周知縣!”周方池急忙放下鳥籠子,近前仔細打量過,就吩咐人上茶,備酒席。
一個知縣,一個匪首,面對一張桌子坐著,一壺老酒喝了一夜,邊喝邊聊。
周方池斟滿了酒說:“周大人,只身闖我的老營,你就不怕我殺了你?”
周知縣與周方池碰了一杯道:“我是來與你商議大事的。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你這個讀書人懂得這個道理呀。”
“來招安?”周方池問。
周知縣答:“眼下還不成,我沒本事養(yǎng)活你的百十號弟兄。”
“莫不是清剿我們?”周方池沉下臉。
“清剿?那我不劃算。”周知縣說,“你的弟兄個個是腦袋別在腰帶上玩命的主兒,可是那些吃糧當兵的官軍,哪個是真心實意為朝廷百姓賣命的啊?在戰(zhàn)場上那些官軍五百人抵不住你的百名弟兄。我花錢養(yǎng)活五百官軍剿你劃算呢,還是養(yǎng)活你的一百兄弟劃算呀?你給我算算這筆賬。”
“周大人不僅是個好父母官,還是個很精明的商人啊。”周方池再一次給知縣斟酒說道。
“不敢當。”周知縣說,“吃朝廷俸祿,就得為朝廷分憂,為百姓做些事啊。”
“周大人既不招安,又不清剿,那與我商議什么呢?”
“想請你和弟兄們到別的地方去安營扎寨。”
周方池瞪圓了眼睛:“攆我走?”
周知縣看著他笑。
周方池這一回不給周大人斟酒,自己喝。
周知縣說:“攆你走的,除了我還有一位,他也姓周,叫周旻,我已經(jīng)把他請到我的府上與小女一同讀書。孩子們需要一個安靜的讀書環(huán)境啊。”
周方池的臉一下子灰了下來:“你、你怎么就知道,周旻是......”
周知縣哈哈一笑:“青延雖然是小縣,卻也有幾十名密探、捕快,我不能讓他們吃閑飯吧。”
“你想怎樣?”
“大當家的, 你若答應(yīng)我,我把周旻當作世侄,一定培養(yǎng)他成才。”
“若不答應(yīng)你呢?”
周知縣喝了面前的那杯殘酒。這時天已大明,他起身拱拱手說聲告辭,就披著一身晨曦下山去了。
從此,青延縣果真平安起來,周旻一心一意讀書,咸豐末年考中進士。那年他還與知縣家的小姐完婚后,被朝廷派到青延的鄰縣北固縣做知縣。金榜題名,洞房花燭,頂戴花翎,少年輕狂,新知縣一到任就組織民團剿匪,一戰(zhàn)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周旻也落入匪手,在押解路上他大罵不止,被一個小匪當胸捅了一刀,死了。
這股匪盜正是周方池一伙,當他知道一個叫周旻的知縣被手下捅死后,一怒之下?lián)]刀劈死三四個小匪,痛苦欲絕。
一天,周知縣在庭院里焦急踱步,小姐屋里一片忙亂,忽然“哇”地一聲啼哭,產(chǎn)婆挑開門簾道喜:“大人,小姐生了,生了個大胖小子,您做姥爺哩。”
知縣大人就吼一嗓子:吃酒嘍!
這時,從院門外踉蹌著走進一個人,周大人走上前一看“啊”了一聲:“周……周大當家的。”
一個知縣,一個匪首,再一次面對一張桌子坐著,一壺老酒,邊喝邊聊。周方池一聲嘆:“人作惡,不可活,今天我自首服法來了,請知縣大人發(fā)落吧。”
知縣為周方池斟滿酒:“作惡最后總是要作到自己頭上,周旻一個多么好的孩子啊,可惜死在你的手里啊。”
“報應(yīng),報應(yīng)啊!”周方池猛地灌了一口酒,“也好,如今我無牽無掛,死在周大人手里也算是我的造化。”
“無牽無掛?”知縣拍了兩掌,周小姐一身縞素,抱著孩子款款走進來,為周方池鞠一躬:“公公大人,兒媳有禮啦,這是您的孫子。”說著把孩子送到周方池的懷里。
老匪抱著孫子慟哭欲絕,忽然跪下:“周大人,任憑發(fā)落了,您的大恩大德來世再報吧。”
“親家,吃酒,吃酒啊!”知縣把周方池扶起,坐好,“這是你有孫、我有外孫的喜酒,要一醉方休哇。”
周知縣沒有把周方池的匪案上報,留他在家里做了老院工,打掃庭院,種花侍草。周方池也常常出門走動,他背著個褡褳,有時走三五天,有時走個半月時間。細心人就發(fā)現(xiàn),周方池哪次出門,一定是哪里有了匪盜,三五天,或是個半月,那匪情就銷聲匿跡了。
隨之周知縣升任云州知府,轄制七八個縣,幾十年竟無一匪患,夜不閉戶,市井井然,百姓安居樂業(yè)了許多年。
佛燈
草原深處有一座廟,叫湯格爾廟。主持廟政的是活佛嘎拉倉。嘎拉倉活佛三十歲,清癯儒雅,一副仙風道骨的樣子。
活佛每天凌晨寅時起床,洗漱一凈就做早課,誦經(jīng)一個時辰,天就亮了,他就到大廟前面的林子里散步。那天早晨,活佛從林子里散步回來,剛要邁上廟門臺階,突然一團黑影撲棱棱飛落到腳下。活佛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只鴿子,身上插著一支箭,受傷的鴿子伸揚著脖子,腿翅亂顫。
這時,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手拎一張彎弓從林子里跑過來,剛要拾起臺階上的鴿子,被守門的兩個喇嘛逮住,惡聲罵道:“混賬小畜生,你怎敢射殺廟里的鴿子,快跪下向活佛請罪。”
那小孩子不服氣地拼命掙脫,小腦袋瓜子左右亂晃,腦后一條小辮子隨著擺來擺去的,就是不肯屈膝下跪。活佛示意兩個喇嘛放下孩子,然后牽住小孩子的手,極是和顏悅色地說:“小兄弟,不要怕,跟我到門房里坐一坐,我有話問你。”
小孩子看看活佛,又低頭瞧瞧拴掛在腰間的幾只鴿子和拎在手里還在撲棱掙扎的鴿子,不敢邁步進院。活佛又一次仔細端詳這個孩子,只見他又黑又瘦,一臉饑色,就說:“我看你還沒吃早飯吧,就到我廟里吃吧。”
小孩子喉頭一動,隨著活佛走進廟里,坐到門房里的一把椅子上。
“小兄弟,你把身上的死鴿子放下來吧。”
小孩子順從地從腰帶上解下死鴿子,堆放在地上。活佛清點一下,問:“一共是七只,都是今天早晨射殺的?”
小孩子點點頭。活佛彎腰撿起剛剛射殺的那只鴿子,從它身上拔出箭支,輕輕撫摸著已經(jīng)死去的鴿子,問:“小兄弟,今年幾歲啦?”
“十二歲。”
活佛看到孩子冷得發(fā)抖,就讓孩子坐到爐火旁邊,問“這么寒冷的天氣,你怎么穿得這樣單薄呀?”
“奶奶死了,我沒有家了。”
活佛“哦”了一聲:“你阿爸、額吉呢?”
小孩子低下頭小聲說:“被草原的豺狼吃了。”
“真是個可憐的孩子啊。”活佛一臉悲憫的神色,又看了看輕輕握在手里的死鴿子,長吁一聲:“可是這個小鴿子比你還可憐,它已經(jīng)死掉了。鴿子的命數(shù)是12到20年。這是個去年才出窩的雛鴿,和人的年齡比算,它的年齡比你還小呢,卻被你殘忍地奪去了生命……”
小孩子的淚水就“吧嗒,吧嗒”往下掉,活佛看出這是一個很善良的孩子,就和藹地問:“你射殺這些鴿子做什么?”
“賣掉換錢,買燒餅吃。”
“如果廟里管你的飯,你還要去射殺鴿子嗎?”
小孩子搖搖頭。
小孩子就做了湯格爾廟里的一名小喇嘛,活佛為他起僧名叫那日松(松柏)。活佛給小喇嘛那日松講的第一課是:戒殺生。
小喇嘛喜歡射技,活佛就為他設(shè)計了盤霸:一盤輪子,輪子上橫一支桿子,桿子兩端是靶標,靶標一頭涂了紅色,一頭涂了藍色。輪盤一轉(zhuǎn),兩端的紅藍靶標上下翻飛。活佛就讓小喇嘛雙日子射紅靶標,單日子射藍靶標。半年時間,小喇嘛練得一手好功夫。在飛快轉(zhuǎn)動的盤霸上,要射紅,絕不射籃;要射籃,也絕不射紅。
一次,小喇嘛嘆息道:“我一手好射技,可惜無用武之地啊!”
活佛說:“只要草原上有豺狼,蒙古人的射技就會有用處的。”
這天,廟里來了兩個人,這兩個人有時說蒙古話,有時又說誰也聽不懂的外國話。他們吃住在廟里,早出晚歸,晚上倆人在油燈下畫圖。細心的活佛發(fā)現(xiàn)他們畫的是地圖,圖上有村子、河流、道路,還有井和泉的標注。還有一張是阿拉泰(金山)的示意圖。活佛知道, 這倆家伙是特務(wù),就抓了起來,送到薩王府衛(wèi)隊去了。幾天后,一隊日本兵來到廟里,說是他們的兩個水利勘探家失蹤了,有人看見就在你們廟里。小鬼子隊長逼著活佛交出人來。活佛說那倆人已送到薩王府去啦。小鬼子惱羞成怒,要燒掉大廟。當鬼子兵剛要點燃沾著酥油的火把時,一群鴿子鋪天蓋地飛來了,在廟宇上空盤旋,“咕咕”哀鳴。來自佛國的士兵畏懼了,個個丟下手中火把,退出廟門跑了。
活佛知道,他的湯格爾廟大難臨頭了,草原也不再安寧了。活佛叫來那日松說:“我和年老的喇嘛留在廟里,為你們準備足夠的炒米、奶食和牛羊肉,你帶著青壯年喇嘛騎上戰(zhàn)馬,用咱們蒙古人的彎刀斬斷小鬼子的魔爪,用血腥攔住小鬼子的腳步。孩子們,為了草原上的生靈,廝殺去吧!”
青壯年喇嘛一旦跨到馬背上,就是草原勇士,他們由那日松帶領(lǐng)著馳騁萬里草原,旗開得勝,大捷天門鎮(zhèn),血戰(zhàn)阿爾泰(金山),奇襲淖爾汗兵營......在八年里始終沒有讓小鬼子在草原上安寧一刻。日軍入侵草原,掠奪牛羊,霸占阿爾泰(金山)的美夢難圓,最后終是被草原勇士趕跑了。
抗戰(zhàn)勝利了,那日松帶著幾百個喇嘛兵來到湯格爾廟,活佛用最好的酒,最好的牛羊肉款待草原勇士。在酒桌上那日松喝著活佛親手斟滿的一杯又一杯奶酒,哭了:“活佛,我再也難做您的徒兒當喇嘛了。”
“怎么呢?”活佛再一次為他滿了一杯奶酒,問,“難道刀光劍影,比暮鼓鐘聲更悅耳?”
那日松說:“不,不是的。”
活佛再問:“難道硝煙戰(zhàn)火,比佛燈爍爍更奇美?”
那日松哭得更加慘厲:“不是的,活佛,您知道,我現(xiàn)在滿手都是血腥,哪里還敢做佛門弟子,哪里再配當您的徒兒啊!”
那日松的慟哭震蕩廟宇。
活佛在慟哭聲中,閉目捻珠,誦經(jīng)敬祈一番罷,說道:“徒兒啊,你殺掉的是草原豺狼,拯救的是草原生靈,你手上哪里有半點的血腥啊!有的是草原百花的馨香,有的是佛燈的圣光哪!孩子,回到廟里來,跪在佛祖腳下,在圣潔的佛光里度過人生,那是最幸福的人生啊!”
那日松就留在大廟里了,后來由活佛推薦做了湯格爾廟的大喇嘛,協(xié)助活佛主持廟政許多年。
解放后,那日松大喇嘛被草原牧人和僧侶推舉做了自治區(qū)政協(xié)的幾屆常務(wù)委員,直到進入21世紀的第八年,大喇嘛那日松才坐化于湯格爾廟,享年111歲。
大喇嘛坐化那天,從黎明到傍晚,鋪天蓋地的鴿群在廟宇上空盤旋,“咕咕”哀鳴,如歌,如泣……
責任編輯""" 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