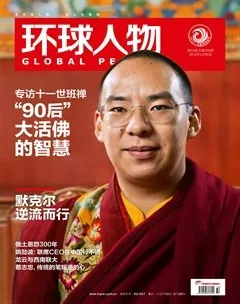馬可·波羅,讓北京遇上威尼斯
人物簡介:馬可·波羅,13世紀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1275年到達元朝,在中國游歷17年,后口述并由他人撰寫了《馬可·波羅游記》,激起歐洲人對東方的向往,對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影響。
“契丹省的各地都發現了一種黑石。它從山中掘出,其礦脈橫貫在山腰中。這種黑石像木炭一樣容易燃燒,但它的火焰比木材還要好,甚至可以整夜不滅。這種石頭,除非先將小小的一塊燃著,否則,并不著火,但一經燃燒,就會發出很大的熱量。”這段文字記載出自《馬可·波羅游記》,描述了元朝時中國北部人民使用煤的生活習慣。
這段描述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不算什么新鮮事,可對歐洲人來講就好像發掘了一個新世界。在馬可·波羅的影響下,歐洲人認為東方真是一片“黃金遍地,香料盈野”的土地,一代代的航海家被吸引著到東方探險,最終促成了新航路的開辟。
威尼斯商人的東進時代
13世紀的威尼斯,水道繁忙,大有成為地中海最富有的港口之勢。當時,威尼斯商人在歐洲大名鼎鼎,他們的商船往來于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現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把來自東方的絲綢和香料轉手賣到歐洲各地。漸漸地,威尼斯商人們發現,如果去掉君士坦丁堡這一環節,直接從東方購買商品再販運到歐洲,會帶來更大的利潤。恰好,13世紀崛起的蒙古連通了歐亞,為歐洲商人東進提供了便利條件,“到東方去”成為當時威尼斯商人的新理想。
1254年,馬可·波羅出生在這樣一個“全民探險”的威尼斯。他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和叔叔馬菲奧·波羅都是有抱負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他們告別了年僅6歲的馬可·波羅,乘坐商船到達了君士坦丁堡,為了獲得更多的商業利潤,他們決定冒險前往那個海市蜃樓般的未知世界——中國。
大約在1265年,尼柯羅和馬菲奧到達元朝的都城上都(現內蒙古正藍旗境內),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見。因為尼柯羅和馬菲奧兄弟是第一批來到中國的拉丁人,所以忽必烈非常重視。當時歐洲正處在中世紀后期,宗教是一切事務的中心,忽必烈迫切想要了解西方各國、羅馬教皇以及其他各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況。因此,他與尼柯羅兄弟的談話也都是圍繞著教皇情況、歐洲的宗教崇拜和基督教教義展開。尼柯羅兄弟不但是虔誠的基督徒,而且經過幾年歷練,已經精通蒙古語,深得忽必烈的喜愛。他們被忽必烈委任為專使,出訪羅馬教廷,請教皇選派100名精通基督教教義的傳教士來華,并從耶穌圣墓的長明燈上帶點圣油來。

尼柯羅兄弟帶著來自東方皇室的任務,踏上了回家的路。1271年夏天,兄弟二人帶上教皇的書信、禮物,以及已經17歲的馬可·波羅,再次踏上前往東方的旅途。
新鮮的東方世界
馬可·波羅跟著父親和叔叔,沿著陸上絲綢之路,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今天新疆的喀什、和田、且末、若羌等地。
穿越羅布荒原給馬可·波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當時,若穿越若羌一帶的羅布荒原,至少需要30天,經過的不是沙地,就是不毛的山峰。他們每晚都要尋找水源,有時還會碰到停留地的水又苦又咸。馬可·波羅日后回憶中提到了羅布荒原中還有可怕的幽靈,商旅常被幽靈所困而死于非命。這個說法在中國的古籍和近代其他一些西方探險家的著作里也有記載。
在路上走了近4年,1275年,馬可·波羅終于和他的父親、叔叔抵達元朝上都,見到了忽必烈,并看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東方大國。忽必烈對于尼柯羅兄弟的歸來非常高興,不但對兩位專使大加贊揚,還注意到了他們身邊的“小跟班”。忽必烈指著馬可·波羅問:“他是誰?”尼柯羅回答:“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兒子。”忽必烈立即說:“歡迎他,我很高興。”下令將馬可·波羅的名字列入榮譽侍從的名冊中。從此,馬可·波羅一家深受忽必烈信任,還接受了元朝政府派遣的一些公務。
馬可·波羅在元朝游歷大江南北,觀察東方的社會和政治,一待就是17年。他所到之處包括上都、大都(現北京)、揚州、蘇州、 杭州、福州、泉州等多個城市,對古代中國的城市建設贊不絕口。比如,他到達當時的貿易大港泉州時,就感嘆道:“這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此處的每個商人必須付出自己投資總數的10%作為稅款,所以大汗從這里獲得了巨大的收入。”
他還仔細研究了大都的城市結構、人口和商業,描述盧溝橋“長300步,寬8步,即使10個騎馬的人在橋上并肩而行,也不會感覺狹窄不便。橋有24個拱,由25個橋墩支撐著,橋拱與橋墩都由弧形的石頭砌成,顯示了高超的技術。”馬可·波羅把盧溝橋描寫得美麗、壯觀,引起了歐洲人的無限向往。因此,歐洲人后來就稱盧溝橋為“馬可·波羅橋”。
最令馬可·波羅感到新奇的,是元朝的驛站制度:“每一條大路上,按照市鎮的位置,每隔大約25或30英里,就有一座宅院,院內設有旅館招待客人,這就是驛站或遞信局;每一個驛站上常備有400匹良馬,用來供給大汗信使往來之用;在各個驛站之間,每隔3英里的地方就有一個小村落,大約由40戶人家組成,其中住著步行信差,也同樣為大汗服務;在每一個3英里的站上有一個書記,負責將一個信差到來與另一個信差出發的時間記錄下來。”這些詳細的記載為后世研究元朝的驛站制度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另外,馬可·波羅還記載了元朝制作紙幣的過程:先用桑樹皮造紙,然后裁成薄片,之后有多位特別任命的官員在每張紙幣上簽名、蓋章。最后,大汗任命的一個總管將他保管的御印先在銀珠中浸蘸一下,然后蓋在紙幣上,于是印的形態就留在了紙上。經過這么多手續后,紙幣取得了通用貨幣的權力,所有制造偽幣的行為,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這些全新的制度和風貌讓馬可·波羅大開眼界,而他本人也在17年中積攢了大量價值連城的珠寶和黃金,就等著找機會衣錦還鄉了。

1292年,波斯君主阿魯渾派遣3個專使,帶著大批的扈從來到忽必烈汗廷,請求大汗為他選擇一名淑女為配偶。大汗選擇了一位名叫闊闊真的17歲姑娘,并派遣馬可·波羅一家由海路護送他們回到波斯。臨別前,忽必烈給馬可·波羅一家鑄造了兩塊金牌,以便沿途地方官員給予關照和必要的供給。由此,馬可·波羅一家得以沿海上絲綢之路西歸,終于在1295年回到闊別已久的威尼斯。
被質疑的天方夜譚
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終于回到家鄉,可經過多年在東方的居住,無論是穿衣打扮還是口音,已經高度東方化的三人無法取得親戚的信任。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辨認和辯論,他們的親戚才明白,原來馬可·波羅一家三人并沒有死,而且還發了財,是真正的“衣錦還鄉”。
回家后的馬可·波羅三人以蒙古禮俗來款待親朋好友:他們先是穿著紅色的緞袍出來“走個秀”,然后換上深紅色的花緞袍子,把之前的紅袍剪成小塊,分送給仆人;酒過三巡后,他們又出去換上了一件深紅色天鵝絨長袍回來,將剛才穿過的花緞長袍撕開分送給來賓;飯后,他們又換回日常衣服,把剛才還穿在身上的天鵝絨長袍又分成小塊送給來賓。當然,“表演”的內容不止于此,他們當著來賓的面,拿出剛回到威尼斯時穿的破舊而又顯厚重的蒙古袍,用刀把衣服劃開,大量的紅寶石、藍寶石、翡翠、珍珠紛紛滾落,耀眼奪目。三人看著滿座親朋的驚訝之色,露出了滿足的笑容。從此,人們把他們的住宅稱為“百萬宅”,馬可·波羅被稱為“百萬君”。
當時的威尼斯也不太平。1298年,威尼斯與熱那亞兩個城邦國家爆發戰爭。作為擁有戰船并富甲一方的商人,馬可·波羅家族必須參加戰斗。不幸的是,威尼斯戰敗,馬可·波羅被俘,被關進了熱那亞的監獄。他在獄中結識了一位名叫魯思梯謙的作家。兩人一拍即合,決定由馬可·波羅口述,魯思梯謙筆錄,寫一本記錄馬可·波羅游歷東方的游記,這便是后來的《馬可·波羅游記》。

書成之后,當即遭到質疑,因為當時的歐洲還無法相信書中提到的東方奇聞,比如他們難以理解為什么“黑石頭”能夠燃燒,等等。1324年,已經70歲的馬可·波羅行將就木,親朋好友們為了他的靈魂可以上天國,要求他取消書中的奇談怪論,可馬可·波羅一刻也沒有遲疑地回答:“我未曾說出我親眼看見的事物的一半。”
事實上,直到馬可·波羅去世后,人們才漸漸了解到《馬可·波羅游記》的重要價值:這本書不但對元朝的城市描寫詳盡,對中亞經新疆而至上都的陸上絲綢之路也有詳細記載,還對日本、南洋群島、印度、斯里蘭卡、波斯灣、阿拉伯海等國家和地區有所描繪,堪稱13世紀關于東方和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
1375年,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監制的喀泰蘭地圖的東亞部分,借鑒了《馬可·波羅游記》中的記載;15世紀時,意大利的航海家哥倫布精讀此書,并由書中指引,試圖到東方探險,但大海茫茫,他無意中闖到了美洲。哥倫布還以為自己到了馬可·波羅書中所稱的東方,把古巴島當做日本,把墨西哥當做書中所稱的“行在”(杭州),把生活在美洲的當地人稱為“印度人(Indians)”,也就是“印第安人”。
哥倫布去世后,歐洲人才意識到美洲是一個“新大陸”,由此,新航路開辟,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人類也由此從原來的分散孤立開始走向集中聯合。
馬可·波羅用一場橫跨歐亞的漫長旅行,一本看似天方夜譚的精彩游記,在無意中,讓世界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