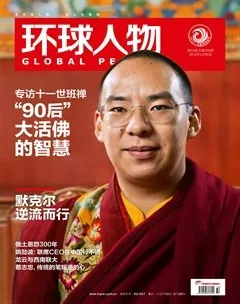江一燕,“消失的”演員
人物簡介:江一燕,1983年生于浙江紹興。2007年主演電視劇《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2015年憑《四大名捕》獲華鼎獎最佳女配角。今年舉辦個人攝影展,獲美國國家地理攝影大賽“華夏典藏獎”。
《環球人物》記者見到江一燕,是在北京798藝術中心。傍晚,夕陽鎏金,不遠還有展館里傳來的吉他彈奏。江一燕素面朝天,幾顆雀斑是常年前往非洲和山區的“紀念品”。見到記者,她對身邊的助理輕聲說:“給我一張吸油紙。”
“這些年你常演驚悚片、懸疑片、動作片,但看起來你本人和這些角色反差挺大。”記者說。
“我愿意去演一些性格很強烈的人,因為覺得生活很普通,在戲里刺激一點,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才有意義。演戲不要做生活里的人。”

江一燕最近一次“不做生活里的人”,是在懸疑片《消失的兇手》中,飾演越獄女囚傅源,與劉青云飾演的警官斗智斗勇。這部片子是3年前香港電影金像獎得獎大戶《消失的子彈》的續集,是編劇專門為當年與獎杯失之交臂的江一燕量身打造的。然而,11月27日該片上映前,卻因提前在網絡點映遭受院線集體抵制,排片率一度為零。
辛苦完成的作品險遭擱淺,江一燕滿腔不甘,在微博上發文號召“別讓電影消失”,她說:“每部電影有它自己的命運,但拍電影的人都是為此拼了命的。”
再也不想本色演出
初次見到江一燕的人,大概都會覺得她是個典型的江南女子。有段時間《天天向上》熱衷于采訪“各省美女”,提到浙江時貼出的標簽是“美和才”,說那是自古盛產美女和才女的地方,走出了西施、林徽因,埋葬了蘇小小、謝道韞。紹興人江一燕是那一期的嘉賓,又唱歌又彈吉他,一集下來,江南女子的靈氣鋪滿整個演播廳。
然而,江南女子并不好惹。前不久,江一燕接受一個網絡媒體采訪,主持人小心翼翼地追問她出了名隱晦的戀情,就好像面對一個易碎的瓷瓶。江一燕卻毫不通融:“公開戀情這種事兒,不是我的性格,將來也不會發生。”
一面是三春之桃的明媚,一面是九秋之菊的清素,想來,一個15歲就敢獨自“北漂”學舞的女孩,內心必然要有某種強大。
這種強大表現在,她從不奢望躲在出色的外形里,做一個大眾臆想中的清純女孩。2007年,她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碰到一部名叫《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的電視劇。導演沈嚴是當時電視圈紅人,靠一部《中國式離婚》聲名大噪。他看到江一燕就把她定為女一號周蒙,一名對愛情充滿美好想象的大學生。“其實我更想演女二號,還主動申請,因為那是一個非常叛逆的女孩。”而男主角陳道明認為江一燕的形象更適合女一號,最終,在導演和陳道明的堅持下,江一燕還是出演了周蒙。
《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講述了佟大為飾演的李然和三個女孩的愛情故事,描繪了年輕人面對現實和理想時的困惑與選擇。江一燕的清純外形讓人眼前一亮,成功從當年的新人中突圍。“但是,經過了那一次,我再也不想本色演出了。”
2011年是江一燕徹底轉型的一年。先是在話劇《七月與安生》中扮演頹廢、漂泊的安生,又在《四大名捕》和《消失的子彈》中扮演蛇蝎美人。對于這種轉型,有“粉絲”覺得浪費了她的形象,是“無處安放的清純”,但江一燕并不覺得可惜,她說:“我應該更豐富。”那一年,她還出演了陳沖導演的微電影《非典情人》,電影講述了一段婚外情,江一燕的角色風情又孤傲。
“和女導演合作有種私密的感覺,能夠講很多秘密。因為是陳沖,所以我從來沒去考慮尺度或者時間的問題。”電影中,江一燕一頭短發,口罩遮住半張臉,眉宇間竟有當年陳沖演“小花”時的影子。
更相似的是眼神里散發出的野心,她和陳沖,都是那種外表如水,內心洋溢,從不肯把自己禁錮在當下的人。
想在非洲開旅店
江一燕兒時生活的紹興,是一個一碟茴香豆、一壺花雕酒就能過一下午的小城,既悠然又文藝。她從小看的是烏篷船與越劇班子,聽的是魯迅、蔡元培、馬寅初等大師的故事。

文藝青年江一燕從不掩飾自己對三毛的崇拜,那些關于流浪的故事,那些陰郁又自我的語言,是少女最不可拒絕的心靈桑拿。“我對于流浪,對于音樂,對于非洲的念想,大概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可以說,三毛就是我流浪的種子。”
種子漸漸萌芽,14歲的江一燕每天想的就是如何離開這座時光靜止的小城。她想:這可是出了秋瑾的地方,我不能這么安生地過一輩子。一年后,她獨自一人北上求學,在北京舞蹈學院附中學習音樂劇。“那時就開始早戀,和弦都沒學完就寫特別反叛的歌,唱搖滾,把老師都看傻了,想象不到那樣的歌詞會是從我的嘴里唱出來的。”那時候她的老師是歌手郝云,兩人骨子里都叛逆,能說到一起。郝云聽了她的作品,對她說:“你應該繼續堅持。”
“這個鼓勵讓我很受用,后來哪怕做了演員我也堅持寫歌。”在話劇《七月與安生》里,江一燕自己創作了一首《愛情香煙》,艷驚四座。后來,郝云一見她面就問:“寫了多少歌了?”
她很驕傲地回答:“好幾本呢!”
成名不久,江一燕就背起行囊挎著單反去了非洲,完成少女時代的夢想。她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那種蒼莽,無拘無束,天地間的寬廣,會讓人知道自己多渺小,煩惱多渺小。”從此之后,定期去非洲拍攝成了她的習慣。“如果哪天不拍戲了,我就去非洲開一家旅店,打開窗就可以看到大象的那種,那是我夢想的生活。”
她拍火山,燙得手起泡;拍草原,整天被巨大的蚊子包圍;拍星空,被沙漠夜晚的寒風凍得瑟瑟發抖。“我拍東西不是技術派,而是從感覺上來。”一次,她看到一只小鳥停在斑馬身上,四下無聲,萬籟俱靜。“那時天特藍,草原一片金色,特別和諧。”彼時,她衣服上沾滿泥垢,內心卻被擦拭得一塵不染。
這張照片入選了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如今正掛在她的個人攝影展上。
不愿被過度消費
最近,江一燕因為支教被媒體大肆報道。8年間,她每年都會去廣西巴馬縣的小學支教,在那兒待上一段時間,給孩子們上課,陪他們過節。
2006年,導演王浩一來找江一燕,請她去廣西拍《寶貴的秘密》,“當時他還忽悠我,說那里風景特別好,去了肯定就美得不想走了”。江一燕一到那兒,才發現是一片窮鄉僻壤,洗澡都成問題。
拍戲在一所簡陋的小學,很多小孩都是走近兩個小時的山路來上課的,還有一些學生,因為學校太偏、家里太窮輟學了。“當時有個小男孩,整天跟著我,一見面就笑呵呵的,看起來特別陽光。后來有村民跟我說,‘小江老師,這個男孩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日子特別苦’。那一刻我特別難受,他這么小,就知道要把最樂觀的一面傳遞給別人。”江一燕說著就哽咽了。
回到北京,她開始給那所小學寄物資,后來一次回去,學生們從天蒙蒙亮就開始等,有的還從別的山頭連夜趕來。他們拉起橫幅歡迎,用的還是去年一塊布的另一面。從此,江一燕每年都會來和孩子們同吃同住,挑選了很多志愿者、“粉絲”一起來支教。“那時覺得,物資對他們來說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們更需要真心的陪伴。”
當記者問道:“為什么不請媒體過去做做宣傳呢?”江一燕表現出了明顯的抗拒和警惕。“都市里的人看多了復雜的人和事,能分清很多善惡,但山里的孩子不會。我希望能在他們成長的時候多留給他們一些純凈的東西,所以我會拒絕很多媒體,在挑選志愿者時也會嚴格把關。”
“其實我做藝人也是這種心態,有時想和媒體保持一點距離。現在藝人的私生活被過度消費了,這對藝人、對公眾都不太好。請留給我們一點空間,網上說的事情你們別太當真。”她的語氣,就像是一張拒絕進入的警戒令。
記者提醒她,這樣的“銅墻鐵壁”是走紅的死穴,她表現得無所謂,說:“我是個沒有計劃的人,很多東西越刻意越不可得,就像沙子,握得越緊流得越快。”
這種“無所謂”,也許正是內心強大、獨善其身的一種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