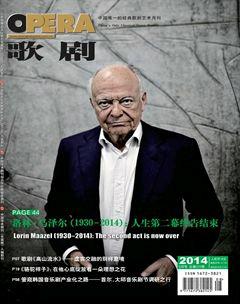《一個美國士兵》“開庭”再敘已故駐阿華裔新兵受辱事件
謝朝宗


2011年10月3日的夜晚,駐阿富汗軍營里的華裔新兵陳宇暉(Danny Chen)被發現中槍死在放哨的碉堡里。據軍方調查認定為自殺,動機不明,但指出他在駐扎期間,曾被長官及同僚過度體罰和以帶有種族歧視性的語言侮蔑。這個結果引起他在紐約的家人以及華裔維權團體的激憤,要求軍方徹查到底。兩個月后,軍方起訴八名與陳同部隊的軍人,包括其直屬長官,其中四人最終面臨軍事法庭的審判。
這個事件經由住在紐約的華裔作曲家黃若和劇作家黃哲倫寫成歌劇《一個美國士兵》(An American Soldier),今年6月由華盛頓歌劇院的“美國新歌劇計劃”演出。這是一個才發生沒多久的事件,對許多人來說仍然記憶猶新,這出戲給人們帶來相當赤裸裸的感覺,加上陳宇暉的家人以及倡權人士都是兩場演出的觀眾,他們的情緒擴散,更增加了現場演出的張力。
黃哲倫表示,最早是一直持續關注案情發展的美華協會會長歐陽蕭安找他寫一部舞臺劇,好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故事。雖然他對這種“紀實劇”(Docu-drama)沒有很大的興趣,但又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當黃若談起要找個歌劇題材時,他就建議了這個故事。“因為歌劇需要的是戲劇化的故事、強烈的情緒、粗獷的色彩,”他說,“這個故事有的正是這些。這不是一個關于錯綜復雜的人性,或評判道德對錯的故事,它有的就是最直接的情感。”
黃哲倫也指出,這個故事在對錯上或許很容易分辨,要把這樣一個剛剛發生的事戲劇化,難度仍是不小的,這是因為“劇本得要有虛構故事的所有要件,像是劇情架構轉折、人物發展等,而且又要讓不知道這個新聞事件的人看得懂來龍去脈”。他們最后決定以第一次軍法審判作引子。以法庭戲的形式為框架,用回溯的手法呈現,并引入陳宇暉的鬼魂,給他一個發聲的機會。
法庭審訊過程以及陳宇暉在軍隊里受操練凌辱的詳情,黃哲倫取材于新聞中的報道。陳宇暉的父母是臺山新移民,他在紐約的唐人街長大,中文都不太會講,一心想要融入美國社會,因此盡管已經申請到大學,仍決定棄文從武,當兵報國。沒想到進了軍中,還是因其種族膚色而被盯上,他被以“秦佬”、“娘娘腔”、“龍小姐”等輕蔑的言詞辱罵,又被特別操練,像是口里含著水做扶地挺身、一邊出操一邊被同僚踢。黃哲倫說這種“想證明自己是美國人,卻因此更加突顯其異類特征”的悲劇,長期以來都發生在美國亞裔身上。在作證的兵士中,他又排入一個非裔,說自己也曾被叫作“黑鬼”,顯示種族歧視在軍隊里相當普遍。
出場的人物,除了與審訊有關的法官、檢察官、證人(由四個演員分飾12個角色)、和被告外,另外就是陳宇暉的鬼魂與他媽媽。母子兩人與法庭的關系都是既身在事中,又身在事外——陳宇暉是死去的靈魂,陳媽媽則是因為不能參與軍法審判,而且又不懂英語。正因如此,他們所唱的,都是他們內心的想法,這和其他角色純粹是外在的言語形成對照。這或許也是為什么,在人物塑造上,這兩人最是鮮明。黃若說歌劇創作期間,適逢他第一個兒子的出生,讓他對母子情深有更深刻的體會,所以特別在歌劇里創造了兩者互動的機會。
在音樂上,黃若以不同的音樂語言區別每個角色,軍人和法官的臺詞很短促直接,唱的也是類似口語的宣敘調,而且充滿不協合音程,洋溢金戈鐵馬之氣。這個音樂在陳宇暉被眾人擲石頭的場面達到最尖銳最刺耳的高潮。男高音安德魯·斯坦森(Andrew Stenson)飾演的陳宇暉的唱段比較接近詠嘆調,不過申訴的都是他不被主流社會認同的悲傷。女中音楊光飾演陳媽媽,一開始的音樂也是比較陳述性的,直到結尾審訊結束,她終于接受兒子不會再回來的事實,才有長段的詠嘆調,最后則是一首搖籃曲,讓歌劇結束在一個比較柔和的尾聲上。楊光說,在審訊的過程中,陳媽媽一直忍著悲傷參與。所以她的音樂,不該只有柔軟,也要表現出她的堅強。
黃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音樂的作用旨在加強戲劇性,刻畫人物個性。歌劇時長約60分鐘,樂團編制是小型的室內樂,使用的14種樂器,除了京鑼外,全都是西洋樂器,由史蒂文·賈維(StevenJarvi)指揮。黃若說他尋求的是中西有機的結合,而不是單純的摻雜在一起。一開始的庭訊,所有人物一起唱著“威武”出場,顯示了這不純是一個完全現實的場面,而是有些超現實想象的成分,因此引入陳宇暉的鬼魂也就理所當然。當陳宇暉在向朋友解釋他為什么要從軍時,樂團奏出鑼鼓點,則是要傳達他住在唐人街的背景。
導演大衛·保羅(David Paul)以簡單的可以推出推進的布景,及燈光打在舞臺不同的部位,讓場景可以作快速轉換,但法庭的主景始終保留在舞臺上,明顯標示出這是故事發生的時空點。
這是黃若寫的第二部歌劇,第一部是《中山·逸仙》,7月在圣達菲歌劇院作美國首演。兩部作品都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黃若說一方面是巧合,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覺得歌劇應該要傳達音樂之外的意義,陳宇暉的悲劇不應該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