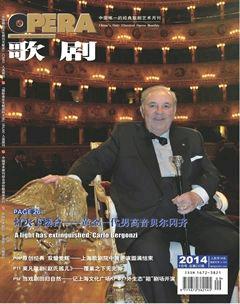文化沙漠中的綠洲
司馬勤
在我的印象中,我每一次到訪圣達菲歌劇院,都跟中國主題的劇目有關。回想2007年,譚盾的歌劇《茶》在圣達菲舉行美國首演。再之前,是2003年盛宗亮歌劇《毛夫人》的世界首演,這部歌劇為中國的前任“第一夫人”添上了肖斯塔科維奇筆下《麥克白夫人》的色彩。
今年7月,我重返圣達菲,目的是觀賞另一部中國歌劇的美國首演:黃若的《中山·逸仙》。而當我準備這次旅程之際,我特意多騰出幾天時間,希望在那里盡量多看幾場演出。本年度圣達菲歌劇院的常規劇目,還包括分上下兩部分的莫扎特《劇院經理》(Impresario)與斯特拉文斯基的《夜鶯》(Rossignol)“雙聯劇”。兩部作品很少出現在舞臺上,更談不上放在一起演。于是我抱著好奇心,還在演出前聽了講座,希望可以多了解些這個制作的淵源。觀眾剛進場,主講者就問了一句:“你們今天來到歌劇院,都是為了看那部‘中國歌劇,對嗎?”
要知道,雖然《夜鶯》來自丹麥的童話家安徒生的手筆,配上斯特拉文斯基與斯蒂芬·米圖索夫(Stepan Mitusov)的俄國唱詞,這部歌劇的故事卻發生在中國。情節是這樣的:一只賦有音樂天分的鳥兒(當然由女高音飾演),從死神(通常讓女低音飾演)的魔掌中救回中國皇帝。作品是俄國式融匯音樂與舞蹈的獨特劇種:有人形容《夜鶯》為“加上歌唱的芭蕾舞”,也有人稱它為“加上舞蹈的歌劇”。而我們身在的圣達菲歌劇院,院方會比較著重哪一半,大家應該都心里有數吧。
《劇院經理》卻是十分德國的混合體,舞臺上的演員“說的比唱的多”。1786年,莫扎特為了維也納宮廷創作這部富有娛樂性的小品,故事取材于后來流行的“后臺喜劇”的雛形:一位歌劇制作人為了讓演出得以順利進行,盡力安撫爭相斗法的幾位“大腕”明星。如果我們認為莫扎特的音樂比較單薄——他只譜寫了序曲、兩首詠嘆調和兩首合唱——那只能說原本的劇本更顯單薄。很多年前,重新制作該作品的手法是:導演改編顯得過時的對白,有時候甚至還會編出全新的情節。今天的現代導演則會盡量減少對白,讓莫扎特的音樂可以盡快陸續“登場”。
但圣達菲版本的《劇院經理》卻反其道而行之。導演邁克爾-喬勒特(Michael Gieleta)把這兩部短歌劇放在一起別有用心,大家需要時間與耐心方能領略其中的妙處。莫扎特原劇中薩爾茨堡劇院的經理弗蘭克先生(Herr Frank),現在換成了流亡巴黎的俄國人尤里-尤素普維奇(Yuri Yussupovich)。而原劇中的制作投資者赫爾茲先生(Monsieur Herz)也同樣被改頭換面,搖身一變成為奧圖-馮·德-普夫(Otto van der Puff)。投資者最大的希望,就是讓他最愛的女高音可以參演。原來的赫爾茲夫人(Madame Herz覡在成了瓦拉達·瓦拉迪米熱斯古(Vlada Vladimirescu),從夫人“貶為”情婦。瓦拉達與另一位女高音阿德琳娜-沃茨杜羅_甘巴倫基(Adellina Vocedoro-Gambalunghi,該姓氏的英文意思是:金嗓子-長腿)激烈爭辯良久,看看誰可以在宣傳海報上壓倒對方,居于首位。
后來我們發現,他們策劃的歌劇制作是——《夜鶯》。
喬勒特的概念中有不少亮點,只可惜演出時,本應引起共鳴的巧妙包袱卻沒有得到觀眾的回應。舞臺上出現過多陳腔濫調、半生不熟的笑料(讓歌劇演員擔任喜劇演員更是在表演上大打折扣),重填的歌詞配不上音樂的韻律,甚至與莫扎特那些自然美妙的樂句背道而馳。莫扎特這位古典大師懂得在老調子上加上帶有諷刺的新歌詞,娛樂觀眾之余又可以“騙到”他們。而演出當天。我猜莫扎特在自己那個沒有標志的墳墓里備受折磨。
中場休息后登場的則是《夜鶯》。作品的連貫性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我們應該把這個問題歸咎給斯特拉文斯基。當年,作曲家創作第一與第二幕之間。經歷了藝術生涯中的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就連今天的我們聆聽這部作品,都可以感覺到,第一幕的創作人是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旗下一位具有天賦的學生,而第二幕卻預示著那是一位很快將以《春之祭》改變世界的作曲家。
盡管如此,喬勒特仍十分努力地把制作統一化,起碼,把不同的戲劇線索編織起來,讓我們感覺到兩部歌劇合并后的整體性。最起碼,演員在兩部歌劇中都相繼出現。比如說,男中音安東尼-邁克爾斯_摩爾(Anthony Michaels-Moore)在上半場演劇院經理,到了下半場把大衣脫下,搖身一變為斯特拉文斯基的中國皇帝。其他演員同樣從容地轉換角色——女高音艾琳·莫爾利(Erin Morley)與男高音布魯斯·斯勒德治(Bruce Sledge)的地位都攀升了——兩人本來只是歌唱家與喜劇演員,到了下半場則擔綱夜鶯與漁夫的重要角色。而我認為,參與斯特拉文斯基的《夜鶯》時,眾演員更被善用,得以更好的發揮,雖然制作從整體來說更像配上強烈視覺效果、演出出色的音樂會,而不是完整的戲劇作品。如果純粹從數學計算來表示,《夜鶯》只是各等同部分加起來的總和,沒多沒少。多少有點令人失望。
從統計學來說,要把歌劇制作現代化,不必勞駕阿道夫·希特勒。但是,正如羅伯特·卡森(Robert Carsen)的《指環》四聯劇(四年前曾由科隆歌劇院在上海演出),除了納粹標志以外,所有關于納粹歷史的元素都擺上舞臺。斯蒂芬·瓦德斯沃斯(Stephen Wadsworth)執導《菲岱里奧》(Fidelio)(這是歌劇首次在圣達菲亮相)的時候,卻好像四川廚子大灑辣椒一樣,讓舞臺各個角落都貼上納粹標志。
大家記不記得,當年正是因為德國歌劇蒙上了納粹的陰影,才促使導演尋找新的藝術方向,把故事背景遷移至現代?這樣不是很諷刺嗎?
無需多言,把貝多芬畢生唯一一部歌劇的場景遷移至納粹集中營,當然引起了一些爭議——《紐約時報》的評價是“令人作嘔”——盡管這個手法讓故事、布景與道具都變得徹底現代,但瓦德斯沃斯所領導的制作卻勾勒出了一些傳統制作無法呈現的細節。endprint
女扮男裝這類橋段,基本上是令人發笑的舞臺手法。貝多芬那個嚴肅至極的故事主線——深愛丈夫的萊奧諾拉假扮菲岱里奧,為了從獄中救出愛人弗洛雷斯坦——往往因為獄官的女兒愛上菲岱里奧這個次要情節,讓人分心而不能完全投入“嚴肅”的故事里。可是,導演把背景改為納粹集中營,使得任何輕松的情節都頓然失去任何可笑的余地。一個到了現在還令人悲傷的戰爭背景,讓觀眾更感覺到瓦德斯沃斯關注每個角色,使得我們更明白貝多芬那個年代“革命”與生離死別是如何嚴肅的話題。
從音樂上來說,這次演出成功,歸功于歌劇院首席指揮哈里-比克特(Harry Bicket)。雖然樂團沒有用上古典時期的老樂器,但比克特為樂團注入了他那熟練的古樂演奏技巧,沒有把貝多芬的音樂過分交響化。
因此,演出效果極佳,盡管演員之中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駕馭管弦樂團的聲量。保加利亞女高音亞歷斯·蓬達(Alex Penda)扮演的萊奧諾拉/菲岱里奧(演員的原名是Alexandrina Pendatchanska,這次用上的縮寫剛好讓名字變得中性)既有感情又有張力,她并非炫耀什么音量與歌唱技巧。而男高音保羅-格羅夫斯(Paul Groves)演繹的弗洛雷斯坦更像一個浪漫主義者,不只是擁有一股英雄氣概。
我覺得這種手法制造出了更成功的敘事效果。因為節奏明朗,情節推動有力,這個版本的《菲岱里奧》變成一部具有可信性的戲劇,而不只是舞臺上出現寥寥幾個演員以及貌似錯位的交響樂演出。
因為本來擔綱黃若歌劇《中山·逸仙》男主角的莫華倫臨時退出(他已經身在圣達菲排練,但最終因為一些原因取消演出)。找來了替補演員約瑟夫·丹尼斯(Joseph Dennis)——他是圣達菲歌劇院年輕演員計劃的成員。本演出季,丹尼斯被安排飾演《菲岱里奧》中的第一囚犯。一夜之間,他像個跳高選手,登上現代中國精神領袖的寶座。這一則小插曲,再次讓圍繞著歌劇發生的事,使得舞臺上所展示的歌劇藝術本身失了顏色。
就像劇中主角的現實經歷一樣,《中山-逸仙》在國外得到的尊重,遠比在他自己的國土多得多。歌劇是香港歌劇院委約,原定于2011年10月1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世界首演。可是,歌劇的北京首演在8月底宣布取消了。院方也沒有詳細解釋“延期”的原因。后來歌劇在香港舉行的演出——以民族樂團伴奏的版本——變成作品的世界首演。雖然首演通過電視轉播。也有人找到過DVD,但沒有一家中國歌劇院愿意搬演《中山·逸仙》。
正因為圣達菲歌劇院院長查爾斯·麥凱(Charles MacKay)在報紙上看到北京把《中山-逸仙》“延期”的新聞,他開始關注這部作品,并且詢問美國首演事宜。他聽過紐約市立歌劇院的錄音(VOX計劃曾經試演歌劇的第一幕),也參與2012年在古根漢姆博物館與亞洲協會舉行的“創作中作品”(works-in-process)座談與示范。于是,麥凱決定把歌劇院的資源投入這部本應由西洋管弦樂團伴奏的歌劇作品。
我們真的應該給他們“點贊”,《中山·逸仙》在圣達菲的美國首演備受矚目,與它在中國受到的冷落剛好形成兩極對比。世界首演時導演陳薪伊處理的那些令人討厭的反美政治宣傳,在這個版本中消失了(我當時已經覺得很奇怪,認為這種處理手法并不合適,因為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量捐款都是從美國來的)。還有,某些樂段也被刪掉了(有一些音樂在紙上顯得合情合理,可是搬上舞臺后才發現阻礙劇情的進度)。
所以,剩下的部分更加到位,無論在舞臺處理、樂團(黃若刪減了某些過分響亮的器樂段落的配器),還是唱詞。本來,黃若創作的樂句配合編劇莊梅巖的唱詞,聽起來的效果更像一段又一段的詠敘調。經過圣達菲的排練與實踐,指揮關琦安與幾位華裔演員調整了各個段落的速度。把詠嘆調與宣敘調區分。讓我們聽得出段落之間的節奏感。男低音龔冬健飾演宋嘉澍,帶動了歌劇的戲劇性。袁晨野飾演孫中山的摯友梅屋莊吉,營造出了比較輕松的場面。
來自西方的演員因為不懂中文,在演繹時只能著重優美的旋律。他們普遍的方法是:塑造旋律的線條性,咬字方面則退而求其次。這樣來看。女中音瑪麗安·麥科米克(MaryAnn McCormick)飾演的倪桂珍,烘托丈夫宋嘉澍,富有戲劇性張力。女高音科琳·溫特斯(Corinne Winters)飾演的宋慶齡,代表了整部歌劇的感情核心。她一方面點燃了孫中山這位革命家的愛意。另一方面成為她父親與丈夫關系決裂的楔子。顯然,宋慶齡演唱的段落最為優美。在處理角色方面,她懂得讓深情的演出引出角色的優雅氣質。
導演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的構思——包括寓意“在建設中的中國”的竹棚子——沒有增添或減少故事的敘事性,在某些地方更顯得像個框架般,特別恰當。孫中山的裹足原配由女高音麗貝卡·維蒂(Rebecca witty)飾演。她同意離婚的時候唱出了動人的詠嘆調,聲稱來生寧愿嫁個“普通人”而不是一個到處奔波的革命家。革命家在舞臺上也有機會在美妙的布景襯托下,形成奪目的視覺效果。在歌劇最后的高潮,孫中山的銅像在舞臺升起,男主角提示觀眾他推動了革命,“當中失敗總不下20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說這番話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香港人。
在圣達菲看《中山·逸仙》唯一令人覺得遺憾的。是找不到一個令人信服的孫中山。丹尼斯富有才華——他無論音高或節奏都把握得很好——但是有時候,總覺得他好像是在演另一部歌劇,特別出戲。我們當然要欣賞這位年輕演員在短時間之內接受這個挑戰的勇氣,在舞臺上唱他聽不懂的語言。但是,當一個高達20米的孫中山銅像在他身后出現,這種隱喻對于丹尼斯來說,讓他顯得特別渺小。就像劇中人當年曾被任命為臨時大總統一樣,丹尼斯的“崗位”,也只是臨時性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