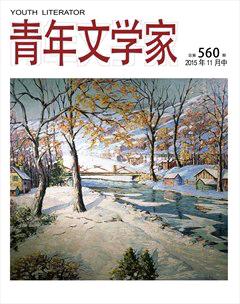美國環(huán)境文學生態(tài)思想的流變與批評
趙俁 楊林
基金項目:2014年遼寧省社會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項目名稱:生態(tài)批評視閾下的詩歌美學建構研究,項目編號:L14BWW005;中國外語教育基金,項目編號:ZGWYJYJJ2014Z30。
摘 ?要:美國環(huán)境文學是針對工業(yè)化發(fā)展模式與控制自然思維的批判,主要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60年代開啟了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第一階段,環(huán)境文學主題圍繞歌頌自然之美,揭露環(huán)境危機,倡導環(huán)境保護展開,試圖喚醒人們熱愛自然、尊重自然、回歸自然的生態(tài)意識。20年代至今是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繁榮期,弘揚環(huán)境正義是這一時代的主旋律。基于歷史發(fā)展脈絡,試圖理清美國環(huán)境文學發(fā)展的流變,從而建構“自然性、整體性、交融性、主體間性”四位一體的美國環(huán)境文學批評范式。
關鍵詞:環(huán)境文學;流變;批評;環(huán)境正義
作者簡介:趙俁(1966-),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楊林(1979-),男,河北滄州人,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從事英美文學與西方文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2-0-03
引言:
法國哲學家薩特把文學理解為一種介入模式,文學不僅介入政治與社會,而且要全面介入人類整個文化之中。美國工業(yè)化推崇經(jīng)濟第一、物質至上、消費核心的發(fā)展觀,無疑造成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無限掠奪與人與人之間的物化。19世紀中期的美國是以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類健康為代價來滿足工業(yè)化發(fā)展,西部荒野伴隨著西進運動的步伐不斷被工業(yè)操控,自然脫去了原始魅力。針對工業(yè)化造成的環(huán)境與生態(tài)危機,美國環(huán)境文學誕生,并彰顯其批判鋒芒。文學介入環(huán)境危機之中,企圖喚醒人類熱愛自然、尊重自然、回歸自然的生態(tài)意識。美國學者內茨利在《環(huán)境文學:一部關于環(huán)境文學作品、作者及主題的百科全書》中認為,環(huán)境文學囊括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體裁,環(huán)境文學不僅表達作者游歷感受的游記及傳授地球生態(tài)知識,而且試圖影響和改變讀者審視自然界的方式[1]。美國著名環(huán)境文學批評家勞倫斯·布伊爾提出了界定環(huán)境文學的四個標準:第一,非人的環(huán)境不僅作為框定場景在場,而且將人類歷史隱含于自然歷史在場之中;第二,人的利益不被理解為唯一合法的利益;第三,人對環(huán)境的責任是文本中倫理價值取向的一部分;第四;環(huán)境是作為一個過程存在的,而不是一種永恒不變或約定的存在[2]。中國學者龍娟認為,環(huán)境文學是一種以散文、小說、詩歌、戲劇等傳統(tǒng)文學體裁為載體,以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基本內容,以弘揚生態(tài)思想、環(huán)境道德、環(huán)境審美情趣等為主要價值導向的文學樣式或思潮,它具有融合文學、生態(tài)學、環(huán)境倫理學、環(huán)境美學等多學科視角、思想、理論和方法的總體特征。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發(fā)展主要經(jīng)歷了兩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分水嶺。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環(huán)境文學誕生及初步發(fā)展的第一個階段,荒野意識、自然書寫、地方倫理等主題貫穿其中,旨在弘揚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正義。20世紀60年代至今是美國環(huán)境文學發(fā)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是美國環(huán)境文學繁榮期,不僅文學體裁靈活多樣,而且主題不斷深化。主題不僅停留在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而且擴展到以環(huán)境為中介的人際正義。
一.美國環(huán)境文學發(fā)展的第一階段:歌頌自然之美、揭露環(huán)境危機、倡導環(huán)境保護
美國環(huán)境文學發(fā)展的第一階段主要以非小說的散文形式歌頌自然之美,揭露環(huán)境危機,倡導環(huán)境保護。斯拉維克視梭羅為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先驅[3]。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家包括亨利·大衛(wèi)·梭羅、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喬治·珀金斯·馬什、約翰·威斯利·鮑威爾、約翰·繆爾、約翰·伯勒斯、瑪麗·奧斯丁、奧爾多·利奧波德等。梭羅、愛默生歌頌自然之美,馬什、鮑威爾揭露環(huán)境危機,繆爾、奧斯丁、伯勒斯、利奧波德倡導環(huán)境保護。梭羅和愛默生從超驗主義角度看待自然,賦予自然神性,歌頌自然之美,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反對工業(yè)化對自然無情地開采、踐踏與控制。梭羅在《瓦爾登湖》中生動地描寫了作者親自回歸自然的簡樸生活,過著人與自然融合的接近原始狀態(tài)的生活。梭羅在評價瓦爾登湖生活時這樣說:“這是一個秀色可餐的晚上。我的整個身體只有一種感覺;我每一個毛孔都流淌著喜悅。作為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我獲得了一種奇怪的自由感[4]”。在梭羅眼里,人融入自然才能獲得自由,工業(yè)化般的駕馭自然是人類的牢籠,因而梭羅大聲疾呼:“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全全世界[5]”。作為一位環(huán)境文學家,愛默生把自然視為上帝的啟示,自然是神性的外衣。他的作品彌漫著歌頌自然精神的基調,其筆下的自然萬物都具有神靈與魂魄。在愛默生看來,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類,從而愛默生猛烈地抨擊以犧牲自然為代價的工業(yè)化道路。馬什、鮑威爾用細膩地筆觸揭露了自然環(huán)境的破壞,環(huán)境危機意識是其作品的主導精神,他們試圖通過環(huán)境危機意識改變人們的思想與行為。馬什在《人與自然》中考察了人類活動對自然造成的影響,認為人類大規(guī)模生產和交通體系破壞了自然和諧,分析了人類行為對動植物、林地、湖泊、沙漠造成的消極影響,從而揭發(fā)環(huán)境危機,并敲響了人類反思自我與自然他者的辯證發(fā)展的危機意識。鮑威爾在《美國干旱地區(qū)的土地報告》和《科羅拉多大峽谷》中揭發(fā)了工業(yè)文明過渡開發(fā)和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危害,主張環(huán)境應與發(fā)展統(tǒng)一起來,否則人類環(huán)境將持續(xù)惡化,后果將一發(fā)不可收拾,人類伊甸園將永不復存在。繆爾、奧斯丁、伯勒斯、利奧波德等美國環(huán)境作家在其作品中積極倡導環(huán)境保護的重要性,并積極投身美國環(huán)境保護運動中,為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繆爾在《我們的國家公園》中號召美國人去旅行,從而喚醒人們的環(huán)保意識。他說:“走進大山就是走進家園,大自然是一種必需品,山林公園和山林保護區(qū)的作用不僅僅是作為木材與灌溉河流的源泉,它還是生命的源泉[6]”。繆爾發(fā)起了小規(guī)模的環(huán)境保護運動,并用環(huán)境文學極力地倡導環(huán)境保護的重要性。奧斯丁在其環(huán)境文學代表作《少雨鄉(xiāng)》中探索了沙漠生態(tài),呼吁人們保護沙漠生態(tài),改變征服沙漠的態(tài)度。伯勒斯不僅書寫自然,而且積極參加環(huán)境保護運動。《醒來的知更鳥》栩栩如生地描寫了鳥類生活,寄希人與動物友好相處,呼吁生態(tài)保護,強調環(huán)境保護有利于人類在地球上生存與發(fā)展。利奧波德是一位具有環(huán)境倫理學家身份的美國環(huán)境文學家,他的代表作《沙鄉(xiāng)年鑒》被譽為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的圣經(jīng)。美國環(huán)境文學第一階段主要針對工業(yè)化和西進運動帶來的環(huán)境負面影響書寫熱愛自然之聲,鼓勵人們與自然建立生命共同體意識,恢復人與自然和諧的伊甸王國。總而言之,美國環(huán)境文學第一階段主題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歌頌自然之美、揭露環(huán)境危機、倡導環(huán)境保護三個方面,同時為環(huán)境文學繁榮發(fā)展的第二階段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
二.美國環(huán)境文學發(fā)展的第二階段:環(huán)境正義
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環(huán)境文學進入了繁榮期,70年代地球日的游行活動,80年代建立的山嶺俱樂部、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無疑推動了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發(fā)展。美國環(huán)境文學第二階段文學主題思想為環(huán)境正義,主要代表人物為羅賓遜·杰弗斯、蕾切爾·卡遜、巴里·康芒納、約翰·麥克菲、愛德華·阿比、加里·斯奈德、萊斯利·馬蒙·西爾克、溫德爾·貝里、凱蒂·李、比爾·麥克基本等。環(huán)境正義是人們在認識與處理與環(huán)境問題過程中體現(xiàn)出的一種正義,主要分為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和以環(huán)境為中介的人際正義,這兩方面的正義構成了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基本內涵。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主要體現(xiàn)為人類開發(fā)利用自然的權利和保護維護自然的義務之間的關系,人類應尊重愛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并平衡發(fā)展。正如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概念所闡釋到,土地倫理是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xiàn)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重。1962年,蕾切爾發(fā)表了《寂靜的春天》,此書驚醒的不僅是美國,甚至是整個世界,因而《寂靜的春天》被奉為現(xiàn)代環(huán)境運動的肇始和億萬人的生態(tài)入門書。卡森控告化學控制法——殺蟲劑、農藥、化肥等的應用致使富有生機的小鎮(zhèn)失去了活力,變得毫無生氣。針對化學控制論造成的人與自然的失衡,卡森提出了生物控制法。生物控制法是基于對有機體及其所依賴的整個生命世界結構的理解而獲得的昆蟲控制方法,也就是說,力求將一種昆蟲力量轉用來與昆蟲自己作對,即利用昆蟲生命力的趨向去消滅它自己。《寂靜的春天》包含的環(huán)境危機觀、自然平衡論和新行動主義無疑關注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把人類思想引導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融的倫理關懷之中。美國環(huán)境文學家愛德華·阿比不經(jīng)盛贊自然之美,而且強調自然非功利的價值。他在《大漠孤行》中把沙漠視為地球上最美麗的地方,并認為自然萬物都有其本身的美和價值,這種價值并不是人類自己設計的。
以環(huán)境為中介的人際正義是美國環(huán)境文學第二階段關注的焦點之一,同時也是人與自然之間正義的延伸,并觸及到社會正義層面。美國環(huán)境文學家認為,人類共同生存在地球上,形成了命運共同體。不論種族階級和性別等差異,所有的人在享受環(huán)境權利的同時都應該承擔起相應的保護環(huán)境的義務,否則就會導致環(huán)境非正義現(xiàn)象滋生蔓延,環(huán)境危機愈演愈烈,最終使得人類無處棲身[7]。美國環(huán)境文學家反對人們以破壞環(huán)境的行為相互侵害人與人在環(huán)境面前的利益,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環(huán)境文學家眼中的人們不僅包括當代人,而且還包括后代人。康芒納特別關注以環(huán)境為中介的人際正義,在《封閉的循環(huán)—自然、人和技術》中,康芒納認為一部分人使用汽車,排放有毒的物質并把有毒的一氧化碳和鉛加在人體之上,每年都要殺死成千上萬的人。一部分人使用汽車的權力無疑傷害到了其他人,破壞了人與人應有的環(huán)境正義。麥克菲在《對自然的控制》一書中揭發(fā)了因對自然過渡開發(fā)而造成對他人傷害的罪行,譴責了人與人環(huán)境非正義的惡劣行徑。一些人過度開發(fā)自然資源,造成了水土流失,破壞了植被和河道,因而導致泥石流的爆發(fā)。泥石流的爆發(fā)不僅毀壞了環(huán)境,同時還給當?shù)鼐用裨斐闪松kU。麥克菲強調人類熱愛自然,并試圖捍衛(wèi)人與人之間的環(huán)境正義。無論是人與自然的環(huán)境正義,還是人與人的環(huán)境正義,美國環(huán)境文學要義就是弘揚自然的價值,突破經(jīng)濟主義的羈絆,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樊籬,重塑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共生的局面。
三.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批判維度
美國環(huán)境文學第一階段主導思想是歌頌自然之美,揭露環(huán)境危機,倡導環(huán)境保護。第二階段是第一階段的延續(xù)與深化,其主導思想是環(huán)境正義。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批評視角主要分為四個方面:第一是生態(tài)審美的自然性原則;第二是生態(tài)審美的整體性原則;第三是生態(tài)審美的交融性原則;第四是生態(tài)審美的主體間性原則。美國環(huán)境文學以上四個批評原則目的是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建立平衡的、多元的、有機的批評范式。自然性原則認為美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自然感受過程。環(huán)境文學家對自然審美的目的不是自然命名化、自然抽象化、自然意識形態(tài)化,而是自然本身的美及其對這種美的感知過程。梭羅說:“在這裸露和被雨水沖刷得褪了色的大地上,我認識了我的朋友[8]”。繆爾把植物稱為植物人,動物被他稱為有毛的兄弟。愛德華·阿比甚至把河流稱為兄弟。自然性原則不是人對自然的工具化、控制化的過程,而是帶著敬畏平等的心態(tài)去聽、看、聞、觸對生態(tài)系統(tǒng)整體性的影響。生態(tài)整體性原則必須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觀,進入生態(tài)整體主義審美的高度。批評與審美不僅僅局限在文學藝術和優(yōu)美如畫的自然觀,而是將感知擴展到整個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便是整體原則的體現(xiàn),正如美國環(huán)境文學家杰弗斯寫道,完整是一個整體,是最大的美,生命與物質的有機體,是宇宙最神圣的美,熱愛它們,而不是人類[9]。交融性原則是建立在生態(tài)主義聯(lián)系觀之上,生態(tài)審美批評不是站在高處遠遠地觀望,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自然,有時候,特別是在審美的初期,甚至是需要忘掉自我,與自然融為一體[10]。交融性原則就是拋開自我,融入自然,開放全部感官,不作他想,全神貫注地感知身邊的一切,接受、領略、感悟自然的智慧。卡森認為,人不能發(fā)現(xiàn)自然的奇妙是因為人類過于自大,把自然當做工具和對象化的自我。斯奈德嘗試融入自然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凝神靜觀,即放下思想重負,放空自我,從凝神靜觀到了然開悟,一步步接受自然智慧的引領。主體間性原則是指人不僅要與整個大自然發(fā)生關系,而且要與具體的、個別的自然物發(fā)生關系。主體間性原則就是要跳出主體與客體、文化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建立相互友好的平等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主人與仆人、征服者與被征服、控制者與被控制的關系,而是互為主體性的平等友愛關系。人類的人性不只存在于我們自身,而是更多地存在于我們與世界、自然的對話中。生態(tài)自然性原則、生態(tài)整體性原則、生態(tài)交融性原則、生態(tài)主體性原則建構了美國環(huán)境文學批評的基本框架,形成了生態(tài)審美的原則與立場,并為美國環(huán)境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四.結語
美國環(huán)境文學以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作為出發(fā)點,在文學歷史上豎立了一座綠色的精神殿堂。在這座綠色的精神殿堂里,人類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美國環(huán)境文學在歷史流變和審美批評兩方面彰顯了熱愛、尊重、保護自然的鋒芒,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喚醒了人們的環(huán)保生態(tài)意識,推動了人類文學與文化的綠色發(fā)展。美國環(huán)境文學發(fā)展的第一階段強調歌頌自然之美,揭露環(huán)境危機,倡導環(huán)境保護。環(huán)境文學介入工業(yè)化與商品化的社會發(fā)展中,批判人們對自然的控制與過度開發(fā),啟發(fā)人類走出自我中心主義、經(jīng)濟主義、功利主義、工具理性的桎梏,熱愛擁抱大自然。美國環(huán)境文學第二階段圍繞環(huán)境主義主題展開,環(huán)境正義分為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和以環(huán)境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正義。環(huán)境正義把美國環(huán)境文學提升到了社會倫理的高度,并樹立了一盞精神明燈。美國環(huán)境文學在其流變中始終圍繞著生態(tài)自然性原則、生態(tài)整體性原則、生態(tài)交融性原則、生態(tài)主體間性原則而展開,彼此交相輝映,共同譜寫了美國環(huán)境文學審美與批評的維度。自然性原則就是尊重自然,把自然視為人類生命的共同體。所以說,美國環(huán)境文學引導人們認識自然的獨特價值,開啟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真諦,并使文學踏上了一條生態(tài)綠色之路。
參考文獻:
[1]Patricia D. Netzley.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n Encyclopedia of Works, Authors, and Themes[M]. California: ABC-CLIO, 1999:8.
[2]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7-8.
[3]Scott Slovic.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251.
[4]亨利·梭羅. 瓦爾登湖[M]. 徐遲譯.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8.
[5]Henry David Thoreau. Walking[M].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534.
[6]約翰·繆爾.我們的國家公園[M]. 郭名倞譯.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
[7]龍娟. 美國環(huán)境文學:弘揚環(huán)境正義的綠色之思[J]. 長沙: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5):108.
[8]Bradford Torrey & F.H. Allen.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6:275.
[9]麥克基本. 自然的終結[M]. 孫曉春等譯.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77、211.
[10]王諾. 生態(tài)批評與生態(tài)思想[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