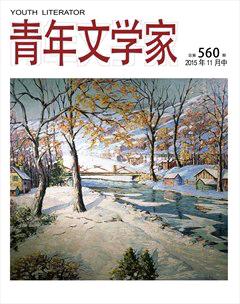托妮·莫里森小說中的暴力主題與瘋女人形象
郎文君
基金項目:西華師范大學2013年校內基本科研業務費科研資助專項項目“對托妮.莫里森小說中的暴力文本及其現實意義的研究”(416239)階段性成果。
摘 ?要:美國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說中暴力主題的描寫十分豐富,本文在梳理莫里森這一寫作特色的文學淵源及其現實基礎的前提下,著重闡述了《寵兒》和 《秀拉》這兩部小說中母弒子這一極端暴力行為及其表現意義。
關鍵詞:托妮.莫里森;暴力主題;《寵兒》;《秀拉》;母弒子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2-0-01
暴力是一種激烈而強制性的力量,它基于人類最原始的沖動,因而它常常成為被稱作“人學”的文學的描述和探討對象。作為文學創作核心的語言不止于模仿或再現現實社會,更重要的是它的創造力。因而,文學中的暴力文本應通過文學語言,運用藝術手法或技巧創造性地呈現暴力現實,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反思暴力,以實現暴力文本應有的社會道德功能,從而消減暴力在現實中的負面力量。然而,暴力并非人性的常態,它是人們無法表達自我時的一種極端訴說行為,普通讀者在超越暴力本身,解讀其背后的文本意義即“次文本”時,常常無法跨越情感共鳴這一文本閱讀的基礎階段,以致難以進一步理性地構建此文本。但西方文學中一直就保有暴力主題這一傳統,如希臘神話中有關美狄亞的故事、悲劇《俄狄浦斯王》、《麥克白》等。當代美國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更是繼承并充分運用了這一文學傳統,在她的作品中大量、集中的描繪暴力這一主題,從而構建起一個濃墨重彩的暴力世界,因而,對莫里森小說中暴力文本的研究是解讀其作品的關鍵。
莫里森筆下的暴力描寫具有堅實的現實基礎。奴隸制下白人對黑人的暴力隨處可見,并且自然的合法化。當暴力愈演愈烈黑白種族間的沖突開始爆發并逐漸升級,處于暴力事件中心的非裔美國人民既是暴力的承受者又是暴力的發起者,[1]在暴力的漩渦中無奈地掙扎著。這一狀況在莫里森的小說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莫里森從不同的維度與視角描寫了暴力這一主題,包括謀殺、弒子、強暴、亂倫、縱火、自殘等。
莫里森的第五部長篇小說《寵兒》中的女主人公塞絲是一位黑人女奴,她曾經在肯塔基州一個名叫“甜蜜之家”的種植園。種植園主加納先生是一位較為開明的奴隸主。他死后加納太太請了她弟弟“學校教師”來管理,“學校教師”和他的兩個侄子嚴酷兇殘,對奴隸任意虐待,濫施暴行。為了追求自由,懷有身孕的塞絲開始了逃亡之旅。經歷了一路艱辛的塞絲最終到達了辛辛那提, 與婆婆及先前送出來的孩子們團聚。然而,二十多天后,“學校教師”帶領人馬追蹤而至。為了不讓孩子們回到種植園重新去過那種非人的生活,塞絲割斷了不到兩歲的女兒的喉嚨。
另一部莫里森的小說《秀拉》中秀拉的外婆伊娃結婚五年后被丈夫拋棄,留下三個孩子相依為命。為了養活孩子,伊娃故意讓火車軋斷了一條腿以領取每月二十三美金的撫恤金,從而撐起了整個家。伊娃唯一的兒子布朗嬰兒時因便秘差點死掉,她用僅有的一點豬油掏通了他的肛門救活了他。后來,布朗應征入伍,退伍之后,戰爭給他帶來的精神創傷使他沉溺于毒品,伊娃為了阻止兒子一直沉淪下去,在他身上澆上了煤油,眼睜睜地看著他燒死。
不可理喻的暴力行為使塞絲和伊娃瘋狂女性的形象躍然紙上。然而這些暴力籠罩下的瘋狂并不說明黑人女性天性兇殘,相反的,她們的暴力恰是源自深沉卻又無可奈何的母愛。在奴隸制下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屈辱生活讓她們意識到一個人的自由與尊嚴高于一切,與其卑微地活著不如尊嚴地死去,于是,她們都為最心愛的人做出了毋寧死的選擇,而讓自己背負起施暴者與瘋女人的罵名茍活于世,這樣的選擇與擔當正是以偉大母愛為原動力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當母愛只能以暴力的形式表現出來時,母親和孩子的生存境況可謂是陷入了絕境,消除這種異化的母愛必須從改善黑人的生存及精神環境開始,這也是莫里森透過母弒子這一暴力主題想要傳達的重要信息之一。
莫里森的另一部代表作《最藍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渴望自己有一雙白人的藍眼睛,她認為只有這樣,媽媽才不會厭惡自己,才會像疼愛白人小主人那樣疼愛自己,而生活的其它方面也都會因之得到大大的改善。然而不幸的是,一切并沒按照她所期盼的那樣發展,她的父親在恍惚中強奸了她,媽媽更加厭惡她、常常打罵她,最后,為了錢,騙子牧師邁卡·惠特科姆聲稱自己能幫佩科拉獲得一雙藍色的眼睛,但她必須完成一項任務 ----將一塊有毒的肉那去喂一只老狗 。當皮科拉眼看著那只老狗吃了有毒的肉之后在地上痛苦地掙扎并最終死去后,她嚇壞了。這次的驚嚇加上被父親強暴的經歷,使得佩科拉精神大受刺激,最終瘋了。追根溯源,佩科拉的瘋性源自白人主流文化及其審美標準對黑人思想的浸染與扭曲,源自在這一文化暴力下黑人社區及家庭內部的精神和肉體暴力。
莫里森小說中的暴力描寫挑戰著人們的閱讀體驗,更考驗著人們的反思能力,啟迪人們深思。從莫里森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暴力已經成為非裔美國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已成為其命運構成的必然因素,人們應該覺醒并深思:是什么使暴力這種人類非常態長期廣泛地存在于美國黑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隱藏在暴力行為和瘋女人形象背后深層的社會與文化根源,是主流文化對黑人民族心理的浸染和扭曲,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的長期文化積淀。
注釋:
[1]朱小琳:托妮.莫里森小說中的暴力世界,載于《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