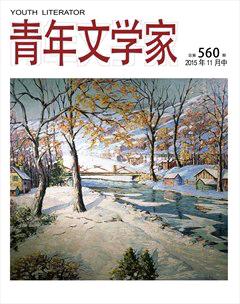南洋華僑與福建基督教會經費自主模式探析
摘 ?要:福建作為“僑鄉”,在國家對外交流和經貿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嘗試簡略勾勒民國時期福建教會經費自主模式和其壯大和發展過程,探討福建基督教會與南洋華人教會組織和信徒之間的關系,進而對當時時代背景下,二者互動中,對以基督教為紐帶發軔的一系列交流與合作做一個更好地探尋。
關鍵詞:華僑;經費;基督教
作者簡介:諶暢(1991-),江西南昌人,暨南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6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2--02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非基督教”運動伴隨著中國民族主義運動高漲呈風起云涌之勢。為應對時局,中國基督教會發起了“三自”運動。經費自主作為“三自”的先決條件,對本土教會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福建教會憑借“僑鄉”優勢,緊密與南洋教會聯系,使改良教會經濟成為可能。當下研究中,李雙幼,朱峰,李少明,張鐘鑫,顏白瑜等人的成果或多或少與近代閩南教會和東南亞華人教會有關[1],但關于福建教會探尋經費自主模式與南洋華僑聯系尚留有空白。筆者試圖通過史料分析,利用一手檔案資料,對福建教會經費自主模式進行考察,尤其重視探討福建教會與南洋華僑的關系,以期對整個基督教會在華發展狀況有全面了解。
一、福建教會的重要地位
基督新教于1842年首傳福建廈門,此后大半個世紀,雖然歷經坎坷和挫折,但作為西教東來最早的幾個地區之一,在西方差會和中國本土教牧的共同努力下,福建教會在信徒人數、教牧數量、教堂數目上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由于山地阻隔、語言不通、經濟落后、思想保守等原因,閩西地區的教會事業發展舉步維艱,與閩南閩中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這導致了福建教會發展的不平衡。瑕不掩瑜,“就基督教勢力而論,本省被認為最興旺之省區,全省各縣均有基督教宣教事業,1/3的縣都有一個以上的差會。據報告,到1920年,福建全省基督教正式教堂的總數已達到965座,而同年全國基督教正式教堂總數為4726座,全省只有六個縣無正式教堂。”[2]細分來看,福建受餐信徒共計38584人,占全國第三位,受薪人員中,西傳教士為454人,中國職員為外國職員八倍。[3]
因此,探究福建教會追求自立、壯大、發展的過程,就是試圖發掘閩教會典型性,以便達到先進帶動后進的歷程。同時,由于福建教會在國內教會中居于重要地位,探求其經費如何自主就顯得極為重要。
二、福建教會追求經費自主的努力
如何使異質的基督教會融入中國主流社會,做到經費自主,一直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本土牧師的共同追求。
閩南教會牧師蔡受恩在1932年提出,“教會經濟何以無法籌備?不是全由教友不明受托責任,不肯捐錢;乃是因為多數教友過于貧苦的緣故。救濟之法,獻策如下:1.教友須各有職業,教會故當倡設半工半讀學校。2.教友有職業者須輸十一捐于教會。3.教友須送子弟入教會學校讀書,其出路為傳道、教員、醫生、農工商業。欲為青年求出路,務須培養訓練他們的才識。4.教友中資力較厚者,須量能設立各種機器廠或工業學校,多容納教友工作,一面也可以訓練子弟。”[4]
同年閩南閩中聯合修養會上,一些利于教會經費自主的方法也由與會代表提出,主要可以歸納為培養教會領袖,開大演講會,由會友收入中抽取自養基金,多設義務傳道等幾個方面。[5]
西方差會也審時度勢,將教會資產和財政自主權逐步移交給中國本土教會。以美國公理會為例,其在1928年的《美國公理會工作移交與閩中大會》中,明確表示將閩中區域內該會產業近乎無償移交與閩中大會,作為條件,閩中大會必須將差會移交的產業,開展與基督教相關的教育、醫療和傳道等事業。[6]
為減少福建教會內耗,避免不同教派之間的紛爭,保存教會經費自主的成果,教會人士提出不少建議, “1.我們真要建設我們的本色教會;2.教會聯合統一,消除門戶宗派之見; 3.為建設新中國而工作;4.我們應有耶穌批評偽善、斥責罪惡、清潔圣殿的精神;5.我們不要徒托空言,一定要實行耶穌的教訓;6.我們要為大眾而工作,為勞苦的大眾而工作。”[7]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有了中國牧師的獻計獻策,使得整個福建教會的經費自主取得了很大進展,西方差會的配合也利于閩教會工作的開展。閩教會化除畛域,更使教會經費自主落到實處。
一言以蔽之,福建教會追求經費自主的過程中,雖然歷經坎坷,但仍取得了一些成績。同時,它并不把視野局限在國內,積極與外界溝通協作,巧妙借助外力來發展自身。
三、福建教會與南洋教會的交流與合作
眾所周知,福建作為我國近代著名僑鄉,福建華僑從沒割舍與家鄉的聯系。他們像廣東五邑的很多金山客一樣,將積攢的血汗錢寄回家鄉,用于幫襯親人生活,并且積極參與僑鄉的各項建設。據廈門大學林金枝教授研究,福建僑匯在民國年間一直保持著一個較高水準,在整個福建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8]華人教徒在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他們以教會為紐帶,以基督教為媒介,為福建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助力。
首先,南洋基督教會在如何增加教會經濟,增強教會活力上為閩教會樹立了良好的榜樣。葉谷虛在1941年中華基督教會馬來亞大會上表明,“……已籌款購進柔佛州附近市區肥沃耶園二百十八英畝,預算月產椰果三萬枚,依現價可售四千余元,除開支費外,全年可得凈利刀幣三萬元左右,以供自養經費……”[9]葉牧提到的這種具體增加教會收入的方法做到了因地制宜,為閩教會籌集經費提供了實例。此外,南洋教眾還在經濟上直接給予閩教會支持, “馬來亞大會前任主席,郭老牧師來函稱,因時局關系,五月[宣教主日]專號的公報,延至七月始收到。大會遂即通知各堂會,學校,訂于八月七日分別舉行宣教主日,收績頗宏,所有獻款,均得按時匯至總會。”[10]泉州教會主席許錫安表示,“一年中對外對內所有措施,及向南洋信僑募捐救濟泉城貧苦會友情形,區會納吳炳耀舉議,應令各堂照前二十六年議案繳常年捐以充會費。”[11]反映當閩教會在遇到困難,教徒遭受不幸時,南洋教會始終是其堅強后盾。
同時,福建教會竭盡全力,將所屬牧師派往南洋,進行宣教活動,并將國內合一教會的組織、結構、規章等傳入南洋,盡力整合南洋基督教勢力。
由此可以看出,在民國時期,雖然閩教會與南洋教會的交流雖很大程度上居于被幫助的位置上,但福建教會也將其一些經驗輸出南洋,二者的互動是雙向的。
四、小結
福建教會充分發揮“僑鄉”優勢,在積極依托南洋教會完善自身,探尋教會經費自主模式的同時,不忘向南洋教會輸出自己的理念,以圖達到依靠南洋教會,又能反哺對方的目的。探尋二者的交流與合作,對于當下我們制定僑鄉宗教政策有一定借鑒意義。
注釋:
[1]具體參見李雙幼:《近代閩南基督教會研究》,李少明:《近代福建基督教的兩大重要地位》,張鐘鑫:《本土化與信譽重建—泉州地區基督教會研究(1857-1949)》,《新加坡華人基督教史初探(1819-1949)》,朱峰:《當代東南亞華人基督教淺析》,《殖民地處境下的華人基督教——以近代東南亞華人社會為例》,顏白瑜:《近代福建基督教傳教策略的轉變探析》。
[2]基督教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歸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3,1190-1191頁。
[3]基督教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歸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上冊,第169,171頁。
[4] 蔡受恩:《建設自立教會的一個小獻議》,參見《公報》,1932年,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教會檔案,U102-0-68。
[5]《閩北閩中聯合修養會之討論結果》,《公報》,1932年,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教會檔案,U102-0-68。
[6]《美國公理會工作移交與閩中大會》,《公報》,1928年,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教會檔案,U102-0-67。
[7]《新壇》第二卷第五期,1949年,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教會檔案,U102-0-62。
[8] 參見林金枝:《略論近代福建華僑匯款》,《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03期。
[9]《公報》,第二十卷,第八期,1948年,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教會檔案,U102-0-74。
[10]《公報》,第二十一卷,第八期,1949年,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教會檔案,U102-0-76。
[11]《中華基督教閩南大會常委各區會議錄》,1940年,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教會檔案,U102-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