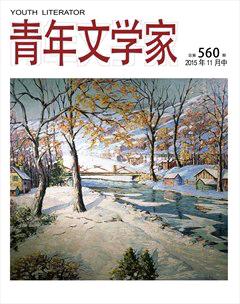亂世求用 進退自如
呂敏
摘 ?要:根據史料梳理山濤之行跡,無論從家世背景或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為官濟世”思想都穿插于他浮浮沉沉的一生。本文摒棄歷來從政治角度對山濤身仕二姓的非議,著重關注山濤的濟世情懷,對其作了一定深度的剖析和淵源探討,以期讀者對他心懷天下,積極入世的遠大抱負有進一步的了解,從而對山濤有更為中肯和深刻的認識,這無論從歷史或是現實方面來說都是極有意義的。
關鍵詞:山濤;濟世情懷;分析探究
[中圖分類號]:B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2--02
山濤作為魏晉竹林名士之一,人生方向和價值觀和其他“六賢”極有不同,因而歷來學界對他褒貶不一。有的學者從政治角度將其歸為趨炎附勢一流,例如趙明說:“在嬉笑怒罵中嘲諷了山濤之流的趨炎附勢,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愿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決心。”也有學者肯定了他的處世哲學和為人之道,贊同他的“以度為勝”。方南波說:“即使存有林下逸志,亦不妨享有廟堂之榮華。四時運轉不息,花開花落,無哀無榮,則人之進退出處,亦當與時屈伸,而不必執一。”筆者傾向于后者的觀點。山濤出生低寒,早年雖僅為一介布衣,但奮發濟世之志已顯露無遺,《晉書·山濤傳》記載:“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日:忍饑寒,我后當做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耳。”
山濤很早就有當作三公的抱負,他為實現政治抱負而積極入仕,這合乎傳統的儒家士大夫的邏輯志向。他為官后頗受好評,尤其是晉武帝多次下詔書,贊譽山濤的品性操節,將他樹為儒家道德典范,他的濟世情懷不容置疑的。但他處世風格卻與儒家所倡導的原則相悖,十分識時變并明智通變,似乎顯得人格有些“分裂”,這看似矛盾的人格事實上成功的將儒家入世思想和道家隱逸態度中和,加之山濤圓融而又方正的內心,正代表著中國傳統士人人格的精華,極具內涵,同樣也是山濤濟世情懷毫不動搖的人格支撐。
一、進
儒學世家的出身使儒家積極入世思想在山濤頭腦中根深蒂固,他的性格受儒學的影響明顯,重儒守禮,心系天下,有著博大的濟世情懷。
1、重儒守禮 盡心所事
山濤出生小族。史載:“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 “小族”出身顯然制約著山濤仕宦,據《晉書》記載山濤直到四十歲這一年才入仕始任郡主簿之職,在這之前山濤沒有顯赫的功績,仕途過程中逐級升遷的過程也表明他并沒有得到外力提攜。他早年就胸懷大志,有“當作三公”的抱負,后來也確實做了三公,歷任吏部尚書、司徒等要職。根據史料的記載,基本上可以推斷出他的思想是以儒家為主體的。儒家主張立德、立功、立言,要求盡可能為國家社會作貢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積極進取,入世有為。
山濤入世的思想濃厚,一生都為入仕積極思慮準備。然而過于周全的政治策略和世人對其“身仕二姓”的不理解讓大多數人歪曲了他的入仕動機,加之以“貪圖富貴貪生怕死”之名,習慣忽視山濤作為政治個體的自我政治訴求性。對此,山濤從未作過任何解釋和辯解,有一則史料倒可以窺探到他獨樹一幟的政治態度背后的真實心態——即山濤向晉帝薦舉蜀漢遺臣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晉泰始起居注載:“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后為令。”諸葛父子一生為蜀國肝膽涂地,實為忠烈之門。照常理講,晉朝滅了蜀國,忠義之輩應以死衛國,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因家仇國恨必定拒絕入仕晉朝,甚至應以死示其忠貞。恰恰相反,諸葛京接受了任命并忠心耿耿官至江州刺史。和山濤境地相似,這也涉及到了“仕二朝”的敏感問題。山濤對諸葛京的“盡心所事”最能理解,他認為諸葛京入仕晉朝是識天命的行為,專忠蜀漢,不仕二姓的偏執則有“不通變”之謬。山濤向士人傳達了這樣的暗示:效忠朝廷是順天命的正確抉擇,只有如此才可能實現濟世抱負,換做任何朝代都一樣,此時恰恰是晉朝而已。這并不是單純為自己仕晉作辯解。這種思想折射出廣闊心境實在不是人人可以理解。朝代變更只是歷史潮流,誰做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為每一代本質都相似的百姓。只要能徹底改變“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的悲慘局面,順應時局發展是施展政治抱負的必然選擇,這讓出身卑微山濤更加明白,人應當認識到“時變”而且明智地“通變”。
他認為治國成功的關鍵在于風俗的純正,人才的培養和選拔是安撫民心、教化風俗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他向來注重風俗教化,推崇王道政治,在述職生涯中,他盡心所事,尤其在人才的選拔和推舉上,公正嚴謹,頗得人心。據史料記載山濤作冀州刺史時:“冀州俗薄,無相推毅。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族命三十余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他利用自己在士林中的威望,在生平的選職工作中,盡心盡力為晉朝選拔杰出人才。每當舉薦某一職任的人選時,都對其人格作全面的介紹和分析,稱作山公啟事,在當時的人才薦舉工作上影響極大。正因此,晉王室才倚重他,正是希望他能夠安定士林,增強朝廷的凝聚力。司馬炎曾對他說:“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正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 巨源的舉止投足,都表明了他的一片赤誠和忠誠之心,為官之道也印證了他的濟世抱負。
2、借隱伺顯,心系天下
正始末到嘉平年間,大背景方面,司馬氏正忙于奪權,放松了對整個社會士人思想方面的控制,竹林七賢在這一階段正式形成。這時候的山濤隱身竹林,冷眼旁觀現實,思索自我如何順應歷史的發展,積極調整個人心態。依照山濤“作三公”的遠大抱負,他理應極關注仕途并往入仕這方面發展。然而他非但沒有表現出積極入仕的模樣,甚至走了反方向,朝隱士的路走去。這讓人疑惑,仔細剖析當時社會形態,從山濤的心理及后期仕途路線我們不難看出,此時的山濤明顯運籌著“借隱伺顯”的政治策略。
當時在以何晏、王弼為首的正始名士的倡導下,玄學——作為一種新型的學說開始彌籠于社會,這一學說主要是將老莊的道學和孔孟的儒學兩派雜糅中和,進而闡發出新的義理。山濤出生于中落的是儒學世家,可以推測有關玄學的文化素養積累的并不多。然而在玄學盛行的時期他接受了新思想并受熏陶,竟發現與自己的骨子里順時通的態度變大為相合,開始對這一學說興趣頗深。山濤知道,若要在玄學上達到更高境界,必須加緊鉆研玄學中的主體即老莊學說,才能更加靈活的運用學說支撐自我的人生準則。因此,他以隱的面貌避開現實后,將隱逸的全部時間都用來研讀老莊之學,談論老莊,效仿老莊。故史書記載:(山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鉆研玄學的人很多,自古通“老莊”之說名士多有文章作品,在闡發意義上用盡心思,因為僅僅靠捧讀老莊書籍,并不能闡發出令人信服新義理,就很難脫穎而出、成為為人稱贊的士人學者。據有限的史料我們已知山濤幾乎無作品傳世,他對于“老莊”學說可謂以心理解,以身實踐,和自身的儒家思想體系相得益彰,關于這點我們從山濤的履歷生涯清晰可見。因而山濤隱逸乃“以退為進”之舉,也是無奈之舉,源于亂世報國無門的惆悵和無奈。當他隱逸竹林時,一刻也沒有停止對如何再次入仕的思考。看似挺悠閑模樣下掩蓋了焦急的等待。他在苦苦地等待著,等待著仕運的降臨。晉書記載“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椽。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這時候到來的仕途之運,對他的夙愿抱負而言,雖不是什么大運,但不管怎樣,從布衣變為官身,山濤畢竟在仕途上走了一大步,也是關鍵的一大步,他的濟世抱負終于得以施展了。
二、退
進而有度,謹慎是山巨源的性格特征之一。他在曹爽與司馬氏惡斗之時避禍歸隱,等到曹爽集團潰敗,司馬氏取得絕對性勝利后才又復出為官,其政治進退和于時事、謹守“慎”字;山濤的官職生涯在不斷升遷,但他卻一直小心翼翼地處世,生活清廉謹慎,甚至飲酒從來都適可而止:“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遵道順時 合于世俗。據《晉書》本傳記載山濤“性好老莊,隱身自晦”,可以說老莊思想賦予了他游刃有余的處世能力,然而山濤的老莊思想又有獨特之處。《世說新語·賞譽》記載談玄領袖人物王衍對山濤的評價:“此人初不肯以縱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山濤從老莊基本的崇尚自然思想里提取了出具有辯證法的可操作思想因素:以不爭而爭,以進為退,以無生有,以虛求實,與世俗相合,完美地將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本體的融會貫通。又加之其寬厚,圓融之中不失方正的人格,這正是山濤濟世之志的思想體系基礎。
山濤從老莊崇尚自然的思想里,提取了出可用適用及可變之道,以求與世俗相符合。他多次的隱身自晦及后來有位居公候的名望,正印證了他對老子之言的贊同,《老子》說:“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持儒家入世思想為主體,實際運作老莊的“后其身,外其身”,二者的完美嫁接終成就其濟世思想。山濤對老莊思想的運用,處處可見,僅作幾例:
一、山濤汲取了老子通變的思想。認為個體本身是自然,身處的社會也是自然,個人的自然要順應社會的自然,才形成真正的自然整體,這才符合人生和社會的存在規律。嵇康被殺后,他薦舉其子嵇紹作秘書承曾對嵇紹說過:“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這句話體現了山濤對老子思想的借鑒和發揮,《老子》二十三有言:“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二者思想內涵不謀而合,山濤極為贊同這順時通變的原則。
二、山濤汲取了老莊以虛無為本,順應靜觀的思想。魏晉亂世,權力集團之間紛爭特別激烈,山濤身處紛亂的政壇爭斗之中卻從未讓這些爭斗傷及自身,這得益于他以虛求實,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此態度也來自于老莊思想的精華,《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稱道以虛靜的心境,靜觀人事糾紛,自己巋然不動的人生態度。山濤正是如此,處處以此為準。在司馬氏與曹魏集團之間,他能夠周全應對,從容穩重。司馬昭西征鐘會時,他鎮鄴以撫壓曹魏勢力,司馬炎登基時,他又護送陳留王至鄴。鐘會與裴秀爭權,他能皆與二人相交而不落怨恨。每一次朝廷舉薦,他都推選數人,然后看詔旨的趨向,再加以排列上奏。正因為此,環境再險惡,山濤卻安如泰山,始終處于有利地位。
三、山濤汲取了老莊的知止不殆的思想。他仕晉的三十余年中,多次向晉帝請退,即使是官位升遷的機會他都會誠懇推辭。何以至此?就是因為他參悟了老莊的以柔克剛,知雄守雌思想。《老子》有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山濤對此極有感悟,他升遷過程中的拒絕包含了真心求退的因素,更多的是他懂得這“退”是適可而止的抽身,是“不殆”必要基礎。
嵇康被殺臨死前對兒子嵇紹說:“巨源在,汝不孤矣。”其內心深處對山濤的信賴已昭然若示,絕交書中的絕情言辭頃刻間破碎。同時可證后人非議其人格,認為他既沒有嵇康的直率,也沒有阮籍的潔身自好,自失于圓滑證據實在不足。山濤的一生中從未做過悖逆本心的事。于官場,盡心盡力,清廉正直;于朋友,寬懷大度,重情重義;于家族,始終如一,光耀門楣。非議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流于表面化,并沒有深入到歷史人物思想品格的深層內涵。事實上,山濤的思想是一個圓融的體系,在這個基礎上,成就的是真實的山巨源——個亂世求用、進退自如,有著博大濟世情懷的魏晉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