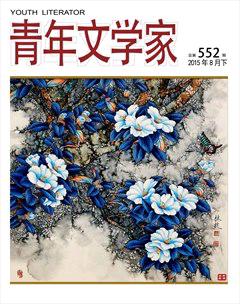論古米廖夫筆下的非洲主題
王娟
摘要:俄羅斯詩人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古米廖夫(1886-1921),以豐富的創作實績和深刻的理論思索被公認為阿克梅派的領袖。他自幼開始閱讀科幻、驚險小說,向往遙遠的國度,迷戀浪漫主義的功績。在高加索、梯弗里斯生活的幾年,參加打獵,進一步增加了他對動物的興趣。在他的詩歌創作當中,浪漫主義的氣質一直有所保留,除此之外,非洲主題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占據著相當大的比重,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枝絢麗的花朵。
關鍵詞:古米廖夫;主題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4-076-02
一、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古米廖夫幼時經常讀探險小說,這激發出了他冒險的熱情。他渴望征服、渴望探索未知,在去非洲之前,曾在詩集《征服者之路》(1905)中就寫道:“如同身穿鎧甲的征服者,/我走出家門,歡快地上路,/有時在快活林中休息投宿,/有時則被無底深淵阻隔。”他頌揚的是強者、是英雄、是具有剛強個性的征服者,他不喜歡安逸,而愿追求刺激,追求自然自由的野性生命力。《在途中》這首詩同樣塑造了征服自然與社會中必然要而臨重重險阻,只要有剛強的個性,不畏困難的勇氣,這樣才能得到“鮮花常開的園林”,實現自己的理想。
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1907年,他首次探訪非洲,游歷伊斯坦布爾、塞得港、開羅等地,創作了這首著名的《長頸鹿》:
今天,我看見,你的眼神特別憂煩
我知道不少神秘國度令人開心的故事,
玉手特別纖細,抱著膝蓋惆悵。
將黑膚色的少女,講年輕酋長的熱戀
請聽著:在遙遠的、遙遠的乍得湖畔
可你太久地吸入了污濁的霧氣,
有一只精美絕倫的長頸鹿在徘徊游蕩。
你不愿相信任何事物,除了雨雪冰霜。
長頸鹿生就一副優美的體態,秀逸的風姿,
我多么想給你講述那神奇的熱帶花園,
奇妙的斑紋把它打扮得更俏麗,
那挺拔的棕櫚,那奇花異卉的芳香……
敢同鹿紋媲美的唯有倒映的新月,
你哭了?請聽著……在遙遠的乍得湖畔,
那斑斑碎影在空濛的湖面搖曳。
有一只精美絕倫的長頸鹿在徘徊游蕩。
(中略)
這首詩一開始運用象征主義詩派慣用的通感于法,通過聽覺看到一只長頸鹿在乍得湖畔徘徊,將我們的視野拉到他營造的世界當中去,并將只能憑借嗅覺感知的奇花異卉的芳香也滲入到聽覺當中,各種感覺彼此溝通,講述著一個個動人的故事。在俄國文壇的象征主義時代,詩人通常運用通感來暗示性地展現與自然應和的精神世界,他們因為擁有這樣一種特殊的視力,能夠知聞彼岸的信息而被視作“半神”。而在古米廖夫看來,詩人充其量不過是個“于藝人”,通感僅僅是一種技巧,在他筆下的都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其中既有長頸鹿美麗外形和優美姿態,又有周遭環境的渲染,虛實相生,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副古老、寧靜的非洲乍得湖畔的美麗圖景,給人以清新明快之感。
二、明心見性,感悟人生
古米廖夫不僅直接描繪非洲的風景,而且將非洲的神話傳說作為自己的創作題材。特別是在他后來幾次游歷非洲之后出版的詩集《珍珠》《異域的天空》中,較之前崇高的、帶有夢幻色彩的浪漫激情,更多了他對現實世界的理解。
如《豹》的創作就是根據阿比西尼亞的迷信傳說“如果擊斃一只豹,而不立即燒盡它的觸須,它的靈魂就將追迫獵取它的人”而來的。主人公違反了這一傳說,將豹殺死卻未燒其觸須,最終抵不過內心的折磨,“在長頸鹿井邊/我來結束我的生命。”在這里,他借由神話傳說抒發了對勇于打破常規、敢于嘗試的人的惋惜,而這也促使他之后的態度的轉變:雖然仍想有所作為,但不再劍拔弩張。
又如《塞米拉米達 對英·費·安年斯基的光輝紀念》:
樹叢中有潤濕玫瑰的貯水裝置,
無處不歡欣,無處不明凈,
睿智的祭司,舞女,奴仆,
清新靜寂,令人心曠神怡。
毛茸茸的天藍色苔蘚遍地皆是,
但是每當夜幕降臨,月神
還有水、氣、火、土四元素。
總那么可怕地俯向大地。
清新靜寂,令人心曠神怡。
我不禁想從這七百肘長高處
一躍而下逃離開花園。
在這首詩的副標題中寫道“對英·費·安年斯基的光輝紀念”,安年斯基是聯結俄國普希金時代審美標準和現代實驗派詩歌的橋梁。他所任職的皇村中學,被譽為俄國詩人的搖籃。作為皇村中學的校長,安年斯基把對于詩歌的熱愛之火傳遞給他的學生們,他的美學立場對于古米廖夫產生了很直接的影響。塞米拉米達是半神話式人物,傳說她曾征伐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創建巴比倫,修建空中花園。這首詩正是以塞米拉米達的功績來紀念安年斯基。
這首詩也是古米廖夫對他婚姻家庭生活的感悟,1910年古米廖夫和阿赫瑪托娃結婚。他們的婚姻就像空中花園一樣,是人人羨慕的,正如“清新靜寂,令人心曠神怡。”一樣,是俄國詩壇的一段佳話。可是當夢想的月光照進現實中,他們的婚姻也就像無根基的空中花園一樣,在這段婚姻當中他是痛苦的,讓他“不禁想從這七百肘長高處/一躍而下逃離開花園。”
三、獨具匠心,以求創新
古米廖夫是將異域題材引進俄羅斯詩歌的詩人,在他富有異域風情的詩歌當中“非洲主題”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除了與他自身對科幻、探險產生的濃厚興趣、多次遠方游歷相關,非洲主題的詩歌更是他對現實世界獨特的感受力的表現。瓦·勃留索夫評論古米廖夫1910年出版的詩集《珍珠》時,說他“生活在一種臆想的,差不多是虛幻的世界中。詩人仿佛對現實生活格格不入,而自己為自己創造了一些國度。安排在這些國度里棲息的也是他所創造的生物:人、野獸、惡魔。在這些國度中,也可以說,在這些世界中,各種現象所遵循的并非通常的自然法則,而是詩人授意施行的那些新的法則;在這些世界中,人們也不是按照通常的心理法則生活和行事,而是按照作者這位臺詞提示人告知的那種奇特的、令人大惑不解的想入非非的主意生活和行動”。
在深層意義上,非洲主題的詩歌為俄羅斯詩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打破了象征派渲染的神秘虛無的天國世界。古米廖夫1913年在《阿波羅》第一期發表了《象征派的遺產和阿克梅主義》-文。他堅決反對象征主義的宗教神秘主義和虛無主義,指出象征主義存在的種種危機現象,聲稱取代象征派的是新流派即阿克梅派,主張用男性的堅強而明晰的視察和活潑的感覺來接觸世界。在處理“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時,它要求“更多一些力量的平衡和更準確的知識”。非洲主題的詩歌創作正是古米廖夫為阿克梅派同象征主義爭論的一種手段,他以果敢的個性獨游非洲、接觸非洲,在非洲古老的土地上獲取靈感,以客觀具體可感的物象來追求原始生命力的美,在現實的基礎上建立其美學大廈。
在俄國,安年斯基是重視談論民族文化風格重要性的人,他認為,要想建設民族文化,首先要確立俄羅斯話語的風格。受安年斯基的影響,阿克梅派素來將自己當做現實世界中文明的當然傳人,有意識地把自己當做聯系俄國和西方世界的一個中介環節。古米廖夫在其包括非洲主題在內的異域題材的詩歌也有深深的印記,并將自己的目光放眼世界,俄羅斯地跨歐亞,處于東方與西方兩種文化的交匯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決定了俄羅斯不可能單獨成為歐洲國家,也不可能單獨成為亞洲國家,體現在其詩歌當中就是代表兩種文化的意象同時出現。如在《非洲之夜》中寫道“幫助他們的是黑曜石/幫助我們的足貼身的十字架”,黑曜石是非洲原始部落的飾物,也是佛教佛珠的制作材料之一,十字架代表的則是西方文明,在詩中同時出現,詩人以這種方式承認,這種獨特的文化交融與結合正是俄羅斯的特點與不可重復性。
小結:
古米廖夫的詩歌創作將筆觸伸向了當時鮮為人知的非洲,這既是他對具有冒險精神、剛強個性的肯定,也是他對現實世界的獨特感受。他以獨特的視角為俄羅斯詩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俄羅斯話語風格的確立和世界文學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