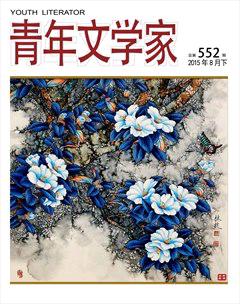從創(chuàng)傷理論視角解讀《最藍(lán)的眼睛》
徐楠
摘要:托尼·莫里森是美國(guó)當(dāng)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作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她時(shí)刻關(guān)注黑人的生存困境和民族命運(yùn)。她的代表作《最藍(lán)的眼睛》,以獨(dú)特的視角反映了白人文化統(tǒng)治下的美國(guó)黑人悲慘命運(yùn)。而主人公彼克拉是小說(shuō)中最具悲劇色彩的人物形象。本文將結(jié)合創(chuàng)傷理論來(lái)分析彼克拉所承受的身心創(chuàng)傷,探究其創(chuàng)傷的來(lái)源及所造成的影響。從而更深入地了解美國(guó)黑人的生存狀況。
關(guān)鍵詞:心理創(chuàng)傷;彼克拉;黑人文化
【中圖分類號(hào)】:I106【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5)-24-079-02
托尼·莫里森的處女作《最藍(lán)的眼睛》發(fā)表于1970年,小說(shuō)一經(jīng)出版就引起了學(xué)者和讀者的廣泛關(guān)注。小說(shuō)中,主人公彼克拉作為一名黑人小女孩,她認(rèn)為只要擁有一雙藍(lán)色的眼睛就能得到父母和他人的尊重與寵愛(ài)。但美好的夢(mèng)想終將敗給殘酷的現(xiàn)實(shí),來(lái)自家庭,種族以及宗教的創(chuàng)傷對(duì)她的身心均造成了重大的打擊。在這三重創(chuàng)傷的迫害下,她產(chǎn)生了痛苦而又復(fù)雜的創(chuàng)傷癥狀,同時(shí)也深陷于女性身份、文化和民族認(rèn)同的危機(jī)中,最終只能在瘋狂中尋求解脫。作者在小說(shuō)中,將彼克拉塑造成創(chuàng)傷壓抑下的受害者,在錯(cuò)綜復(fù)雜的事件和人物關(guān)系中,展現(xiàn)了黑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對(duì)其悲慘命運(yùn)的深刻同情。
“創(chuàng)傷”一詞最初來(lái)源于希臘語(yǔ),一方面指身體創(chuàng)傷,即由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身體損傷。另一方面,指的是心理層而,即某種強(qiáng)烈的情緒傷害所造成的心理?yè)p傷。“創(chuàng)傷”一詞原本是醫(yī)學(xué)詞匯,在1996年,美國(guó)學(xué)者卡西·卡魯斯在《沉默的經(jīng)驗(yàn)》中首次給予“創(chuàng)傷”文學(xué)含義。隨后,創(chuàng)傷理論與心理,文化,歷史,和政治等方而相結(jié)合,不斷發(fā)展與完善。在心理學(xué)方而,心理創(chuàng)傷往往會(huì)帶來(lái)生理、認(rèn)知、情緒以及行為方面的不同表現(xiàn),如虛弱麻木,思考緩慢,焦慮恐懼溝通困難等等。
1.家庭創(chuàng)傷
弗洛伊德作為心理創(chuàng)傷理論的領(lǐng)軍人物,他認(rèn)為創(chuàng)傷有三個(gè)成分,即童年早期經(jīng)歷的事件的記憶,青春期后經(jīng)歷的事件的記憶及后期經(jīng)歷事件觸發(fā)的對(duì)早年事件的記憶。而在《最藍(lán)的眼睛中》中,小說(shuō)主人公是一位11歲的黑人女孩,她的童年生活就是極其不幸的。來(lái)自家庭的創(chuàng)傷給她的身心造成了極其嚴(yán)重的傷害,對(duì)她的價(jià)值觀念以及行為方式均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她母親波莉給予彼克拉不是關(guān)愛(ài),而是負(fù)而的因素,冷漠、暴力、輕視。同伴嘲笑彼克拉的相貌,作為母親,她并沒(méi)有幫助彼克拉建立自信或是給予安慰,她同樣認(rèn)為女兒相貌丑陋,這種否定態(tài)度造成了彼克拉審美觀念的扭曲,在壓抑中,不切實(shí)際的愿望也越發(fā)強(qiáng)烈。同時(shí),波莉在與丈夫喬利爭(zhēng)吵廝打時(shí)絲毫不顧及彼克拉的感受,暴力場(chǎng)而往往會(huì)盡收眼底。因此,彼克拉在家庭生活中感受不到溫暖和關(guān)愛(ài),更多的是暴力壓抑與痛苦。在小說(shuō)的第三部分,有這樣一個(gè)情節(jié):彼克拉不小心將餡餅打翻在地,滾燙的糖漿將她燙傷,沒(méi)有得到母親的安慰與幫助,卻得到了一番謾罵與毒打。“布里德洛夫太太一把把她拽起來(lái),又朝她打去,一面用氣得變成尖細(xì)的嗓音罵著佩科拉……傻瓜……我的地板,一團(tuán)糟……看你干的好事……滾出去……現(xiàn)在就滾……”母親波莉?qū)⒈丝死度氲娇謶峙c無(wú)助的深淵中,而對(duì)待哭泣的白人小孩,給予的卻是溫柔的話語(yǔ),耐心的安慰。“別管她們,寶貝。”“她那甜蜜的嗓音和湖而上落口的余暉相輔相成,十分和諧。”這種鮮明不公平的對(duì)待,將會(huì)給彼克拉的內(nèi)心造成揮之不去的傷害。
與其冷漠強(qiáng)勢(shì)的母親相比,彼克拉的父親喬利帶給她的創(chuàng)傷更為致命。作為一名父親,他毫無(wú)家庭責(zé)任感,醉酒、厭世、暴力,同時(shí)他也喪失了愛(ài)別人的能力,不知道如何與自己的子女交流給予他們關(guān)愛(ài)。對(duì)于生活充滿絕望的喬利,強(qiáng)暴了自己的女兒,并導(dǎo)致其懷孕。這樣的行為對(duì)彼克拉造成了身體和內(nèi)心的致命創(chuàng)傷,從此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最終導(dǎo)致她精神陷入瘋狂。
在創(chuàng)傷心理學(xué)領(lǐng)域,一些心理創(chuàng)傷看似并未危及到生命,但隨著口積月累的負(fù)而情緒,最終將導(dǎo)致情感、行為、軀體以及認(rèn)知等方面的慢性、部分或全面的心理障礙疾病。小說(shuō)中,主人公彼克拉生活在無(wú)愛(ài)、暴力的家庭中,造成了她膽小、懦弱自卑的性格特點(diǎn)。而而對(duì)父親的強(qiáng)暴行為,她的內(nèi)心倍感羞恥、無(wú)助和痛苦,行為上則開始逃避現(xiàn)實(shí)。
2.種族創(chuàng)傷
作者托尼·莫里森將小說(shuō)時(shí)空界定在1941年,俄亥俄州的洛雷恩市。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的歷史背景和社會(huì)狀況,美國(guó)南方的黑人仍然備受貧困、種族歧視和恐怖主義的困擾。小說(shuō)中,作者通過(guò)彼克拉的親身經(jīng)歷,建立了白人與黑人這一對(duì)鮮明的二元對(duì)立,即白人代表著美和優(yōu)越性,而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黑人則代表著丑陋與低下。以白人文化和價(jià)值觀為主導(dǎo)的社會(huì),黑人則必然被置于被壓制和歧視的“他者”地位。
小說(shuō)中,無(wú)論是白人、混血還是黑人,均不同程度地對(duì)彼克拉造成了心靈創(chuàng)傷。首先,在第一部分中,彼克拉來(lái)到了雅克鮑斯基的小店中購(gòu)買糖果,作為一名白人老板,他對(duì)待彼克拉的態(tài)度是極其輕蔑厭惡的。“在時(shí)空的某一固定點(diǎn)上他感覺(jué)沒(méi)有必要浪費(fèi)他的眼神。他并沒(méi)有看見(jiàn)她,因?yàn)閷?duì)他來(lái)說(shuō)并不存在什么看得見(jiàn)的東西。”“它帶有利刃;在下眼簾的某個(gè)部位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是厭惡之感,在所有白人的眼神里她都曾見(jiàn)到過(guò)。”從這些細(xì)節(jié),可以看出在雅克鮑斯基眼中,彼克拉是毫無(wú)價(jià)值和存在感的。他不屑于與她有任何眼神交流。而當(dāng)彼克拉遞給他錢時(shí),“他猶豫了一下,不愿碰她的手”。從中可見(jiàn)任何與黑人的肢體接觸都會(huì)讓他產(chǎn)生強(qiáng)大的厭惡情趣。這一細(xì)節(jié)的描繪,作者展現(xiàn)的絕非黑人不幸遭遇的個(gè)例,而是非裔美國(guó)人和真正美國(guó)人關(guān)系的真實(shí)寫照。備受壓抑、厭惡與歧視才是黑人生活的常態(tài)。
在20世紀(jì)70年代的美國(guó),以白人文化為主流文化的觀念同樣深入了混血與黑人的內(nèi)心。膚色往往象征著經(jīng)濟(jì)狀況和社會(huì)地位。小說(shuō)中,混血兒莫里恩·皮爾的到來(lái)使整個(gè)學(xué)校為之傾倒。“老師叫到她時(shí)總是滿臉微笑以示鼓勵(lì)。黑人男孩子在走廊里從不使壞將她絆倒;白人男孩子也不用石子扔她……”與她產(chǎn)生鮮明對(duì)比的則是彼克拉的遭遇,老師對(duì)她厭惡輕蔑,同學(xué)們經(jīng)常欺負(fù)捉弄她,還經(jīng)常對(duì)她進(jìn)行辱罵:“小黑鬼,小黑鬼,你爸爸睡覺(jué)光屁股。”由于膚色,彼克拉內(nèi)心遭受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造成的她畸形的審美觀念。當(dāng)她遭到侮辱和歧視時(shí),她內(nèi)心喪失了反抗的欲望和能力,將過(guò)錯(cuò)歸咎于自己的丑陋,因此長(zhǎng)期的羞恥情緒和對(duì)藍(lán)色眼睛的強(qiáng)烈渴望使她步入痛苦的深淵。
3.宗教創(chuàng)傷
由于殖民活動(dòng)以及黑奴交易的影響,非裔美國(guó)人的傳統(tǒng)宗教在不斷地改變與發(fā)展。從18世紀(jì)末,基督教在黑人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并逐漸被接受。小說(shuō)中,基督教絕不是簡(jiǎn)單的一種宗教信仰,而代表著白人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文化內(nèi)涵以及審美觀念。基督教不僅改變了黑人的生活態(tài)度,還對(duì)黑人的本土文化造成了巨大沖擊。
小說(shuō)中,主人公彼克拉直接或問(wèn)接地受到了宗教的毒害。首先,彼克拉的母親波莉?qū)⒆诮绦叛霎?dāng)成精神寄托,沉浸在宗教生活中,她將其視為生活中極其中要的部分,而其他的一切則是無(wú)意義而又虛無(wú)的。這種畸形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她母性身份的喪失,最終使彼克拉生活在冰冷的家庭氛圍中。另一方而,來(lái)自皂頭牧師的創(chuàng)傷則更加嚴(yán)重。作為一名牧師,他僅僅是一名披著宗教外衣的殺人犯,以上帝博愛(ài)之名,行傷害之實(shí)。他的欺騙行為直接導(dǎo)致彼克拉精神世界的崩潰。除了來(lái)自外界的宗教創(chuàng)傷,彼克拉內(nèi)心世界同樣被宗教所蒙蔽,她無(wú)數(shù)次祈求上帝給予她一雙藍(lán)色的眼睛,以此來(lái)擺脫困境,但實(shí)際上,上帝并不是救世主,彼克拉的愿望最終依然會(huì)幻滅。
4.結(jié)語(yǔ):
小說(shuō)《最藍(lán)的眼睛》,作者通過(guò)彼克拉悲慘命運(yùn)的描寫,展現(xiàn)的是非裔美國(guó)人共同的生存困境。正如小說(shuō)中的波莉、喬利以及皂頭牧師,表而上他們是施害者,但實(shí)際上他們也是受害者。和彼克拉一樣,在白人統(tǒng)治的社會(huì)下,受到家庭、宗教、種族的創(chuàng)傷,造成了自我、民族和文化意識(shí)的喪失。作者通過(guò)作品表達(dá)了對(duì)黑人命運(yùn)的同情,同時(shí)也在激勵(lì)同胞探索生存之路,找回真正屬于黑人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認(rèn)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