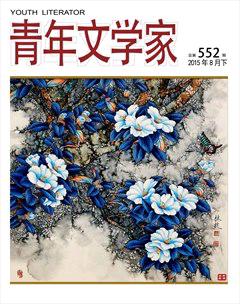論《黑暗的心》中的延宕性敘事
李貝貝
摘要:《黑暗的心》是波蘭裔英國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說講述了主人公馬洛沿著剛果河深入尋找庫爾茲的經歷。原本簡單的事件經過作者獨特敘事手法的處理,競變成一樁混亂不堪的大事,撲朔迷離又耐人尋味。因此本文著眼于小說中敘事結構的延宕性,圍繞其框架性敘事,懸念的設置,以及行動的拖延三個方面來具體加以論證。通過對其敘事形式的關注打開通往作品意義的大門,并分析其達到的藝術效果。
關鍵詞:黑暗的心:延宕性敘事;庫爾茲;框架性結構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4-060-02
約瑟夫·康拉德是波蘭裔英國小說家,曾被評為英國現代八大作家之一。處于二十世紀文學轉型期的康拉德是一個勇于革新的文學實驗者,他努力擺脫傳統敘事方式的束縛,采用一系列新的敘事程序來架構作品,大大突出了作品的文學性,讓讀者耳目一新。本文以其代表作《黑暗的心》為例,具體分析了延宕性敘事在作品中的表現,并進一步探討其敘事于法背后的意義與所達到的藝術效果。
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把延宕,即“阻撓和延緩”看成是藝術的一般規律。他認為:“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喚回人們對生活的感受……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變得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藝術是體驗事物的藝術構成的一種方式。”此即“陌生化”概念的提出,因此延宕的敘事作為作品陌生化的方式之一,無疑增加了讀者感知作品的難度和時問,使讀者同時沉浸于事件和敘事本身去思考,從而獲得更高的審美體驗。
在《黑暗的心》中,敘事的延宕性首先表現在框架性敘事即“套中套”的敘事結構上。從整體來看,作者設置了雙重敘事結構,第一層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向讀者講述在“賴利號”巡航帆艇上聽一個叫馬洛的人講述自己的遭遇;第二層是,敘述者馬洛向同船的人講述他的非洲之行,那么第一層的敘述者“我”在第二層中就轉換為敘述接受者。由此便造成了兩重分裂從而造成了敘事的延宕。首先,由于兩層敘事的設置,馬洛敘述的統一性和完整性由于既是傾聽者又是置身事外的第一層敘述者“我”的存在而被割裂,作者在馬洛的敘述中插入了“我”對馬洛的觀察和其他人對其故事的反應。這樣就使得馬洛所講的非洲之行的進展被打斷,延緩了故事的敘述,同時使讀者跳出故事情境,以旁觀者眼光審視故事本身。其次,雙重敘事所造成的不同敘述者視角之間的轉換,不僅使現實與馬洛所講遙遠非洲故事之間的斷裂被突顯,同時兩個敘述者之間觀點的不一致,對文本意義的解碼起到了延宕的作用。例如,在小說的開始部分,面對泰晤士河,船上的“我”發出感慨,“有什么偉大的東西不曾隨著這河水的退潮一直漂到某片未知的土地的神秘中去!……人類的夢想、共和政體的種子、帝國的胚胎”,并對過去時代的宏偉精神加以頌揚。然而當馬洛一開口就說到“這個至今也一直是地球上的黑暗的地域之一”。文章開頭兩者觀點的截然相反,便會引起讀者的注意和興趣,去探求事實的真相。于是沒有一個權威敘述者的表態,文章的主題只能是讀者自己去發現,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的主題也是被延宕的,只能隨著事情的發展而一步步被揭開。
其次,在《黑暗的心》中延宕于法還表現為懸念的設置。首先,作者并沒有直接把庫爾茲形象完全展現在讀者而前,而是將其設置成一個謎。在馬洛追尋謎底的過程中,我們不斷接收到關于他零散的信息片段,這個懸念的設置不僅構成故事向前發展的動機,更調動了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動力。在尋找的過程中,不同敘述者上場,提供了關于庫爾茲的不同信息。總會計師說他送回的象牙數量非常之多,是第一流的公司代理人,前程遠大;一位經理說他是“奇才”,是“憐憫、科學、進步的使者”,使得馬洛以為他是懷有“道德觀念”的人;庫爾茲的追隨者對其忠心耿耿,他還受到野人的瘋狂崇拜;最后庫爾茲出現,他足一個陷入了欲望、野心的深淵而墮落成為了貪婪、殘暴之人。整個事件缺少一個統治一切的權威“敘述者”,莫衷一是的評論塑造了庫爾茲的神秘性。那么庫爾茲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他值得這樣一次歷盡周折的冒險嗎?零散、混亂的信息一點點向讀者浮現,讀者在驚奇中不斷判斷、甄別、玩味這些細節,從而加深了印象;在思考中讀者還可能得到額外的認知收獲,局部細節的意義得到凸顯,作者為自己簡單的框架填充了豐滿的“肌質”,并一步步引導讀者參與到事件本身和呈現事件的機制當中,這也是康拉德文學觀的一種體現。同時,馬洛試圖重構故事的完整性,他作為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不僅告訴我們別人對庫爾茲的評價,庫爾茲自己的話還描述他所親眼看到的庫爾茲等,但是由于庫爾茲故事所包含的深刻矛盾、神秘性或者其罪惡本質,使得故事本身是抵抗被敘述的,因此在敘述者和被敘述的事件之問就形成了一種張力。
通常,在以往傳統小說中,如果文章的開頭提出一個問題,那么在結尾時相應會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然而在康拉德作品中卻并非如此。對于庫爾茲形象的描述,不同的敘述人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他究竟是什么樣,作者在最后也沒確定表述。他到底有沒有過固定的職業,他的最大才能是什么,他過去究竟是做什么的,他曾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還是給報紙寫文章的畫家,還是一位能繪畫的記者,還是根本不會寫文章,等等這些連他的表兄都無法提供準確的信息。隨著情節的進展和不同敘述人的上場,“我”對庫爾茲的認識一再被推翻重寫,這事實上不僅構成了敘事的延宕,還構成了一種敘事顛覆和被解構的過程,它造成了一種與傳統封閉式結構不同的開放式結構,同時也是作者自身懷疑主義思想的體現。
除此之外,懸念的設置還表現在小說的標題中。“黑暗的心”作為小說的標題,對于它意義的解讀為我們埋下一條隱性的主題之線,與庫爾茲之謎構成雙重謎而,拓展了作品的深度。我們隨著馬洛的足跡進入非洲這片充滿原始野性的土地,惡劣的環境,凄涼陰暗的大片叢林、霧靄,頻發的疾病,野蠻的原始人,受非洲奴役的黑人……這一切使非洲成為整個世界的黑暗中心;當我們目睹黑人們受到殖民者的殘暴統治和非人遭遇,他們只有干活和死的權利,空氣中充滿痛苦死亡的味道,這揭示了殖民主義者的黑暗內心;當馬洛找到庫爾茲,發現這個他以為曾經擁有非凡才能和道德觀念的人,已經墮落得充滿野心、欲望,貪婪而殘忍。所以“黑暗的心”也是人性的墮落與黑暗。豐富的審美意義空問隨著一明一暗兩條主線的展開而不斷深化、被解碼,隨著局部細節的填充而拓寬,隨著作者獨到匠心的設置而慢慢彰顯,讓讀者在撲朔迷離中回味無窮。
最后,延宕的敘事還表現在馬洛出發前行動的一再被拖延。先是沉船事件,馬洛的船在他到來前兩天被開出去,撞在礁石上沉沒了。之后維修過程因缺少鉚釘被耽擱,接著預定的鉚釘遲遲不到,等汽船終于修好,再加上路上花費時問,當他找到庫爾茲時,庫爾茲己與外界隔絕一年有余,同時病重的庫爾茲還阻止他們找到自己。這除了展現混亂的現實,表達渴望有所作為而不可得的尷尬處境之外;這種阻滯從審美效果方面來說,遲滯了高潮的到來,延長了讀者的感受時間,為讀者最后參透玄機、審美快感的到來做鋪墊。之后馬洛回想起來懷疑這是有人刻意安排,從而也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陰謀,人心的險惡。
因此,總體來看,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采取了一種延宕性的敘事策略,這不僅使得統一、完整的敘事被打斷,而且因為缺乏一個權威敘事者的存在,事件本身變得混亂不堪,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使作品“陌生化”的效果。俄國形式主義者尤里·梯尼亞諾夫認為在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中,將一件簡單的小事發展成意見混亂不堪的大事,“這里的關鍵在于事物的特殊語義學的結構,在于引導讀者去行動的特殊方法”。作者不再赤裸裸地將事件擺在讀者面前,而是通過敘事結構的架構,不同敘述者的設置,使事件本身的神秘性、內含的深刻矛盾性和本身的罪惡凸現出來。同時,讀者與作者創作的文本之間的互動關系被激活,讀者若要獲得真正的審美愉悅,應當充分調動自己的感官,積極參與到與作者、文本的互動中,才能更好地獲得審美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