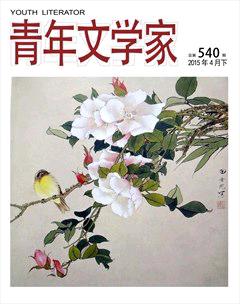論杜牧的揚州情結及其文化根源
舒小超
摘 ?要:創作主體的主觀思想,個人經歷等必然影響到作品本身的生命力的集合方向,而主體本身所處的社會存在這一客觀因素,也往往牽動著作品生命力的具體表現形式。本文試圖從主、客觀兩大方面,以杜牧關于揚州的詩歌作品為線索,深入剖析杜牧的揚州情結及其產生的文化根源,并力求揭示這種文化根源對創作主體的影響程度。
關鍵詞:杜牧;揚州情結;生命內核;主觀;文化外延;客觀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2-0-01
正如談到大上海就想到張愛玲,談到鳳凰城就想到沈從文一樣,談起揚州這座中國封建時期著名的風月之都時,不可避免地要想起晚唐詩才杜牧。可以充滿詩意地說,揚州是杜牧的揚州,杜牧則是揚州的杜牧。“東風歷歷紅樓下,誰識三生杜牧之”,杜牧與揚州,才子與紅樓,注定是一場命中注定的愛恨糾葛。杜牧的揚州情結,其生命內核所掩映下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映射交織,彰顯出了時代環境下個人意識與社會存在的碰撞融合的文化張力。
(一)
杜牧揚州情結的生命內核,主觀上來說,變現為審美主體的審美體驗的有序化,其中,既有對身處風月場所的酣暢淋漓的再現,也有對漂泊異鄉的凄涼寂寞的重塑,而貫穿其中的理想主線,這是寒門仕子仕宦報國的理想追求的破滅所彰顯出的巨大文化通透力。
杜牧出身名門望族,其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而他本人在弱冠之年便寫出了《阿房宮賦》這樣不朽的名篇。“春風得意”,“倜儻風流”,青年時代的詩人豪放灑脫,雄心萬丈。然而社會存在與個人意識的巨大反差,無情地破滅了他的仕宦理想,也鑄就了熠熠生輝的揚州情結。父親去世,家道中落,牛李黨爭,朝政混亂,才華橫溢的詩人心灰意冷,杜牧應淮南節度使牛僧孺之邀于公元833年4月首次來到揚州。彼時的揚州作為聞名全國的風月之都,多多少少為受傷的詩人帶來精神上及肉體上的慰藉。“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多情的詩人不惜為萍水相逢的歌女揮毫潑墨。這不僅僅是詩人風流意識的雜亂堆積,更多的是對積極入世的仕宦意識的巨大彰顯,以及價值取向落空之后的心理反差。無怪乎詩人流連青樓,或許,在詩人敏感的心靈深處,煙花女子比廟堂君子來得更為直白而情切,這何嘗不是個性自由與仕宦報國不可并存的失落之意的情感聚集。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在《寄揚州韓綽判官》一詩中,我們看到,離開揚州后的詩人對繁華歲月的無限留念,亦或說是對宦游別處的巨大排斥。揚州,曾是杜牧的溫柔之鄉,也是他的傷心之地,這個風月場所裹挾著詩人滿腔的愛與失落,以至于已是不惑之年的詩人還在追憶那段風花雪月的生活“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正是詩人這位審美主體內在的個性自由與浮世約束,精神追求與理想破滅,放浪形骸與仕宦入世的巨大反差,從主觀上來說,支撐起了杜牧揚州情結的生命內核的金字塔,這座金字塔頂端所熠熠生輝的折射的是文人在禮樂崩壞的浮世沉淪、掙扎的迷茫與矛盾。
(二)
杜牧揚州情結的文化外延,從客觀上來說,則是在特定生產力水平之下的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與精神追求,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杜牧的揚州情結則是無數多人的揚州情結之下的集中反映。
晚唐江南一帶城市商業經濟較以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再者,較之中原地區戰亂較少,因而江南地區城市取得了空前發展,形成了坊市合一的新興城市格局,商業活動甚是繁榮。揚州,這座作為與西京長安與東都洛陽齊名的全國大型城市,在南國歌舞升平,吳儂軟語的浸染中,雅俗共賞的紅樓館舍大量設立。大量失意政客,寒士浪子,流連煙花之所,南朝風月,朝歌夜弦,讓他們忘記了現世生活的失意。而杜牧,這位在現世生活中被官僚士大夫所擯棄的“丑石”,在男人特別是文人與生俱來的風流的促引之下,像許許多多的寒門仕子一樣,投身風月,流連忘返。從這個角度來說,揚州,不僅僅是杜牧的揚州,更是所有文人才子的揚州。
社會的主流意識與價值在于文人士大夫與政治進行或多或少的靠攏,誠意正心,成為文人們的品格內核,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則構成他們個人價值的全部。當這種價值追求無情破滅時,他們對畢生堅守的儒家封建禮教產生了某種動搖,歸隱,狎妓,甚至充當專制與暴力之下的無恥文人的角色。天生的特殊性格與儒家士大夫階層思想難以調和的矛盾,加之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詩人浪漫、風流不羈的性格,使得鏡頭音律的在都市生活,勾樓瓦舍、娼館酒肆成為他情感自由宣泄、靈魂超脫于物的感情傾訴之所。從這個角度來說,杜牧的揚州情結與陶淵明的歸隱情結,林逋的梅妻鶴子情結,本質上來說是一樣的。只是客體的不同,造成了杜牧的揚州情結的文化價值的有序化與獨特性。
杜牧的揚州情結,其文化根源的表現形式正是在于其主體與客體的生命內核與文化外延的完美交織。揚州,沉淀著這位多情風流的失意文人的愛恨情仇,折射著時代背景中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這座令人流連忘返的南國城市,在那清冷如斯的二十四橋明月之下,永遠滌蕩著才子佳人的文采風流。
參考文獻:
[1]曹中孚,晚唐詩人杜牧[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
[2]馮集梧,樊川詩集注[H].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