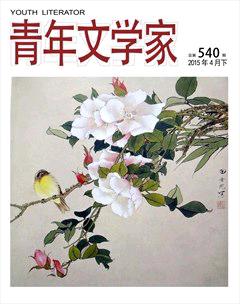基于主旋律的歷史變奏
摘 ?要:電影《天將雄獅》雖然標(biāo)榜改編自真實的歷史事件,但呈現(xiàn)出來的卻是對歷史神話式的敘述。在這種敘述中,民族的概念被多民族共同體所置換,描繪出對和平的、烏托邦式的絲路的愿景。通過對歷史的改編,片方在電影中呈現(xiàn)出來的多民族和平相處的圖景正與國家的整體戰(zhàn)略布局同步,呼應(yīng)了主旋律的詢喚。
關(guān)鍵詞:歷史敘述;民族共同體;主旋律
作者簡介:胡豐(1978-),男,漢族,山東濟寧人,2004年畢業(yè)于煙臺師范學(xué)院,現(xiàn)為山東省微山縣第三中學(xué)教師。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2-0-01
電影《天將雄師》自上映以來可謂是褒貶參半,其中關(guān)注較多的一點即是這部電影所講述的故事——當(dāng)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兩個帝國之間僅有的軍事接觸——是否如片方所說果有其事。其實,既然是改編,就意味著編劇和導(dǎo)演具有二次創(chuàng)造的權(quán)力。與其執(zhí)迷于對歷史本事的考據(jù),不如潛心思考在這全新的想象空間中,電影歷史的方式傳達了怎樣的現(xiàn)實訴求。
一、走向神話的歷史敘述
柯文在《歷史三調(diào)》中區(qū)分了作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歷史,認(rèn)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是人們了解歷史的意義、探尋并最終認(rèn)識歷史真相的不同途徑,反映出來的是完全不同的音調(diào)或‘調(diào)子”。①講述歷史方式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歷史面貌。具體到影片《天將雄師》上來,影片所立足的歷史事件——羅馬軍團戰(zhàn)俘歸漢,以及影片呈現(xiàn)的霍安維護絲路和平的傳奇經(jīng)歷即是這一段歷史本事中的事件和神話的兩個維度。
公元前53年,克拉蘇統(tǒng)帥羅馬軍團進攻中亞強國安息,不料卻陷入重圍,兵敗卡爾萊。克拉蘇戰(zhàn)死,只有其長子率領(lǐng)第一軍團六千余將士向東突圍,最終不知所蹤,成為歷史上的一個謎團。八十年代末期,中澳蘇三國學(xué)者展開聯(lián)合考證,從班固所著《漢書·陳湯傳》的記載中,得出羅馬軍團曾與漢朝軍隊有過軍事接觸,并被俘虜,驪靬就是西漢朝廷為安置這批羅馬戰(zhàn)俘而建立的結(jié)論。②
影片《天將雄師》即在此假說的基礎(chǔ)上鋪展開來,講述了一段發(fā)生在西域的傳奇故事。影片中,羅馬將軍盧魁斯護衛(wèi)小王子奔逃到雁門關(guān),意圖攻下城池以作落腳之處,不料卻遭到了西域都護霍安的抵抗。二人交戰(zhàn)之際忽逢沙暴來襲,共同的災(zāi)難不僅中止了爭斗,還使二人建立起了真摯的友誼,連同在筑城過程中化敵為友的三十六國民眾也親如一家。然而,理想的和平之城卻遭到了野心家緹比斯的威脅,小王子和盧魁斯相繼遇害。最終,緹比斯所代表的強權(quán)的威脅和金錢的誘惑不僅沒有擊垮三十六國,反而使得他們在霍安的精神感召下團結(jié)起來,與緹比斯殊死抗?fàn)帲匦l(wèi)了絲路的和平。可見,且不論假說是否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即使假說成立,《天將雄師》的改編也走出了歷史的限度,走向神話式的敘述。影片所體現(xiàn)的多民族和睦相處的和平理念實質(zhì)是在現(xiàn)實主題的基礎(chǔ)上對歷史本事的神話式改寫。
意大利歷史學(xué)家克羅齊認(rèn)為“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不論講述者對歷史做出怎樣的闡釋,歸根結(jié)底都很難擺脫現(xiàn)實的處境,在自覺不自覺中帶有對現(xiàn)實的訴求。《天將雄師》雖然號稱是根據(jù)真實事件改編,卻無意去再現(xiàn)真實的歷史事件,而是基于現(xiàn)實的主題去發(fā)掘這一歷史事件的意義。盡管這是一段脫胎于漢朝和羅馬戰(zhàn)爭的故事,電影傳達出的卻是多民族和諧相處、大國間互信共存的現(xiàn)實主題。
二、想象的多民族的共同體
雁門關(guān)筑城是在影片敘述中是一個核心部分,它不僅勾連起前半部分的霍安被陷害、盧魁斯東進和高潮部分的抵抗緹比斯,也借霍安的行為宣揚了編劇對于民族關(guān)系和和平問題的理想。太守府命雁門關(guān)守將十五日之內(nèi)完成原本半年的工期,這本意是刁難雁門關(guān)筑城人員,意圖降罪于霍安。然而,羅馬軍團發(fā)揮西方在建筑上的特長,幫助他們完成了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在筑城的過程中,各族人民用理解取代了隔閡,和平取代了戰(zhàn)爭。再加上昂揚樂觀的背景音樂以及恢弘壯麗的暖色調(diào)布景,這都為影片涂上了理想化的色彩,使雁門關(guān)成為烏托邦之城。
筑城的過程是各個民族之間加深了解的過程,也隱喻了由絲路各國由地方民族主義走向大民族主義的過程。代表各個民族的旗幟在雁門關(guān)共同升起的場面就象征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被各民族共存的大民族主義取代的標(biāo)志。美國學(xué)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將民族定義為“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zhì)上有限的(limitied),同時也享有主權(quán)的共同體。”③霍安所宣揚的理念,其實是以西域這一多民族雜處的特殊地域為例,重新定義了民族的概念。他將民族的邊界擴大化,以此建構(gòu)了一個想象的、高于政治主體之上的多民族共同體。而使這個共同體穩(wěn)定化,并能夠像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一樣應(yīng)對危機的關(guān)鍵,正是作為共同的生存空間的絲路以及人類對和平的渴望。霍安在片中一以貫之的形象即是作為這個共同體的秩序的守護者和理念的踐行者。
總體說來,在“一帶一路” 作為國家的戰(zhàn)略性決策,并受到全球數(shù)十個國家熱烈響應(yīng)的今天,“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所包含的互信、和平的理想正與當(dāng)下我們所倡導(dǎo)的新型國際關(guān)系的理念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影片通過霍安傳達的聲音正是商業(yè)化的市場話語對國家主流話語詢喚的呼應(yīng)。與其說影片是在講述歷史故事,不如說它是在面向現(xiàn)實發(fā)聲。“一帶一路”是在平等的文化認(rèn)同框架下談合作,體現(xiàn)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而《天將雄師》的核心,正是借助于歷史展現(xiàn)在這種理念主導(dǎo)下出現(xiàn)的烏托邦世界——一個沒有戰(zhàn)爭,互信合作的理想化絲路。揭開電影的歷史面紗,我們發(fā)現(xiàn)的是主旋律的另一幅面孔。
參考文獻:
[1][美]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diào):作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的義和團[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2]郗永年、孫雷鈞.永昌有座西漢安置羅馬戰(zhàn)俘城[J],人民日報,1989年12月5日第三版.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M],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