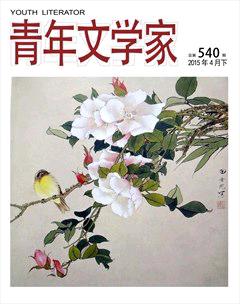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胡王駿雄
摘 ?要: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個專門研究文藝工作的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的《講話》也成為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和我國革命文藝發展的根本指導,這次會議也成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必然,不但為當時解放區文藝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促成了大批作家創作轉型和文學新形式的產生,同時它也可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階段劃分的重要節點。
關鍵詞: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現代中國文學;創作轉型;文學史分期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2--03
今天,在我們探討現代中國文學并且試圖把握其發展脈絡的時候,往往容易忽視一些重要會議的作用和影響,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一次文代會以及第四次文代會,甚至可以說前不久習近平同志在北京召開的文藝座談會都是現代中國文學發展階段的重要歷史節點。時至今日,學界對延安時代文學及文藝的研究仍然較為薄弱,究其原因,不少治學者認為,正是因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延安文學與政治聯系過于密切,難以成為一個有“文學價值”的研究對象。然而需要我們關切的并非是研究對象樣態距離自己的文藝理念有多遠,而是作為歷史其價值如何,又是如何影響歷史的。我們學界認為“五四文學”“新時期文學”乃至“十七年文學”是現代中國文學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那么也就沒有理由不重視延安文學。延安文學就像一個轉接點或是中轉站,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與下半葉中國文學進行銜接與整合的重要階段,是現代中國文學的重要轉型期,沒有延安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就會出現一個無法解釋和彌補的斷層和空缺。而作為催生延安文學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其歷史作用與文學史地位由此也就可見一斑。
一、座談會“談”了什么
延安文藝座談會于1942年5月在延安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樓召開,期間分別在5月2日、16日及23日進行討論會,與會人員都是邊區或延安文藝工作者和魯迅藝術文學院師生。那么,座談會又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在怎樣的語境中召開的呢?這是因為這一時期延安文藝界乃至整個解放區文藝界都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系問題……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 1盡管這些問題當時并未構成文藝界的主流,但是卻是不利于抗戰和革命事業,同時也阻礙了文藝自身的發展。在決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毛澤東就曾邀請多位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就當時解放區文藝界出現的諸多問題進行過意見交流。“為什么要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找我去,說了兩句話,非常之重要,從這個話才能理解延安文藝座談會。他說邊區的經濟問題我們解決了,現在我們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文藝界的問題。”2著名作家劉白羽這樣回憶他與毛主席的交談。而作為抗戰前夕第一個從大城市到達陜北蘇區的名作家,丁玲受到毛主席極高的贊賞,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毛澤東同志也多次與她交換了文藝批評等問題的意見:“召開這次會議,也可以說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節有感》而引發的吧,但絕不是僅僅為了某一篇或某幾篇文章。座談會以及毛主席的講話很明顯都是為了正確解決在新形勢下革命文藝工作和文藝思潮中出現的基本問題和傾向”。3
1942年5月2日下午,眾人期待的座談會召開了第一次討論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開宗明義,娓娓道來,他指出,當時解放區文藝界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和學習問題。在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引言部分后,與會的文藝界工作者進行了認真的學習和激烈的討論。5月16日召開座談會的第二次會議,毛主席整天時間都在認真聽取與會人員的發言,并不時做著筆記。23日進行了第三次討論,當日晚飯后,毛主席就三次會議以來大家的討論進行了總結講話,“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4,也即后來的《講話》中最重要和精髓的部分——《結論》。那么,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這次座談會以及它的會議文件——《講話》談了什么,又是如何指導解決這些問題的呢?
一、文藝服務對象的問題:自古以來文藝必將屬于一個階級,因為文藝創作者本身就屬于一定的階級,有一定的政治立場。中共需要的新中國新文化,應該是與無產階級大眾站在一起的文藝創作,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文藝就應該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講話》指出明確其中“人民大眾”的概念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工人。第二是農民,第三是作為革命戰爭主力的武裝起來的工農軍,第四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5文章還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原則性的問題。”6脫離這個原則,脫離這個根本去搞創作,就脫離了最深廣的現實社會基礎,文學藝術和意識形態是我們的精神食糧,在每個時代都是為人們所需要的,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以最廣大的現實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和文學藝術。文藝工作者只有熱愛群眾,深入群眾,學習群眾,才能挖掘出人民群眾的真情實感和精神需求,才能創作大眾化的文藝,從而豐富人民的生活以致寓教于樂,團結群眾并爭取戰斗最后的勝利。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一個根本問題。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在抗戰時期為統一思想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建國后這一思想仍被繼續作為文藝建設的標尺。
二、文藝如何服務的問題: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接下來就得解決如何去服務的問題。簡單來說,主要是怎么處理文藝作品普及和提高的問題。文藝既然是為工農兵,那么,它的普及和提高也一定是要圍繞工農兵來進行。毛澤東在座談會上指出:“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而要達到這個要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7任何成熟的文藝創作者,都應該到群眾中去,去真切地體驗生活、認真地感受生活,才有可能進入最佳的創作狀態。因此,直到今天這仍是指導文藝創作不變的真理,新時代的新文學,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從群眾中吸取養料,否則其作品必成空中樓閣,不切實際。
三、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文藝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和階級性,這是其不爭的社會性質,否定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政治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位置,這顯然不是正確的。政治因素的參與不會危害文藝的審美性,它們是辯證統一的。《講話》從審美價值、功利標準以及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等方面論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對于文藝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同志表示有三個問題需要認真對待,其一是以抗日為根本目的;其二在民心上需要團結起來;其三則是在文藝方法和藝術作風問題上團結起來,主張現實主義。離開這三個問題的其中一個,都將削弱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力量,不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大眾進行革命抗爭。
四、文藝批評標準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文藝批評依然應該是文藝界最主要的斗爭方法,但文藝批評需要從兩方面入手,即藝術標準和政治標準并存。“政治標準來說,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團結的,一切利于群眾同心同德的促成進步的東西都是好東西,反之則為壞,這里說的好壞不但要看動機(主觀愿望),還要看效果(社會實踐)。”8我們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者,應該以辯證的手法對文藝作品進行評判;而以文藝的標準批判時,將允許也必須允許文學藝術以各種形式和方式自由發展,應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予正確評判,不斷發展和提高文藝水平,從而豐富工農大眾的精神需求。
此外在《結論》中,毛澤東還談到了黨內思想整頓的問題,并且集中批評了解放區文藝界當時存在的幾種錯誤認識,從而為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向掃清了思想障礙。
二、 也談座談會以后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及1943年《講話》發表后,解放區文藝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習文藝座談會和《講話》精神的風潮。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指引下,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走進現實社會生活,文學作品在主題題材、人物形象及語言藝術等諸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現代中國文學也真正突破了知識分子的框架,融入工農兵,也是從此時起,新文學才得以真正意義上深入農村,把新文學革命的成果普及到社會最底層。從這層意義上看,這是“五四”新思想啟蒙的一個拓展,也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學弱點的克服,此后,新文學對作為中國現代社會生活中尖銳問題的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才予以較為全面地反映和充分的觀照。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后延安解放區的文學面貌的歷史性變化來看,其在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重大的。
一、延安文學體制的建立:延安文學是指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區根據地在上世紀30-40年代所衍生出現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理清了當時解放區文藝界思想的混亂,為文學藝術創作指明了在特定歷史時期內正確的方向,同時也促成了延安文學體制的建立與規范。延安文學體制“通過對作家的創作和發表進行規范、監督和評判,使作家成為了遵照文學體制要求進行創作的主體。”9正因如此,延安文學體制也就有著它不可避免的局限:它要求文藝工作者站在工農兵的立場贊頌工農兵,堅持文藝民族化、大眾化,堅持工農兵創作方向。作家們的這時期創作大都開始轉型,深入工農兵中間去,與工農兵交朋友,進而抒寫他們真實的生活。而這種生命經驗與作家們的思想文化背景構成以及文藝的本質屬性就必然會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在強調文藝為革命和政治服務的同時,由于有時作家們對于政治的理解過于狹隘、機械,對文藝基本特征認識不夠充分,不敢大膽揭露社會真實的矛盾,導致現實性不足,這時期的部分作品甚至還有粉飾生活的情況,文學多樣化和作家個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束縛和綁架。
二、解放區作家創作的集體轉型:座談會后,在活躍在解放區的作家群體可以歸類為三種,但他們的創作面貌都或多或少地發生了一些變化。
30年代的青年作家,他們在20、 30年代就已經在文壇上初露頭角,是第一種類型作家群。座談會召開及《講話》發表后,他們都深入工農兵的真實生活,有些在創作上實現了新的突破。而這類作家的創作又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擁護、積極參與文學體制的建立,創作積極適應新的文學體制,作品變化較大,例如何其芳、艾青等,雖然創作轉型后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取得了相當好的創作成果,但是其作品總體的藝術價值還是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二種是擁護、積極參與文學體制的建立,創作只是作了局部的調整,例如丁玲,“五四”時期以《莎菲女士日記》轟動文壇,隨后又有多部作品問世,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她積極投身河北地區土改,創作了長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作品滿腔熱忱地描述了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生活、新精神。此時丁玲的創作達到了新的高度,標志其現實主義創作走向了成熟。此外周立波、劉白羽等的文學創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三種是與新文學體制保持距離,創作基本沒有變化,如王實味等人,經歷周折,難有成就。
第二種類型作家群體是農村中的知識青年,他們大都出身農民階級,只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及《講話》精神的引導下,他們開始熱愛文藝,并逐漸成長為優秀的人民藝術家,例如,趙樹理,就是土生土長的農民文學工作者,長期致力于農村通俗化、大眾化的文學創作,并且積極宣傳,他的創作,總是蘊含著十分熱忱、迫切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常常以一個現實革命的觀察者和參與者的身份關注實際的革命斗爭中出現的種種社會現象和矛盾,并且努力挖掘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廣大中國普通農民身上所蘊藏著的英雄品格以及以人性最樸實的真善美。所以,他的作品總是具有某種泥土般樸實、凝重的特征和熱情、明朗的風格。
工農兵作家是第三種類型作家群,他們是從社會最底層的工農大眾之中直接成長起來的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是第一批工農作家,如,馬峰、西戎等人,都出身農村,年紀輕輕就參加了八路軍,后又到延安魯藝文藝干部訓練班學習、到報社學文化,當編輯,邊學習邊寫作,創作了《呂梁英雄傳》等優秀作品。
三、新文學形式的生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延安文藝工作者為了貼近廣大群眾的需要,大量采用民間文藝形式,解放區的創作在充分吸收和改造民間傳統藝術形式的基礎上,形成了許多新的文體:新評書體小說——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趙樹理的文學創作;新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和《新兒女英雄傳》影響巨大;民歌體敘事詩——這種新歌謠是在民間傳統歌謠形式的基礎上,加上抗日救國和革命的內容,歌頌革命、革命政黨、領袖和軍隊,就成為新歌謠的基本主題;新歌劇——以《白毛女》為代表的新歌劇的改革,帶來了敵后根據地的一系列文藝的變化,首次促進了話劇的民族化,也促進了秦腔、京劇等傳統戲劇的改變。與此同時,新文學藝術的創作中也真正出現了人民群眾的身影。在座談會召開后的解放區,群眾性戲劇創作和詩歌創作可謂高潮迭起,一大批民間藝術家涌現了出來。民間藝術家和群眾性文學藝術與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得如此深遠,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三、現代中國文學史分期節點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從總體創作方向上來看,完全可以把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作為中國新文學分期的節點。而談及將文學會議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史歷史分期的界標就不能不提及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從某種意義來說,“這部文學史著作奠定了將文學會議作為文學發展的歷史轉折的理論基礎,其文學史觀念、核心觀點和方法論都對文學會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影響深遠。”10王瑤將中國新文學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是1919年到1927年,相當于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所分的第一第二兩時期”;“第二時期是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相當于《新民主主義論》里的第三時期”;“第三時期是1937年到1942年的五年,即從抗戰開始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抗戰期間前五年的文學”;“第四時期是1942年到1949年的七年,即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到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的時期。”11以王瑤確立的這種將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一個獨立階段的分期標志的分期方式和分期標準,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一直是編撰現代文學史的一種基本構架和準則,即使個別版本的文學史著作或教材的編寫略有變動,但總體上是萬變不離其宗。
而文學會議作為文學史分期界標的歷史功能開始被逐漸淡化,則是進入上世紀文80年代中后期了,文學的審美性原則以及文學形式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視。尤其自1987年《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提出將現代中國文學分為三個十年以來,這種現代文學分期為學界更多學者認同,楊義在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采取的就是三個“十年”的結構與體例,在討論“第三個十年”的小說發展的階段性時,他強調“文學史的分期是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政治史的分期的”。12 過度強調作為文學史發展進程中界標的文學會議的意義,不可否認的存在政治標準優先的傾向的潛在風險,從而導致我們忽略文學發展進程中那些被政治標準和意識形態束縛甚至是掩蓋了的文學本質的追求,以機械單一的標準來審視文學發展,漠視其豐富性和復雜性。另一方面,倘若刻意淡化重要的文學會議對文學史發展進程的歷史影響,甚至完全忽略政治對文學的引導作用,選擇無視重要的文學會議以及文學中的政治元素,從某種意義來說又是一種逃避,是對文學本身的歷史狀態的選擇性粉飾和改寫。正因此我們更應該正視、直面文學發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秉持著批判性的思維來考察處于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而全面地理清兩者的關系,客觀地看待與評價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分期節點的這次文藝座談會。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隨著作家們的創作的轉型,為新文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物題材、抒寫主題和新穎獨特的藝術形式,新中國文學的雛形在此時期也得以孕育,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新文學在反映社會真實生活上的局限,開拓了文學發展的新局面。縱觀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在我國現代思想史和文藝史上,延安文藝座談會不可謂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座談會的召開,引發了了繼“五四”后又一場意義深刻的新文學革命,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道路和豐富的可能。
注釋:
[1]胡喬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回想延安·1942》,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第317-318頁.
[2]劉白羽.《決定我一生的是深入火熱的斗爭》.《回想延安·1942》,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第62頁.
[3]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回想延安·1942》,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第358頁.
[4]杜忠明.《延安文藝座談會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41頁.
[5]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75.第13頁.
[6]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75.第15頁.
[7]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75.第15頁.
[8]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75.第30頁.
[9]陳建華.《延安文學體制與作家的創作轉向》,西南師范大學,2004
[10]黃發有.《文學會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分期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8).
[1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新文藝出版社,1954.第16-19頁.
[12]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