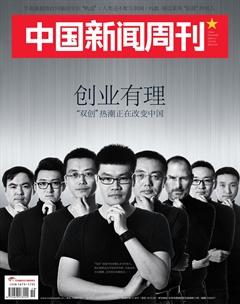卡斯特羅兄弟“擁抱”教皇
左曉園
5月10日上午,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拜訪羅馬天主教教皇方濟各。這次私人會談在保祿六世大廳的書房舉行,歷時50多分鐘,透露出來的信息顯示氣氛親切。這是83歲的勞爾和78歲的教皇首次會面。勞爾感謝教皇為改善古美關系所做出的貢獻,并表達了古巴人民期盼教皇到訪的心愿。
勞爾在當天舉行的記者會上說:“教宗的智慧和謙遜使我深受感動。我閱讀他的每篇講話。若教宗如此繼續下去,我這個共產黨員也將會回歸天主教會,重新開始祈禱。” 為明確態度,他甚至補充說,“這并非戲言。”
勞爾和方濟各的會見,一時間成立各國媒體的關注熱點,有報道直接以“勞爾·卡斯特羅將重新皈依天主教”為題,而卡斯特羅兄弟的宗教觀也引發了外界的興趣。
“基督教和古巴革命目標相互兼容”
執政將近50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各種場合多次闡述過自己的宗教觀。他一再表明,基督教和古巴革命目標相互兼容。
由于母親的影響以及在教會寄宿學校受教育多年的經歷,菲德爾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義有深刻的理解。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基督教教義中找到了契合點。他認為,基督教義的精神實質與社會主義之間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都是為了人類的福祉而奮斗;耶穌基督是個偉大的革命者,為反對不公正和壓迫而獻身;《圣經》中對教徒規定的戒律同共產黨對革命者的要求非常相似:教會提倡犧牲自我、節儉、謙遜和友愛的精神,以及反對腐敗、偷竊、淫亂和作偽證等邪惡行為,正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品質要求。
菲德爾表示,如果不是從宗教角度而是從社會視角來說,“我是一個基督徒。”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卡斯特羅兄弟出生在古巴原奧連特省中北部一個叫比蘭的偏僻莊園。父親來自西班牙加利西亞,白手起家,憑借勤勞和精明的投資逐漸積累了財富;母親是古巴人,出身于一個貧窮的天主教耶穌會農民家庭,是非常虔誠的教徒。
菲德爾和勞爾幼時都在教堂接受了洗禮,從小在天主教會學校學習。菲德爾回憶起他在拉薩列小學的日子,“學校一年級就系統講授教義問答手冊和宗教知識,《圣經》中記載的歷史基礎” “宗教教育、教義問答、做彌撒和其他宗教活動,在日常中很平常,就像上課與課程表一樣”“第一階段,我學《圣經》中記載的歷史就像學習古巴歷史一樣”。后來,菲德爾先后在更嚴厲、宗教使命感更強的多羅雷斯耶穌會學校和古巴最好的耶穌會中學——哈瓦那的貝倫中學求學。他曾經多次提到在耶穌會學校寄宿的經歷:每天必須做彌撒,學校更像個修道院。
然而,教會學校多年的宗教浸潤似乎并沒有使青年時代的菲德爾樹立宗教信仰。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古巴雄獅卡斯特羅的青少年時代》一書中,記載了菲德爾1985年在與巴西天主教多明我會(又譯為“道明會”)的神父弗雷·貝托的一段訪談。菲德爾在訪談中表示,“不可能通過呆板的、教條的和不合理的方式來對我灌輸某種信仰,企圖通過這種方式向我灌輸那種信仰是做不到的。我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念,在學校他們無法對我灌輸那種價值觀。”
但即便如此,家庭的影響和宗教的浸潤還是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烙印。他能夠尊重宗教作為古巴社會現實的客觀存在,這也成為古巴革命政權和羅馬天主教教庭能夠最終擯棄舊怨、實現和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菲德爾回憶說,“在漫長的斗爭年代,非常危險,我母親和外婆為祈禱我們的生命安全而許下了很多愿,我們之所以能在經歷了漫長的斗爭后活下來,無疑是由于她們有著雙倍信仰????雖然我的世界觀和她們不一樣,但我從沒有和她們爭論過這些問題,因為我看到了她們的宗教感情和她們的信仰帶給她們堅強、勇氣和安慰。”
與梵蒂岡關系一波三折
天主教是傳入古巴時間最早、勢力最強的宗教。古巴與梵蒂岡的外交關系建立于1935年。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后,雖然雙方關系出現波折,但一直保持著外交關系。最初,由于深諳宗教在民眾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遵循尊重宗教信仰的原則,對各宗教都持友好態度。然而此時古巴天主教會發布了一份題為《面對槍殺》的通報,反對革命政權。隨著古巴革命政府頒布包括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等在內的一系列法律,天主教會同革命政權的沖突日益公開化。

5月10日,梵蒂岡,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與羅馬天主教教皇方濟各進行私人會談。攝影/Gregorio Borgia 圖片編輯/何晞宇
1959年11月,古巴天主教大會在哈瓦那召開,抗議革命的激進化。1960年,一些天主教頭面人物發表文章或者發布致教友公開信,組織示威游行,反對政府的政策。1960年年底,天主教會向教友散發了由全體主教簽名的秘密信,譴責“卡斯特羅實行共產主義”,從而使整個教會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1961年9月,教會組織的一次宗教儀式發展成為一起反政府示威游行。此后,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擊措施,對教會學校和私立學校實行國有化,驅逐約130多名從事反革命活動的天主教教士,此后大批教士和修女移居海外。古巴政府的舉動引發了羅馬教廷的嚴重不滿。1962年梵蒂岡撤回駐古巴大使,降低了對古巴的外交規格。不過古巴政府并沒有采取對等行動,古巴大使仍然留在梵蒂岡,這種不對等狀況持續了13年。
梵蒂岡撤回大使后,將原來的使館一秘薩奇提升為臨時代辦。以薩奇為首的古巴天主教會對與政府的關系進行了反思,開始重新定位教會在新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紀60年代末,拉美一些進步的天主教神學人士推動了“解放神學”運動。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古巴天主教會于1969年4月發表一份牧函,表示擁護政府并強烈譴責美國加強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同年9月,教會在另一封牧函中要求教徒“必須懷著尊重和基督之愛區接近無神論者”。
古巴天主教會態度的積極變化得到了政府的及時響應。政府放松了對宗教活動的限制,允許在一份官方出版物上刊登禮拜日的宗教活動情況,并對需要維修的教堂提供幫助。此后多年里,菲德爾利用各種與拉丁美洲宗教界人士見面的機會,闡述自己對宗教問題的看法。他多次重申,僅僅相互尊重是不夠的,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國家和教會之間應當建立“戰略性聯盟”。特別是1985年他與著名的巴西天主教多明我會神父弗雷·貝托進行了長達23個小時的談話,全面、深入闡述了自己的宗教觀。談話經貝托整理后出版,在整個拉美宗教界引起強烈反響。
脫去戎裝迎教皇
前蘇聯解體后,美國加緊經濟封鎖,古巴陷入嚴重危機。為了應對危機,1991年10月召開的古共“四大”修改了黨章,允許教徒加入共產黨。菲德爾開始把古巴稱作一個“世俗”的國家,而不再是“無神論”國家。
古巴與羅馬教庭的關系在上世紀90年代也有了進一步發展。1996年,時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應邀訪問梵蒂岡,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會晤。1998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應邀訪問古巴。此前他曾14次訪問拉美,足跡遍及拉美各國,卻從未訪問過古巴。菲德爾脫去一貫的戎裝,身著深藍色西裝和其他古巴領導人到機場迎送。從機場到下榻賓館長達25公里的道路兩旁,擠滿了揮舞著梵蒂岡和古巴國旗的歡迎群眾。教皇在四個城市做了露天彌撒,電視臺向全世界現場直播。最后一次彌撒在哈瓦那的革命廣場舉行,廣場上人山人海,四周建筑物上原有的革命口號換成了歡迎教皇訪古的口號,懸掛著耶穌的巨幅肖像。在訪問中,菲德爾數次與教皇肩并肩出現,并參加了最后一次彌撒。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訪問中批評了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從國外強加的限制性經濟措施是不公正的,在道義上是不能接受的”,“愿古巴盡其最大的可能向世界開放,愿世界向古巴開放”;同時也要求古巴實現更大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并向古巴政府遞交了一份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名單。
教皇訪古前后,古巴政府進一步放松了對宗教的限制,大大改善了政府和教會的關系。1997年古巴政府恢復了自1969年取消的圣誕節,并于1998年起將其定為法定節日。古巴政府還先后釋放了300多名犯人。
約翰·保羅二世的訪問成為古巴向外界展示自我的絕好機會,產生了積極的連鎖反應。當月月底,危地馬拉宣布與古巴復交;兩個多月后,多米尼加也與古巴復交;3月美國宣布放松封鎖的四項措施,包括允許向古巴出售食品和藥品;4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七年來首次否決了美國提出的反古提案,同月加拿大總理訪問古巴,成為20多年來訪古的首位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首腦;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反對美國對古巴實行經濟制裁的提案,贊成票之多前所未有;11月拉美一體化協會決定吸收古巴為正式會員。
時隔十四年后,2012年3月,另一位教皇——本篤十六世對這個加勒比島國進行了訪問。這次迎候在機場的是勞爾·卡斯特羅。四年前他從兄長菲德爾的手中接過權力,在推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進一步改善和天主教會的關系,就釋放政治犯和異見人士問題上與教會進行對話。教皇造訪期間數次提到為雙方關系的改善感到高興,但同時敦促古巴建立更開放的社會。此次訪問后不久,古巴宣布將圣周五定為法定節日。
2015年9月方濟各將成為第三位造訪古巴的教皇。在訪問完古巴后,他將對美國進行訪問。他的美國之行將包括與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見面。分析認為,教皇的訪問將會促進古美關系早日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