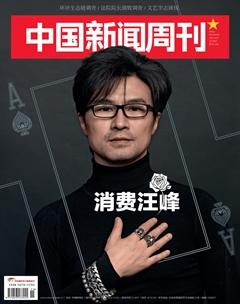“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對接與連通
何亞非
“文明對話”是對接的基礎
“一帶一路”沿線幾十個國家,人口44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各種文明的混合帶來的區域文明,使這個地區的文明多樣性異常豐富,多個文明圈相互重疊。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倡導的亞洲文明對話,道出了時代的心聲和各國人民的心愿。
“一帶一路”構想的核心是區域一體化,是沿線國家結成利益和命運共同體。要實現如此恢宏的目標,文明之間的對話和融合必不可少。只有文明之間平等對話、相互學習,合作伙伴了解和理解彼此的價值觀、思想體系、社會結構乃至風土人情,才有可能在經濟貿易諸方面進行全面合作,獲得共贏的結果。
就拿宗教來說,它在地緣政治中“貌不驚人”,但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巨大,往往決定著各文明之間、國家之間的關系框架。一個負面例子是,美國小布什政府進入新世紀后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并試圖以西方民主模式來改造伊斯蘭國家。但美國忽視了伊斯蘭文明對中東和南亞地緣政治的決定性影響和伊斯蘭內部派別的世代紛爭,結果教訓和損失慘重。美國學者亨廷頓對文明沖突早有深刻的闡述。
“一帶一路”構想以文明對話為引領,從文明融合和文化交流層面,實現沿線國家在文明包括宗教上和平共處、相互包容,意義深刻。例如連接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兼顧了周邊國家地緣文化和宗教因素,連接以儒教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圈和以伊斯蘭教為核心的阿拉伯及波斯文化圈。2009年,中國成為中東最大商品出口國和沙特石油最大買家。中國市場成為伊斯蘭金融投資優先選擇。
“一帶”將來不僅有四通八達的石油管道和基礎設施,還有涓涓流水的文明和宗教往來,拉緊儒家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傳統友好紐帶。“一路”上,中國與日、韓和東南亞國家由漢傳佛教形成的文明紐帶,如充分利用,將有助于政治溝通、增進了解、化解矛盾、防止沖突,為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對接創造條件。藏傳佛教在蒙古有較大影響,南傳佛教在東南亞有廣泛信仰基礎,同樣可以為“一帶一路”構想提供文明交流的渠道和平臺。
中國文化包容性強,我們有文明和文化自信。“一帶一路”構想包括亞洲基礎設施銀行(AIIB)就是開放的。 “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但一定會比“馬歇爾計劃”做得更好。“馬歇爾計劃”只是復蘇了西歐經濟,但它是排他性的,不向東歐國家開放,由此產生了美蘇冷戰。“一帶一路”不僅包含沿線國家,而且向各國開放。
“產能轉移”是對接的“關節”
亞洲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有些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鎮化,有些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還有一些仍在工業化初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對“一帶一路”建設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從中國發展經驗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需要有基礎設施支撐和適合本國國情的制造業和加工業。中國倡導“一帶一路”構想正是從這兩個方面出發,希望與廣大沿線國家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起跑器。只有基礎設施扎實,而且相互連通,經濟和貿易才能流動起來,才會出現經濟合作1+1>2的互補局面。為了填補亞洲基礎設施每年730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中國帶頭籌建了AIIB和絲路基金。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成功經驗是從80年代資本高度短缺,到現在資本凈輸出。這是中國從國際資本流動規律和過去自身資本緊缺的歷史中汲取的重要經驗。資本過剩需要走出去是經濟規律,全球化就是資本推動的。關鍵是中國資本不會走西方國家資本“無節制追求利潤”“每個毛孔都滴著血”的老路。
“大河有水小河滿”,中國資本走出去,要講經濟效益,更要體現大國擔當和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實現可持續發展。西方總是懷疑中國在“一帶一路”中藏了什么,在AIIB上有什么圖謀。這都沒有根據。從長遠看,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將使區域一體化邁上新臺階,中國及其合作伙伴都將受益。
中國目前產能過剩是現實,也是中國發展的必然現象。它不是壞事,而是中國發展惠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重要資源。在發展戰略對接中,通過轉移合適的產能和技術,沿線國家將獲得發展經濟的產業和動力。
“一帶一路”沿線除新加坡等少數富裕國家,都是發展中甚至貧困國家,都需要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過剩產能、資本和基礎設施建造技術這些國家都緊缺、都有需求。基礎設施投資大、工程大,而中國高鐵等產業都是優勢產業。這些工程需要鋼鐵、水泥、玻璃,又都是中國富余產能。很明顯這個產能合作既是優勢產能也是富余產能合作。這是從經濟層面看問題。
從戰略層面看,中國對世界的大國擔當是什么?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能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做些什么?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問自己這個問題。“三個世界”思想是當時“中國智慧”對世界的貢獻。而“一帶一路”則是今天中國對世界的擔當和貢獻。無論從國際經濟發展戰略出發,還是從區域可持續發展看,“一帶一路”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目前同時具有資本、產能和技術且可輸出的國家并不多,中國有這個能力。在習近平總書記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國以大國的胸懷和擔當提出“一帶一路”構想,真心希望中國發展戰略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充分對接,以實現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
要把“對接”放在大格局來認識和實施
我們絕不應該僅僅把“一帶一路”看作是經濟項目,那太狹窄、單一了。它更應是全球治理的突破口,是全球治理或至少是區域治理綜合施策之舉。我們現有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發展的結果。東亞、東南亞目前的秩序則是美國地緣政治延伸的產物。國際政治的現實是,美國相對衰落及其地緣影響力下降,與中國崛起和影響力擴大,將在21世紀長期并存。這決定了全球治理將從主要是“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逐步轉變。當然,這一歷史時期會持續較長時間,也不排除出現曲折。
關于“一帶一路”,中國表示,亞投行將是世界銀行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已難以滿足和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也就是無法履行全球治理體系應盡的責任。發展戰略對接需要合適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全球治理體系的配套。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以西方“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模式”為理論模式的全球治理體系信譽掃地,體系本身也是“千瘡百孔”,亟需改革。二十國集團(G20)興起,并替代“七國集團”(G7)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協調平臺,是大勢所趨。雖然,G7還在國際舞臺上“苦苦掙扎”,如日本前不久推動G7外長會議通過所謂關于海洋安全的聲明,企圖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但畢竟作用很有限。“一江春水東流去”,G7風光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發展戰略的對接需要國際秩序的調整,這種調整實際早已開始,但需要長期的探索和磨合。G20近年在國際金融領域和全球治理機制調整的頂層設計上的舉措,如調整IMF和世界銀行的份額和投票權,雖因美國國會阻擾而未果,但勢頭已形成,國際社會必須承認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的現實,并相應調整全球治理體系。
現實就是秩序,存在決定一切。這就是我們天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的根本考慮。你發展了,塊頭大了,秩序就要圍繞你來調整。關鍵是要充分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提出建設人類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希望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各國發展戰略能夠對接,走共同發展的道路,目的是要打破過去“國強必霸”的強權邏輯,建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以及與之配套的全球治理機制和體系。“一帶一路”是中國從人類命運體的角度出發對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貢獻。
為什么發展中國家不喜歡IMF和世界銀行?這不是他們矯情,而是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思想阻礙了資本的正常流動。IMF和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有許多苛刻的條件,如民主、自由、人權、宗教,與你經濟毫不相干的東西,它都要管。否則,對不起,沒錢給你。這其實也正是美國在背后阻擾亞投行的根本原因。發展中國家有了亞投行可以不吃世界銀行那一套了。當然,亞投行投資決定不會不講經濟規則,會按國際規則行事,但肯定不是西方定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