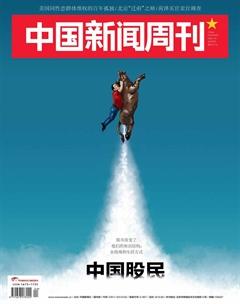另一面的陳云
徐天
稿件刊出后,有同事和我說,她喜歡那篇《評彈里的性情陳云》,因為發現了陳云的另一面。
其實,這就是這組稿件的初衷。
在公眾視角或者宣傳體系中,陳云是“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為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杰出貢獻”。
過去,我眼里的陳云亦是如此,扁平且標簽化。這次,為了認識不一樣的他,采訪了十余名在他身邊工作或者和他接觸過的人。
吳宗錫,上海評彈團的老團長,已90多歲,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交往,他從他們第一次見面說起,直到回憶起二人最后一次往來。
采訪徐檬丹時,她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陳云。她說起,陳云喜歡她在文革后創作的兩部中篇評彈,分別是《真情假意》和《一往情深》,來回聽了許多遍。當時正處于人生轉折期的她,因得到陳云的肯定而自信倍增,自己是被陳云“扶上馬”的。
徐檬丹說,近期才得知,陳云離世前,聽的最后一個曲子,是自己創作的《一往情深》。說到這里的時候,她忽然停頓不說話,眼里全是淚。
我滿心震撼。人心間的輝映,并不只存在于普通人之間。這個沒有見過陳云的人,如此誠摯。
后來,我又陸續見了陳云身邊的秘書、警衛人員、醫生和護士。
他們告訴我,陳云工作很忙,兒孫很少打擾他。有時候陳云想見孫子輩,就會向妻子于若木要點錢,讓工作人員去買山楂片,然后用山楂片“誘惑”孫兒們來看自己。后來,孫兒們漸漸長大,山楂片越來越不起作用。
陳云晚年練書法,有時候寫完了,就問陪在身邊的人,好不好看。小護士嘴甜,會說老爺爺寫得真好看。陳云大笑,把書法送給了那個小護士。
當然,也有人和我坦承,在領導人身邊工作,壓力非常大,生怕出任何狀況,釀成大錯。有的人甚至養成了吃安眠藥的習慣。
他們中有的在醫院陪伴陳云最后一程,也有的離開陳云做了其他工作。但他們每年都會在陳云忌日這一天,和陳云的孩子一起去八寶山祭奠他。秘書會給陳云講講國內外的大事,兒孫們則會匯報家里的新進展,比如誰結了婚,誰有了孩子。
每當這個時候,他們都會覺得,這個晚年甚少外出、但是愛笑而隨和的老人家,就像尋常人家里的爺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