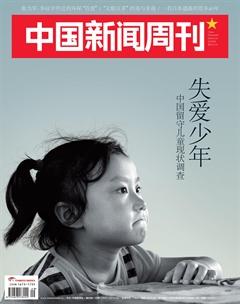中國成為區域及全球大國的新階段
杜大偉
曾任美國財政部駐華經濟與金融特使,世界銀行中國與蒙古局局長,現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

美中兩國的計劃具有互補性。中國的計劃資助的基礎設施是貿易與投資的硬件,而美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在另一方面,則代表了一體化中的軟件,有利于降低貿易阻礙,開放貿易與投資服務。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保持著快速發展的態勢,但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中國的發展模式出現了重大變化。在2007年之前的六年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增長率為11%,其中投資占GDP的41.5%。在該階段,中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持續上漲,占GDP的10%以上。在危機之后的六年里,中國國際收支順差陡降至2%?3%,但是需求的下降幾乎全被投資增長所彌補,近年來,投資在GDP中的比例已超過50%。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發展引人矚目。然而在受到贊賞之余,中國的增長率眼下已經下降到7%左右的事實卻被忽視,而這比危機發生前減少了四個多百分點。因此,中國近期采取了大量投資的舉措,但經濟增長率卻低于從前。
這一發展模式反映出三個問題。其一,根據全要素生產力(TFP)增長的測評結果,中國的技術進步已經放緩。與此密切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資本的邊際效益正在下降,其結果是,增加投資卻產出更少。而這反映在現實中,便是那些空蕩蕩的住宅樓、未使用的機場,以及重要制造部門里嚴重的產能過剩。第三個問題是,消費水平十分低下,尤其是家庭消費僅占GDP的三分之一。
針對變化中的增長趨勢,中國對內對外均做出了反應。從外部看來,在國內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中國啟動了諸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金磚銀行以及“一帶一路”等新計劃,這些計劃的先后推出并非巧合。亞投行的誕生主要是出于對現存國際金融機構管理的改革發展緩慢的疑慮。而“一帶一路”計劃比亞投行規模更大,該計劃希望在中國經中亞通往西方的路線上以及從中國經東南亞通往南亞、非洲及歐洲的路線上強化各地的基礎設施。
中國的亞洲鄰居十分歡迎這類舉措,這也有利于亞洲一體化。然而,認為這類計劃可以解決國內過剩產能問題的看法大多是具有誤導性的。這類計劃對中國需求的貢獻可能微乎其微,而且并沒有太多宏觀經濟學上的意義。
作為對產能過剩問題的內部反應,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來加以應對。這些措施中對中國經濟增長下降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分為四個領域:戶籍登記制度、政府間財政改革、金融自由化以及開放中國服務業。以上四個領域的改革形成了一組連貫的措施,可以控制住浪費性投資,提高創新與生產率增長,并提升消費水平。這些領域的成功改革將會使中國在下一個十年甚或更長的時間里保持持續的增長。
在很多人眼中,中國在亞洲的一系列計劃對美國來說是一種挫折。美國政府通對其盟友加入亞投行的勸阻反過來印證了這種說法。最終,美國的幾大盟友——英國、澳大利亞以及韓國都加入了中國的這項計劃,日本也在仔細斟酌加入事宜。
但是,這可能僅僅只是美國外交上一次暫時的挫折。各國對亞投行的反應清楚地表明,亞洲和歐洲國家不愿意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也沒有理由令他們非要做出這樣的選擇。美國在對待亞投行的問題上做出了錯誤的反應,但美國也無需夸大這一問題的影響。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經濟計劃——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可能將在2015年年底完成。這一計劃著眼于通過夯實21世紀貿易的基礎,將貿易擴大到服務業等新領域。我們已經注意到,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與越南等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都想同時加入中國(亞投行及“一帶一路”)與美國主導的計劃,以此減少貿易阻礙。 他們所采取的顯然是聰明的策略。
其實,各國的不同計劃都是互補性的。中國的計劃中資助的基礎設施是貿易與投資的硬件,是深化一體化進程的必要非充分條件。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在另一方面,則代表了一體化中的“軟件”,有利于降低貿易阻礙,開放貿易與投資服務,并協調各類監管壁壘。
當然,有人擔心,美中之間這些競爭性的計劃有導致地區壁壘、貿易分解的風險,但我認為更可能的結果是帶來雙方的合作。美國也將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中獲益,因為它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的一個重要的新機制。
總而言之,美中之間相互競爭的計劃將產生更有力的機制,從而進一步深化亞太地區的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