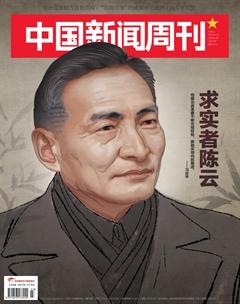《大憲章》800年
彼得·辛格
當飛離倫敦西斯羅機場的時候,你可能會飛越一片叫做蘭尼米德(Runnymede)的草地。八百年前的這個月,這片草地色彩斑斕,遍布著男爵和騎士的帳篷,更有規模更大的英格蘭約翰王的王帳,它們看上去像是飄蕩著王旗的馬戲團。
這次集會看上去像是一次游園活動,但氣氛無疑是非常緊張的。集會的目的,是調和反叛的貴族和英國國王之間的沖突,用當時人的話說,國王“惡貫滿盈”。
約翰王想要籌集資金用于奪回在法國失去的土地,他所籌集的資金額超過了貴族從先人手中繼承的常規稅費的規模。而且,國王沒收了富裕貴族和商人的地產,有時連人也一起劫持,然后索取巨額的贖金。
如果連年的斂財帶來的是勝利,約翰王大概也不會那么專斷了;但是,當他在法國落敗而歸時,一群貴族奮起反抗并占領了倫敦。作為坎特伯雷大主教居間調停的和平協議的一部分,國王最終接受了貴族們的要求——簽署一份被稱為《大憲章》(Magna Carta)的歷史文件。
《大憲章》并不是英格蘭王所授權的第一份憲章。早在一個世紀以前,亨利一世就頒布了《加冕憲章》(Coronation Charter),以示其將比前任更加尊重貴族特權。但亨利一世的繼任者很快又回到了國王專斷的老路上。
《大憲章》看上去也不會維持多久。很快,它就被與國王結盟的教皇英諾森三世取消了。但在第二年,約翰王駕崩,貴族們需要支持其繼承人、年僅九歲的亨利三世,以對抗覬覦王位者。為了贏得支持,亨利政府重新頒布了其自身的《大憲章》,至今,它仍是英國法律的一部分。
《大憲章》被復制了多份,頒發給大英格蘭地區的多家教堂。拉丁語原文則被翻譯成貴族的語言——法語,然后再翻譯成英語。到世紀末時,英國農民也開始引用《大憲章》與不公進行抗爭。
第一份印刷版的《大憲章》于1508年問世。17世紀40年代,議會從《大憲章》中尋找推翻查理一世的法律依據。后來很多起義,包括美國革命和南非曼德拉所領導的運動,都援引《大憲章》來論證他們的行為。
這些正義和自由之士從這份3500字的文件中所獲得的,是應對約翰王專斷臣民物權和人權的關于通用原則的簡短陳述。例如,《大憲章》第39章說:“自由民,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傷害。”它在第40章則簡潔地表述了另一項強大的原則:“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絕或延擱其應享之權利和公正裁判。”
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是這兩章的現代回音,它規定,“如未經法律程序”,各州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 或拒絕任何人“獲得法律的平等保護”。
但《大憲章》并不是一份民主文件。盡管它規定稅收必須以“一致同意”(common consent)為前提,但這一同意是通過高等和低等貴族、主教和修道院長的集會而形成——在騎士制度的時代,就連騎士也無資格參與這樣的會議。
當時,人們形成這樣的觀念,即倫敦等城鎮應產生自己的代表,但是在《大憲章》最終的文本中卻難覓這一內容的蹤影。因此,《大憲章》表明,“誰統治”是一個問題,“如有,政治權力的界限在哪里”則是另一個問題。
《大憲章》試圖為政治權力規定界限,但又不把這一界限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之上,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讓哲學家們為此糾結了八百多年。既然約束統治者的原則既非來自統治者,也非來自臣民,那么它們來自何方呢?
自然法傳統提供了一個中世紀學者所熟悉的答案。對他們來說,自然法可以通過我們的“自然理性”來理解,相反,另外一些法律只能通過“天啟”而得到發現。《大憲章》的關鍵原則可以視作為理性所啟發,因為法律的思想排除了專斷的逮捕和沒收,也排除了以法律合理應用之外的基礎所做出的裁決:如果依法A必須在B的奶牛進入A的土地時將它歸還給B,而C的奶牛在基本類似的情況下進入了B的土地,B也應該因由法律之義務而歸還C的奶牛。C不需要賄賂法官才能要回自己的奶牛。
事實上,《大憲章》并沒有阻止制定和實施不公正法律的內容;但它確實讓法律位于統治者的意志之上。然而不幸的是,這一思想迄今尚未被許多國家所接受。我們知道,美國在關塔那摩島的監獄還一直存在著,這表明,即使在以《大憲章》為政治制度源泉的國家,對安全的威脅感也削弱了《大憲章》當時所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