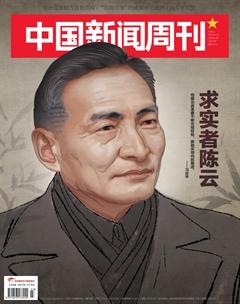是什么“殺死”了中國綜藝節目的原創性?
高敏
今年各大衛視播出的真人秀已火爆熒屏,這把“火”也從電視熒屏“燒”到網絡世界,不斷引發現象級話題。
引發關注熱潮的節目,多為引進海外模式,這些節目備受追捧的背后,國內綜藝原創性不足的問題凸顯出來。
海外模式熱潮
2013年在業界被稱為“版權引進年”。據統計,當年各電視臺播出的引進海外模式節目多達56檔,“洋節目”扎堆熒屏,引得廣電總局當年10月即下發限制政策:要求每家衛視每年播出的新引進境外版權模式節目不得超過一個。
然而,各大衛視對海外模式如火的熱情并未被限制政策澆滅,反而愈演愈烈。據樂正傳媒統計,2014年,全國各電視臺及視頻網站播出海外模式節目共61檔。只是以“聯合制作”的名義替代了“引進境外版權”,搖身一變成為“混血綜藝”,打了政策的“擦邊球”。
從今年已經開播的真人秀和即將涌進暑假黃金檔的節目來看,海外模式熱力仍不減,樂正傳媒研發與咨詢總監彭侃結合往年統計,今年引進海外模式節目不會比去年少。
追溯國內綜藝節目的“拷貝史”,央視應該是鼻祖,1990年的“骨灰級”綜藝節目《正大綜藝》,即由泰國正大集團旗下傳媒公司提供。而CCTV5于1998年首播的《城市之間》,是對法國電視臺老牌節目的同名引進。
2012年的《中國好聲音第一季》,可謂引入海外模式的“典范”。節目取得荷蘭THE VOICE的代理權后,獲得了對方提供的多達數百頁的節目制作“寶典”。從人員分工到機位布置都給出了詳細指導,甚至導師拿麥手勢、轉椅的設計都事無巨細,更派出“飛行制作人”全程跟蹤節目制作。這個精細拷貝的節目的大獲成功,可以說是2013年引進熱潮的“導火索”。
節目模式,在世界電視行業內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產品,世熙傳媒董事長劉熙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全球每年電視節目模式的交易規模可達三四百億元,節目模式這個產品在很多國家之間互相買賣已是常態。”
節目的創意固然重要,但業界更看重的是節目背后一整套結構和系統的操作方法,這是節目模式真正價值所在。《中國好聲音》或許是最具說服力的案例之一,甚至導師轉椅都從國外運來。業界更愿意將節目模式看作“工業化生產的產物”,“節目背后的東西更具實用性,這也是大家花錢去買模式的一個理由。”樂正傳媒研發與咨詢總監彭侃說。
引進與跟風
國內電視節目仿佛進入這樣一個“怪圈”:引進、模仿,再跟風引進、跟風模仿。
彭侃通過對2014年引進模式分析,得出韓國取代美國成為了中國節目模式最大的進口來源國這一趨勢。湖南衛視的《爸爸去哪兒》和《我是歌手》均引進自韓國MBC電視臺,節目大火之后,各大衛視緊隨其后,瘋狂追逐韓國綜藝。
“2014年,國內電視臺共從韓國購進了12檔節目模式,如果算上與韓國電視臺或制作公司聯合研發的新節目,這一數字還會翻番。”彭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韓國與中國地理位置臨近、交通便捷,原版節目制作團隊可以深度參與中國版節目的制作。如浙江衛視的《奔跑吧,兄弟》前五期,便主要由韓國Running Man的制作團隊操刀。相似的文化背景,更推高了國內電視臺對韓國模式的熱情。
在劉熙晨看來,近兩年來的“韓國模式熱”更主要的原因或許在于韓國模式進入的策略,“他們進入中國市場時,有意無意選擇了最好的平臺。”從《爸爸去哪兒》和《我是歌手》開始,選擇與中國最好的電視平臺和制作團隊合作。被網友調侃的抄襲界潛規則:“過去湖南抄歐美,全國抄湖南,這回湖南抄韓國,全國依舊抄湖南”,或許不無道理。
“全國抄湖南”大致有兩種途徑,“高明”一些的跟風引進韓國節目,更簡單一點的,跟風制作同題材節目。《爸爸去哪兒》爆紅后,各大衛視的“親子節目大混戰”蔚為壯觀:青海衛視《老爸老媽看我的》、陜西衛視《好爸爸壞爸爸》、以及浙江衛視的《爸爸回來了》等,二十多檔相關節目扎堆出現。
中國電視節目“一窩蜂”跟風現象并非近兩年才出現,而電視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競爭壓力,導致了不斷升級的同質化競爭。
不同于其他國家業已形成的幾大電視臺“寡頭壟斷”的局面,中國條塊分割的體制要求每個省都有衛星電視臺,導致存在諸多定位相同的頻道。一省一個衛星頻道,加上CCTV1,綜合頻道就有三十多個。
業界人士往往用“惡劣的競爭環境”來形容當今國內電視臺的市場競爭。“觀眾買賬的電視節目類型就這么幾種,三十幾個頻道,必然會跟風,這是一個結構性矛盾。”劉熙晨說,各省電視臺不能跨區域整合,不能強強聯合,(跟風)也是無奈之下做出的選擇。
在電視界從業多年,同時在高校擔任教職研究電視節目的張紹剛,更愿意將原因歸結為“功利化心態”,“當大家對自己都不夠自信的時候,才會出現同質化。我可能掙不多,但也賠不死。當大家都以這種功利的心態來做節目時,就沒有人嘗試新內容,而是一味跟風。”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綜藝為何缺乏原創
引進海外模式熱潮、同質化跟風,是國內綜藝原創性不足的外在表現,而內在原因更多被歸結為體制原因和逐利的功利心理。
從國外經驗來看,歐美國家電視行業進入市場已有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投資方都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競爭。而中國電視臺過去一直都是事業單位,實行行政化的管理,投資方是國家,導致缺乏優勝劣汰市場機制。在劉熙晨看來,只有建立起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市場機制,才能夠推動節目模式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產生創新。在他看來,這是中國電視缺乏原創性的歷史原因。
現實邏輯是,中國電視界惡劣的競爭環境驅動下,電視臺主管往往趨于保守。“沒有哪個國家有中國這么多的電視臺,在激烈的競爭環境當中,拼收視率,盡可能保證成功是電視人更愿意選擇的穩妥方法。”彭侃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
在保證宣傳安全外,爭奪收視率和廣告收入是當今電視臺最急迫的兩大任務。在面對原創節目方案和國外已經成型的成功產品時,選擇后者顯然是更為討巧的做法,對電視臺主管和廣告客戶們的說服力都要更強。
從制作角度講,購買國外成熟模式相比自行原創,也具有效率更高,少走彎路和降低成本的優勢,彭侃說,原創拼不過成熟模式,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當今電視臺將‘掙錢作為很重要的事情,急功近利的心態下,很多有發展前景的節目,比如素人(網絡詞語,指普通人)秀 ,都不敢去嘗試。大家都在追逐成效立竿見影的節目。” 張紹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原創嘗試的期望最終還需寄托在一線電視臺身上,包括CCTV,但CCTV的制作和經營亦受到嚴重的擠壓。廣告賣不到高價,做原創精品節目的預算就沒有,所以還是萬惡的金錢在作祟 ”。
所謂原創,無非是內容和形態兩個層面。
從內容層面講,有待開發的空間領域非常多,比如親子類、社會服務類、生活服務類,在張紹剛看來都有很大缺口。他將《爸爸去哪兒》歸為一類“玩小孩兒”的娛樂節目,與親子類或是教育類無關。
至于形態方面,現今面臨的真人秀節目的“井噴”,反映了功利心態的驅使下追逐流行的姿態,而放棄了去尋找新的節目形態。
國內電視節目粗放式的生產方式,亟需市場這只“無形之手”介入,來推動創新;而市場邏輯下越來越現實和功利的心態,似乎又成為原創的阻力。這樣的矛盾或許是中國綜藝原創性不足的內在邏輯。
必經的階段性過程
不可否認的是,引進海外模式,在全世界都是電視節目發展的一條必由之路。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世界上購買節目版權數量最多的,其實是美國。
國內目前爭相購買模仿韓國模式,而韓國節目也不盡然都是原創,最初通過模仿國外創意,將其很好地本土化,加入本國元素才得以發展。韓國也是經過十幾年的模仿和摸索才逐漸有了自己的風格。據業內人士介紹,韓國《隱藏的歌手》節目,即脫胎于瑞典節目。
中國電視節目的實踐也在證明這點:模仿和引進海外模式,是一個必經階段。
而跨越過“引進模式”這道門,國內電視節目將去向何方似乎是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從事多年節目引進和開發工作的劉熙晨認為,模式的引進和銷售應該是一個常態的行為,現在引進,將來售出。隨著中國創意和制作水平的提高,我們也會不斷把我們的模式賣出去,中國的節目模式能夠具備原創新和可復制性,具備很好的市場性和國際銷售能力,這是我們節目未來追求的方向。
作為市場參與者,從業者遵循的往往是一套市場邏輯。劉熙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所認為的成功模式,就是可以在很多國家銷售流動的節目。浙江衛視的《中國好歌曲》據稱已出口英國和越南,但這在他看來并不算是成功。“我們的標準就是你能賣到多少個國家,當一個模式賣給一兩個國家的時候,這樣的模式太普遍了;當一個模式賣給十幾個國家時,它才是一個真正的好模式,這是一個標準。”
從教多年的張紹剛則更執著于“意義”和“情懷”。他認為我們的目標不是通過談論國內的節目“走出國門”來自我滿足,我們不應以出口為目的。首先要做到的,應該是讓普通觀眾耳目一新。
“我們做節目,除了收視率之外,總要有些情懷吧。”張紹剛經常在課堂上這么對學生說。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也喜歡看《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等節目,但僅限于當作娛樂節目來看。“一定有節目是娛樂的,但是一定不能所有節目都是娛樂的。”
當前各大電視臺“砸錢”引進制作的節目,值得注意的是,幾乎都是“明星秀”,這也使國內節目創新陷入尷尬境地。明星的身價隨著節目的火爆和各大衛視的爭搶“水漲船高”,讓缺乏資金的電視臺陷入窘境:跟風“明星秀”卻無資金,導致粗制濫造;通過計算投入產出比,又沒有底氣嘗試新模式。
因而,在張紹剛看來本應成為下一個“現象級”節目的“素人秀”,遲遲得不到關注。無獨有偶,業界人士也對“素人秀”的未來抱有期待。彭侃則預測,不排除廣電總局將頒布限制“明星秀”的新政策的可能,從節目進化規律來看,“素人秀”存在很大發展空間,或許有望“逆襲”。
至于韓國模式的熱潮會持續多久,劉熙晨認為并不會長久,跟風總會持續下去,但面對激烈市場競爭下“見風使舵”的國內電視主體,韓國模式并不能持續多久。
或許,“拿來主義”進行到一定階段,隨著國內節目制作水準的提升,跟風引進國外模式的“燒錢”行為有望“降溫”。擁有了自己真正兼具原創性和市場性的節目,中國電視熒屏被海外“創意舶來品”占據的尷尬局面或許可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