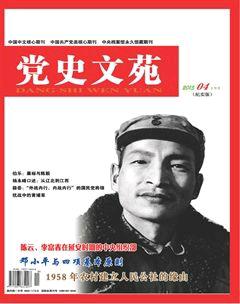抗戰中的黃埔系
黃修毅
“黃埔”聯結著中國近代戰史上絕大部分軍功顯赫的名字,除國民黨軍中的3000多員將領外,也為共產黨培養了53位將軍。這所在因陋就簡的條件下草成的軍事學府,與美國西點軍校、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俄羅斯伏龍芝軍事學院等并稱“世界四大軍校”。
抗戰八年,有200多名黃埔教官、學生擔任師長以上職務,指揮全國三分之二的抗日之師;抗戰勝利前畢業的前19期黃埔學生約20萬人,更充實著各級部隊的基層干部崗位,“黃埔系”挺起了中國軍隊抗戰的脊梁。
“黃埔部隊多已打完,其余當然望風而潰”
1937年淞滬抗戰初開之時,一班年輕軍官冒著炮火聚集上海江灣某隱蔽所,站在臺前訓示的,正是被委任為淞滬警備司令的前黃埔總教官張治中。
當日聽眾中,職銜最高的桂永清,也不過是上校副師長。日后在國民黨軍中任兵團司令的長沙分校學生廖耀湘,還只是個中校參謀主任;后在解放軍中官拜上將的黃埔一期學生周士第,此時遠遠落在了同期生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后頭,別人都當上了軍長、師長,他還只是個師參謀。
張治中的話在年輕人頭腦中嗡嗡作響,不亞于日軍炮火的一次次叩擊。他說:“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到后方擴軍,大家升官,我升集團軍總司令,你們營長升團長,團長升師長,師長升軍長;另一條是到前方作戰犧牲。兩條路走哪一條,請各位自決!”
淞滬血戰三月,為達成“趕敵下海”的戰略目標,投入戰場的黃埔軍為作戰最得力之部隊。1934年以來,國民政府即著手以“中央軍校教導隊”擴充而成3個全德式裝備“示范師”為樣板,整訓陸軍60個師之計劃,于此時已完成大半。美國記者斯諾曾記述道:“1937年的中國陸軍是該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一支。”
在楊行、羅店等抗戰初期爭奪最激烈的戰場,統軍者正是黃埔系大佬級人物胡宗南。
與蔣介石同為浙江老鄉,報考黃埔時因身高不足被破格錄取的胡宗南,此后在軍中的節節躥升卻是高度驚人。抗戰爆發時,他已是純黃埔血統的蔣介石嫡系部隊國民革命第一軍軍長;待到武漢會戰失利,蔣非但未追究其罪責,反嘉許其為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遂以43歲之齡,成為黃埔畢業生中擔任上將第一人。
胡宗南“老大哥”身份的奠定,還要上溯到1927年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他當時正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副師長身份,率部駐防杭州。
彼時桂系欲趁機施壓,遣散駐扎江浙的國民革命軍7個主力團,甚至設計迫使黃埔軍北上獨拒孫傳芳,而由桂系軍隊接防江南,以斷其后路。世故老到的胡宗南,憑借在“黃埔同學會”中施展手腕,聯合7個團的將領拒不從命,從而保存了“黃埔系”實力,博取了蔣的信任。
此后其所在的第一軍不斷擴編,在抗戰初期成為蔣最為倚重的部隊。1937年9月,胡宗南受命馳援淞滬戰場,在楊行初接敵,即展開血戰。淞滬警備司令部作戰科長到第一軍訓視,留下了如此記錄:“該軍已補充兵員四次,接防換防五次,總算能頂住。第一師旅長先后傷了3個,團長先后死傷5個,全師連長除通信連長外,余均傷亡換人。”
胡宗南率部白天隱蔽在竹林村莊,任敵機投彈掃射,不輕易出擊,如此“守多攻少,反可持久”,硬是死守陣地逾一周。直到戰區副司令顧祝同接通第一軍軍部電話,告胡宗南當晚派部接防時,他才吭氣:“再不換防,明天我也要拔槍上火線頂替了。”
淞滬抗戰功虧一簣,全國各地的部隊蜂擁在撤出上海的道路上,相互擠踏,狼狽不堪。胡宗南實在看不過去,于11月20日致函密友戴笠(黃埔六期):“弟刻又在無錫進入陣地,此前前方撤退各軍,秩序紀律毫無……黃埔部隊多已打完,無人支撐,其余當然望風而潰。第二期革命已失敗,吾人必須努力,培養第三期革命干部,來完成未來之使命也。”
“無堅守陣地之羈絆,反覺海闊天空”
武漢失陷后,蔣介石在南岳主持召開了有第三、第九戰區各部隊指揮人員參加的“第一次南岳會議”,這抗戰以來首度召開的軍事檢討會,陣容相當整齊,每位與會代表均按號次入座,并佩掛識別證。
會上,蔣介石首次提出了把中日戰爭劃分為第一、第二兩個時期的理論,宣布中國抗戰轉入戰略防御階段,“以時間換取空間”以期最后的勝利。這一戰略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曾擔任黃埔軍校軍事顧問團團長德國將軍塞克特的影響,其在1938年5月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前,就得出了“只有時間才能救中國”的結論。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茲后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把“策應敵后之游擊隊,加強敵方控制區之擾襲”列入了指導方針,明確了將“三分之一的部隊留在敵后作游擊戰”的布置。
故而在華北、東南沿海淪陷地區,不僅活躍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更盤踞著大量游擊化的國民黨正規軍。黃埔一期生李默庵后來被譽為“國軍中的游擊戰干才”,在晉南多次發動對日軍馬車站、運輸隊的擾襲,予敵以重創,由第十四軍軍長升任第三十三軍團軍團長。
1937年9月至11月間發動的忻口會戰,以黃埔四期生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捷”最為耳熟能詳。彼時參戰的部隊主力實系李默庵的第十四軍,在其所鎮守的左翼戰場上,中國軍隊以散兵戰壕阻擊日軍之坦克。晚年李默庵曾回憶:“對中國守軍威脅最大的是坦克車,第十師二十八旅五十七團的一個連,遭敵坦克攻擊,橫碾該連的臨時戰壕。官兵被碾埋一半,無一退避。”
在這場殲敵2萬余的大戰中,中國軍隊付出了兩倍于敵傷亡的代價。給這批黃埔系軍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軍訓練精良,射擊準確,其戰術法則,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難敵對手。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中條山區,開始了對敵游擊戰。
李默庵與中共軍隊合作無隙,收獲了“土嶺大捷”等一系列游擊戰成功戰例。李默庵的部將、黃埔三期的石覺曾在作戰總結中寫道,“我各級官兵,對于敵后之游擊戰術,較抗戰初期——晉西蒲縣游擊時,大有進步。無堅守陣地之羈絆,反覺海闊天空”。endprint
1938年春節,李默庵專程跑到洪洞縣牧馬村八路軍總部拜年,與他的老鄉、黃埔一期同學,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的左權交流游擊戰經驗。而那位在忻口會戰中立下奇功的黃埔四期師弟林彪,因赴蘇聯療傷,從此在抗日戰場上缺席。
“中國軍隊有能力獨自發動攻勢”
隨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形成,以及盟軍在太平洋戰場形勢的扭轉,中國軍隊開始了大規模主動出擊,精銳部隊則被推向了國門以外的滇緬戰場,這支部隊吸收了大量知識青年入伍,當時的國人“為百年來首次出境作戰”而鼓舞。
第一次遠征緬甸的統帥杜聿明,是黃埔一期出身,但比起胡宗南等同期老大哥,他因與長年的頂頭上司關麟征(黃埔一期)相處不睦,而在黃埔系中一度處于邊緣狀態。但是,他當年賭氣之下隨徐庭瑤去創建的“快速機械部隊”,到了20世紀40年代卻已然上升為國軍中的精銳。
事實上,早在臺兒莊戰役時,杜聿明就曾率所部馳援過外圍戰斗,但因蘇聯支援的戰車(5噸級炮戰車87輛)和從意大利購買的戰車(3噸級槍戰車200輛)尚未運到,可供他實際調配的僅一個戰防炮團,中國戰場上的“裝甲大戰”終未發生。但日軍在臺兒莊拋下的幾具戰車殘骸,亦打破了此前的作戰常態,“日軍未有遺裝備予敵的陳跡,因彈盡油絕,而棄車戰場,足見其潰退之狼狽”。
入緬之時,杜聿明一手建立的第二○○師已擴充至第五軍,配備了炮戰車59輛、槍戰車55輛、各型汽車1000輛;而他手下的得力戰將也都系黃埔出身,鄭洞國黃埔一期,廖耀湘黃埔六期,戴安瀾黃埔三期。
擔任史迪威聯絡參謀的王楚英,初見杜聿明,即留下了這般印象:“看起來好像不像一個將軍,沒什么大的威嚴,像個教書先生一樣,講話慢條斯理,分析問題很中肯。”
杜聿明和未來的上司初次見面,即給史迪威留下了良好觀感。他一走進作戰室,發現墻上掛有二十萬分之一和百萬分之一的緬甸全圖,系英軍于1941年航測而制,十分詳細新穎,頓時眼睛為之一亮。還未落座,他就轉身對史迪威發難:“地圖對戰地指揮官何等重要!我們軍中卻還在用30年代中期英軍測制的老圖,這種過了時的軍用地形圖早就應當銷毀了,豈能發給作戰部隊使用?”
不想,史迪威非但不尷尬,立時迎面握住他的手,主動歷數起此前杜聿明在古北口與昆侖關作戰中樹立的聲威。杜聿明的實干作風,讓史迪威一反常態地放下了輕視國軍將領而不假辭色的常態。
此后的作戰中,杜聿明敢于放言“能以一師兵力抵擋日軍一師團(相當于兩師兵力)”,頗得性喜“攻勢作戰”的盟軍指揮部贊賞。直至制訂曼德勒會戰計劃時,盟軍參戰各方的戰略目標分歧,導致杜當場與指揮過諾曼底撤退的英軍名將亞歷山大翻臉:“貴軍既然決心放棄現陣地,繼續撤退,那就請你們自便吧!中國軍隊有能力獨自發動攻勢。”
結果到了戰場上,英國人臨陣退卻,致使杜聿明手下戴安瀾之第二○○師雖在同古作戰英勇,但幾遭覆滅之災;廖耀湘之新二十二師在曼德勒以東孤軍難支。1942年5月26日,戴安瀾殞命緬北之日,與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血灑太行,只隔了一天。而與左權同為黃埔一期的共產黨將領徐向前與陳賡,在1949年建制之后,于1955年分別被授予元帥和大將之銜。
兩位黃埔高材生飲恨疆場,也是抗戰中犧牲的數以十萬計的黃埔師生縮影。據日本投降后的統計資料顯示,黃埔畢業生在戰后幸存者僅11000多人,相比之抗戰期間入校受訓的20萬學生,“黃埔系”在抗戰中的犧牲率高達95%。
到了1945年末,杜聿明部被從滇緬調往東北戰場,可謂二戰末期最遠程的跨緯度軍事轉運。此時他要面對的對手,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在抗戰中閃亮登場,此后卻幾乎被外界遺忘的師弟——林彪。○
(本刊編輯部摘自《人民文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