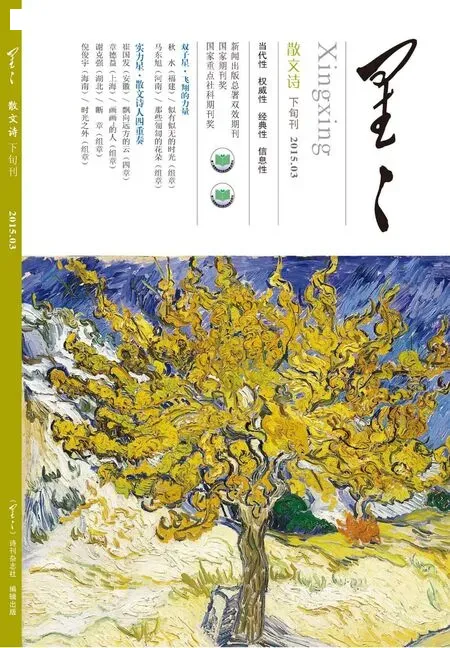梯子(外一章)
汪峰
他不停地?fù)v騰著木料,把森林變成樹(shù),把樹(shù)變成木頭;他不停地把木料用鋸、刨、刀、鑿、墨尺變成長(zhǎng)短、方圓、粗細(xì);他不停地敲擊、校勘、接榫、扶正,將木頭變成一個(gè)安分守已的器具。而這個(gè)器具僅僅是把山的高度衍變成了一個(gè)不斷攀高的梯子。山的高度是有限的,而梯子的高度是無(wú)限的。
一個(gè)造梯子的人,他在把山改成梯子的過(guò)程中無(wú)聲地活著,在一個(gè)不為人知的小木房里抒情,和陰暗、潮濕相依為命。大量時(shí)間將自己活埋,而他有一部分時(shí)間在山上尋找靈感。在他逝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鐘,他從沒(méi)有活得比山更高。但他在日灑雨淋中,在悲霜苦雪中,努力咬住自己的根。這個(gè)木匠,他長(zhǎng)時(shí)間把自己關(guān)在時(shí)間的內(nèi)部尋找自己垂直的路徑,于是他想到了梯子這個(gè)注定要和天空靠近的路。因之他的未來(lái)成了一步步敞開(kāi)的風(fēng)景。
他在山中摸索了一段較長(zhǎng)時(shí)間。他沿著每一棵樹(shù)每一根藤條所要去的方向不斷地開(kāi)采著智慧。這等于他一遍又一遍地踩遍自己每一寸肌肉,搜括自己青春最顯而易見(jiàn)的財(cái)寶。
一個(gè)造梯子的人,是美夢(mèng)成癖的人。一個(gè)造梯子的人,他在美夢(mèng)中飛,翅膀里面藏著沒(méi)人看得見(jiàn)的梯子。
梯子來(lái)源于山中的一個(gè)偶然的想像。在這個(gè)想像中,一個(gè)兒童指望順著鉛筆爬上天空。他要讓星光成為一朵朵牽牛花盛開(kāi)在幼兒園里。而他的童年只生活在他自已的天堂里。他的愿望來(lái)源于對(duì)梯子簡(jiǎn)單算術(shù):每一分鐘都往上增加一格,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到達(dá)天上:“黃金的花朵一舉手,梯子就來(lái)到它們手里。”
一個(gè)造梯子的人,我是不是在他的夢(mèng)中醒來(lái)的?我告訴他:“我像一個(gè)背負(fù)梯子走路的人,我想登上高處,現(xiàn)在卻要把我趕向遠(yuǎn)處。一個(gè)人走到山崗上又從山崗上走下來(lái)。只想掏高處的一個(gè)鳥窩。我攀爬著梯子慢慢來(lái)到那思想的最高點(diǎn)上,我知道我和神啟越來(lái)越近,鳥蹲在梯子上,把它當(dāng)作一棵樹(shù),夢(mèng)著梯子和瞌睡一同發(fā)芽。會(huì)飛的小動(dòng)物,它是舉著內(nèi)心的小梯子飛翔的。”我告訴他:“我置身在這樣的世界里:我被賤踏著卻無(wú)怨無(wú)悔地?cái)v扶著人們走向更高或者更危險(xiǎn)的地方。”
“你曲解了我,但你一點(diǎn)也不會(huì)回頭觀望。你攀得夠高了,你從來(lái)不會(huì)計(jì)較梯子的感受。你干脆拆壞它,你并不知道梯子是你的腿。”梯子無(wú)法把自己收起來(lái),只有砰的一聲倒下。他命定像山一樣,只有在撥高的過(guò)程中找出自己的尊嚴(yán)。在撥高過(guò)程中他的木質(zhì)的紋理才再一次有了森林的味道,覆蓋了整整一座山。
盥洗聲
洗衣聲不停地從盥洗間溢出來(lái),不斷灌進(jìn)我的耳朵。其實(shí)我分明看到它在空氣中所形成的波紋,在陽(yáng)光下閃著光。我努力描述著它,看著它,撫摸著它,它是細(xì)碎的,慢的,隨便的,沒(méi)有音樂(lè)好聽(tīng),但基本保持了一定的節(jié)奏。但它在空氣中不斷擴(kuò)大,先是占了居室一小塊地盤,接著逐步地整個(gè)居室都占滿了。至少我開(kāi)始有一種抵擋欲,因?yàn)槲以陔娔X前聽(tīng)一支鋼琴曲,浩大的音樂(lè)正幫我舒筋活血,我正被一只珠光寶氣的手從頭頂?shù)侥_上按摩。現(xiàn)在洗衣房里帶著肥皂泡的聲音溢了出來(lái),它無(wú)意地來(lái)到了我的眼前,它是原聲的,它的原創(chuàng)音樂(lè)正走到前臺(tái)。它從不管背后閃著貴族光澤的樂(lè)器和眼前敞亮的金碧輝煌的大廳,它不管它的出現(xiàn)是否和諧或令人質(zhì)疑,它像一個(gè)盲人正演奏和陶醉屬于自己的音樂(lè)。它從空中能隨便抓到樂(lè)器,它不管品相、音準(zhǔn)、音階,任意地發(fā)聲并讓它在我生活的空間彌漫。我知道它正在以另一種真正屬于它自己的聲音語(yǔ)言,來(lái)解釋世界,它是屬于時(shí)間的,在時(shí)間的延續(xù)中,它把它的手指放了進(jìn)去,把時(shí)間拆開(kāi),分解為每一個(gè)動(dòng)作和體驗(yàn),我坐在電腦前眼睛仔細(xì)地端詳著它,它是手指的形狀,一個(gè)又一個(gè)帶著皺紋和凍瘡的手指的形狀,此刻,它正在清理我的頭發(fā),翻檢我的皺紋,整理我的衣褶,揩抹我的污跡……啊,這些從手指的毛細(xì)孔中發(fā)出來(lái)的盥洗間的聲音,它也在慢慢磨損著消耗著,侵入我像一件衣服的整個(gè)上午和漫長(zhǎng)的無(wú)休無(wú)止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