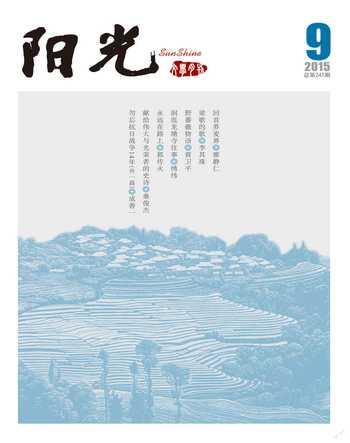父親的憂傷
一
父親喜歡拉二胡。父親拉二胡的時候,月光暗淡下來,宅子四周的樹枝上、竹葉上、扁豆藤子上似乎都沾滿了水,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氣息。如夏夜乘涼,深夜里醒來,偌大的稻場只有自己一個人,星星在天,樹枝橫斜,心跳惶然。
父親“右派”甄別后,在藥材公司做臨時工,管理倉庫,加工中藥,借住在藥材公司大院。這里除了我們,都是正式工、國家干部,拿固定工資而且經常開會、學文件。我和父親、哥哥住一間十平米左右的房子。沒有廚房,在門口支一個煤爐子,常常還被踹倒。踹倒爐子的有頑童,間或有些正式工們。他們說父親是老右派。
住大院的時候,二胡藏在床下一只爛箱子里,用幾層報紙和皮紙包著。
藥材公司在郊外有一處藥圃,種過白芍、杜仲之類的,后來荒蕪了。藥圃沒有電,房子破,屋后一百米不到全是亂墳崗,陰雨天瘆人,沒有人愿意來看圃子。成了野兔子、老鼠、蛇的樂園。
但那地方對于父親來說就是天堂。父親虔誠地向領導提了要求,領導說,行!
我們頭也不回地搬出了大院,像從一個不透氣的房間里走出來,大口地喘氣。我們不再擔心爐子倒了,水壺可以開心地唱到什么時候都行。
藥圃東邊緊挨著林場,樹木成林。父親指揮我們拔草,平整院子,在四周栽上“刺莓苔”,一種植物,有刺,夏天開花。三間瓦房,又搭了一間小廚房,我們居然有了堂屋,有了臥室。不知不覺,父親說話的聲音也大了許多。我摘下苦楝樹上的果子當彈子玩,父親居然沒有呵斥我。
院子東南方有一棵苦楝樹,很大。發三枝杈,我常常坐在西北枝上望東南方。東南方是舒城,我的出生地。我母親仍然在那個村里。村里有大塘,有小河,有山。我來蓼城的時候七歲,拎了一雙布鞋。
堂屋里的中堂掛著父親自己寫的字:“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院子里有很多野莧菜,不知道怎么會有這么多。父親命我們掐下尖頭,炒來做菜。掐頭的地方過不了幾天又發出幾只尖頭,成幾何數。野莧菜耗油,而我們又沒有多少油使野莧菜吃起來順滑,吃下去野莧菜就醋心。
父親的眉頭就一直鎖著。
夏天的夜晚,父親常常會搬一張凳子在苦楝樹下搗鼓二胡。緊弦,定調,抹松香。3 5|6 1|2 12|61 55|3……這是劉天華的《良宵》。那時我上初中,知道“良宵”的意思。就是不明白為什么《良宵》聽上去讓人傷心,良宵應該高興才是啊。
問父親,不理我。他沉溺于后面的高八度,手指猛然向下一滑,仿佛準確跳過了一道坎,帶有驚喜、恐懼,間或還有惡作劇般的慶幸,步伐漸漸地平緩起來。
良宵在父親的手指間嘆息。
沒有月亮的夜晚,父親會把“63”把位換成“15”把位。12 61 2 2312|56 53 2……(劉天華《病中吟》)步伐慢了許多。我想象出這樣一個場景:一個男人病了,沒有親人沒有醫生甚至沒有一杯熱水。亂山殘雪夜,孤獨異鄉人。劉天華悲從中來,憂傷從手指間緩緩流出,如雨如雪,如山如河,如草如木,如泣如訴。
一團濃霧在眼前,滯澀,凝重,揮之不去,化解不開。
音樂真是個奇怪的東西,幾個音符居然說出許多人間故事。父親有一本劉天華的曲譜,清秀的劉天華帶著無框的眼鏡,默默地注視著看他曲譜的人。那眼神清澈,深不見底。憂郁的神情透過歲月,透過紙背。
我一直覺得二胡這個樂器生來就是為憂傷準備的,緊緊地繃著的兩根弦永不相交,馬尾弓摩擦出了百轉千回,嗚咽泣訴,手指擠壓出悲歡離合。突然崩斷的弦讓訴說戛然而止,又如山體塌方,萬劫不復。
父親喜歡二胡,似乎命中注定。而他自己卻沒有跳過生命中的那道坎。
二
一個十四歲少年拎著一雙鞋,從舒城追隨土改工作隊來到霍邱。少年的父親是在兒子消失幾天后才知道。長嘆一聲,只當小兒子像他哥哥們一樣,被戰爭或饑餓奪走。
父親選擇革命其實理由很簡單,工作隊有飯吃,有韭菜炒豆干,發衣服發鞋子。韭菜炒豆干的香讓父親覺得革命是真實的。
爹爹去世的時候父親都沒有回去,他工作正忙。懷有一腔熱情的青年,心目中只有革命。很久后,父親在爹爹墳前長跪不起。
土改工作結束后,因為父親追求進步,工作積極,組織上安排他進入了黨校學知識學馬列,后來又送省黨校培訓了一段時間。我看過父親年輕時的一張照片:一表人才,年輕精干。中山裝口袋插一只自來水筆。
不久父親認識了母親。母親家庭成分是地主,她能歌善舞,讀高中。父親這個農村的孩子被城市的新鮮深深吸引。他不顧一切地和母親結了婚。此時,美好的前程已經向他展開,二十一歲的他要去一個區任職。
我可以想象出當時父親手中的二胡曲一定是《燭影搖紅》,是《光明行》。
音符從高八度降為低八度。突然轉換的音調讓父親來不及換把位,手指停在弦的最上端。曲調停在一個冬季。
因為給組織提了一個意見,父親為單位完成了“右派指標”。沒有來得及收拾行李,父親就被派去馬車隊。馬車隊里已經有了許多人,有的是父親尊敬的老師,有的是曾經高高在上領導。父親趕起了馬車,有幾次從奔馳的馬車摔下,險些喪命。
那飄揚的紅旗,那鐮刀斧頭組成的圖案,曾經為之追隨的神圣,突然之間與父親毫無關系。父親從開始的驚惶、抗拒到辯解、到沉默,到后來的絕望。他不得不認同了身份的轉換。
每天清晨,在瑟瑟的寒風里,車輪輾碎薄冰,也輾碎了父親的夢。父親后來對我說,他有次把馬車趕進黨校大院,被門衛呵斥,才恍然夢醒。
父親和母親第一次離婚,大哥被寄養在農家。那時的我,只是以一個生命的期許形式存在。父親用馬鞭抽打著自己的心,看著它破碎,碎片散落在馬車周圍。父親碾過碎片,他讓自己的憂傷蜷縮在薄薄的棉被里,孤獨地綻放在沉沉的夜里。
被兩個“家”遺棄的父親住進了馬車隊簡易的工棚。二胡形單影只地掛在柱子上,布滿了灰塵。一根弦彎曲地耷拉著,偶爾有風讓它微微顫抖。它不知道主人為什么舍棄了它。
有次居然從琴桶里掉下來一只小老鼠,掉在父親的身上。父親懶懶地看了看,原來蛇皮已經被老鼠咬了個小洞。父親說他覺得自己應該死去,或者寧愿成為一只老鼠。
兩年后父親又去了副業場喂豬。即使是農村長大的娃,父親也第一次知道護崽的母豬會咬人,那次差點兒要了父親的命。父親在豬場的煤油燈下讀醫書,他知道,他肯定成為不了良相了。
因為大哥,父母親又復婚了。復婚的原因很簡單,父親抱著大哥經過一座橋,迎面走來了母親。大哥撕心裂肺地喊媽媽,父親把他屁股都掐青了仍然無法阻止。父親放下大哥大哭起來,母親也抱著大哥哭。
父親的悲哀如橋下滾滾的河水。
結了婚以后我才明白,對于男人,尊嚴大于生命,孩子大于尊嚴。父親的憂傷如灰色的云隱在漆黑的夜色,如琴弓離開二胡。
我的父親,我不知該如何評價您在橋上與母親的偶遇。您的哭,您的悲憤,您的屈辱,作為一個男人,我懂。橋上,您彎曲的身體化成珠穆朗瑪峰,聳立我心。因為那次偶遇,有了我,也有了今天的文字。
三
一個男人的悲哀和無助,穿透了我的胸膛。讓我在幾十年后的文字里,仍然彌漫著憂傷。我不喜歡二胡,也很少聽二胡曲。我更喜歡笛子或者嗩吶,甚至我可以喜歡簫,就是不喜歡二胡。
如我不喜歡甚至刻意地回避那段灰色歲月。我知道,那段灰色似乎也不屬于父親一個人。但對于父親來說,憂傷就是整個世界。
那段歲月里,我們的國家何嘗不是《病中吟》呢。
四
父母復婚后,母親回到了父親的故鄉舒城。我就出生在一個叫舒茶的山村,在一個雨水的節氣里,注定了我的根最初扎下的地方。對于蓼城來說,我是棵移栽的植物。我的根系從不習慣到適應到后來的盤根錯節,我有頑強的生命力。如二胡上的蛇皮,能發出并不屬于我本性的聲音。
歷史總是富有戲劇性。一九五八年,一個偉人站在山坡上說:“以后山坡上要多多開辟茶園。”偉人指過的地方,后來茶樹滿坡。
是那個偉人讓熱血的、追隨革命的父親去趕馬車、喂豬,并被遣回原籍;也是他,站在父親的家鄉的山上吸煙沉思。在父親血脈延續的地方,他揮手之間改變了江山。
偉人不認識我父親,但我父親認識他。
父親在蓼城,我們在舒城。記憶中有一年直到年三十家家戶戶都放鞭炮的時候父親才進門。沒有客車,他硬是借了輛自行車騎了二百多里路回家。到家后父親癱坐在地上,母親則大哭。那年,我第一次認識了自行車,我們愉快地轉著它的輪子,看著它從起點回到起點。
父母親第二次離婚后,我來到了蓼城。或許這就是輪回吧。
住進藥圃后,父親開始修二胡了。找來了膠水、松香,從藥材公司買來了蛇皮。但是做藥的蛇皮卻無法讓二胡唱歌,后來父親尋到了一個琴師,在一次紅燒肉、青椒炒雞蛋下酒后,二胡在父親的手中跳躍,躲避,拒絕,掙扎,平靜,擁抱……父親破天荒地讓我們用米飯泡肉湯。
父親緊鎖的眉頭漸漸開放。真是一個良宵啊!
如水般的夜啊,如水般的二胡聲,浸潤著全身。慢慢流走了周遭的熱量,涼意從頭發梢向下,直達心膜。我蜷曲在苦楝樹下,第一次聽父親如歌的行板。
我隱隱看見了父親臉上淌著兩條月光。
性格決定命運,命運也可以改變性格。父親年輕時血氣方剛,頭破血流后低眉順眼,其實內心是憋屈的,是不服的。父親才華橫溢,會醫、會書法,口才好,唐詩宋詞張嘴就來。還寫了很多醫學論文,在權威期刊上發表。關于瓜子金治療慢性咽炎的文章發表后,接到了全國各地的求助信件。父親看信時很開心,但一回到現實就更不開心。他的編制問題,他的待遇問題,他的補償問題,他已逝去的青春年華,已經破碎的家庭……這些都是一把把刀子扎在父親的心里。
男人最重要的兩個家——大家,小家,在父親心里都支離破碎。他是一個被拋棄的人,一個充滿熱血和奉獻精神卻被不屑一顧的人。
父親在外低眉順目,對我們則聲色俱厲。我們常被罰跪。父親生氣了會喊把雞毛撣子拿來。我們乖乖去拿,盡管知道這個撣子會很痛地打在我們身上。
記憶中父親只有兩次慈愛。一次是我高考前夕,半夜里父親遞了一只雞腿給正在復習的我,還有一次是我和新婚妻子去蚌埠醫院看他。告別后我們回頭,父親在三樓的窗戶前目送我們。
我有了孩子后,我沒有動過他一手指頭。我在外可以義正詞嚴,可以據理力爭,甚至可以強詞奪理,但我在家人面前永遠低八度。如二胡的低音弦。
我知道這樣的做法或許不好,對孩子的教育不利。這是我童年、少年時代的陰影,是父親苛責給我帶來的后遺癥。但我原諒父親,原諒父親對我一切的泄憤般的嚴厲。
因為父親的憂傷,那種“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憂傷。
秋涼如水的夜晚,沒有燈光。黑魆魆的田野,墳地里飛舞的螢火蟲,墻角處唱歌的蛐蛐,苦楝樹搖曳的斑駁。父親的二胡穿行在月白風清中,如一只船載著他的歲月,他的回憶,他的思念,他的悔恨。我能看到聲音游走的軌跡,它用雙手拽著父親的憂傷,氣喘吁吁。
父親,我和您能在這個世界上同行一段光陰,這就夠了。
后來父親終于徹底平反,并進了一個機關。但不久就查出了癌癥。
五
父親被查出癌癥后,似乎解脫了。或許在他內心中,渴望著回歸。他不再鎖眉,甚至最后拒絕我們給他治療。他寫好了自挽。交代了墓地的修建方法,他畫的圖,像僧人坐化的圓形壇,他的骨灰將端坐中央。
憂傷在這個時候已經被打敗。是的,死亡可以打敗一切,歡樂,悲傷;貧窮,巨富;乞討者,英雄;統治者或者草民。
生命即將終結,附屬在生命上的憂傷如塵埃遇到了黑洞。
父親最后一次拉二胡是《光明行》。那是一個清晨,在他居住的小閣樓上。1 11|1 11|1 11|1 11……我能聽出來這是鼓聲,是前進的號角,號角在召喚著光明。劉天華穿破了憂傷的濃霧,他要去哪里?我覺得父親和劉天華和二胡是相通的。
小閣樓是幾年前父親自己建的,閣樓不大,樓梯僅容下一人,環繞著竹林、大樹,門前一條小石子路。沒有人知道父親為什么當初放著平房不蓋,卻要蓋一個好看卻不中用的六角樓。后來我才知道,或許父親是想“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
父親遺囑里要求永遠保留著六角樓。如今小樓已傾斜,岌岌可危。苦楝樹也在某年被劈為柴火。
閣樓成為老宅子一個標志性建筑,也是我記憶中的一個傷疤。
父親走在一個夕陽西下的秋天,大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遠處有新婚的鞭炮聲。生命就是在這樣的忙碌中輪回。我的幾個姊妹因為父親的離去而聚集在了一起,這是父母第二次離婚后我們姊妹第一次相聚。父親平靜而祥和,眉頭舒展,沒有痛苦沒有怨恨沒有憂傷。五十二歲,對于有些人來說,正是生命鼎盛時期,而在父親這里,已經終結。
二胡按照我們的習俗燒給了父親,包括那本曲譜。
曲終人散。
六
父親的憂傷這些年一直縈繞著我,如我流淌著他的血脈,繼承了他的姓氏。我一直在尋找一條通道疏導,否則淤積的情緒會成為我心里的“堰塞湖”。
父親去世之前我才有機會和他深入地溝通,我們像朋友。我甚至知道了父親最初的愛情,分離思念和結果。這些事曾經諱莫如深,不敢問也不會說。他仍然罵,但這是朋友之間的親昵,是帶笑的罵。我在父親的罵聲里熱淚盈眶。
我對父親說我不喜歡劉天華,他太憂傷。父親說你不懂,能說出來的憂傷,都不是真正的憂傷。
二胡會說嗎?
二胡會說!
什么是憂傷?我覺得用所有的詞解釋憂傷都是蒼白的。怨天尤人,報國無門,沉冤難昭,懷才不遇,情緣難了……或借酒澆愁,或唉聲嘆氣,或蒙頭沉睡,或長歌如哭,或香消玉殞。
對于父親來說,憂傷從音符高八度跌落開始,從《燭影搖紅》到《病中吟》,從《光明行》到《悲歌》。對于已知天命的我來說,我更懂得了父親。他是堅強的,也是軟弱的。他用低眉順眼掩飾他的內心抗爭,不服,憋屈,他用苛責掩飾他軟弱,憂傷,祈求。
個人的命運和國家命運扣在一起,掙脫不開,既是幸事,也是悲哀。一場劫難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只是歷史;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生。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是一種憂傷;“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也是一種憂傷。無論是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憂傷如影隨形。
父親的憂傷是個人無法擺脫、無力抗爭、無法改變的憂傷。是一錠徽墨,越稀釋越漆黑。
七
長歌當哭。
我們從來時的自己哭,到離去時的親人哭,哭即是歌,哭即是曲。如果生活是二胡,是笛子,是鋼琴,是吉他,是笙簫;性格則是曲譜,是音符,是和弦,是八度空間的跌宕起伏;命運則是演奏者。或憂傷,或歡快,或華貴,或激情四射,或嗚咽嘈雜。
父親繃緊了自己,卻永遠無法奏出《喜洋洋》《步步高》的歡快,他用半生譜寫了憂傷,完成了演奏。
如果父親的生活是小提琴,又恰逢清平盛世,我想那一定是一首華麗的圓舞曲。
只是人生永遠沒有“如果”。
劉天華三十七歲英年早逝。五年后,一九三
七年,父親出生。
感謝劉天華,讓父親的憂傷如山澗里的泉水,奔涌跳躍,此消彼長……
張子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有小說集《打死我也不信愛情》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4年卷,并獲“安徽文學獎”“安徽省首屆小說對抗賽”金獎。出版長篇小說《黑白布局》《舊城》,有多部小說被改為影視劇和被各類選刊選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