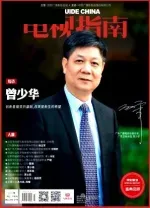穿梭70年的歷史影像
李洋
十年來,抗戰風云從未退出過熒屏,戰火持續“蔓延”。今年這把火燒得尤其厲害。
今年是二戰勝利70周年,伴隨著系列紀念活動的契機,原本已炙手可熱的抗戰劇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有朋友和我說,現在看電視,只要打開電視機,幾乎換三個頻道就有一個在播抗戰劇。談情說愛,婆婆媽媽,家長里短,加上炮火連天,幾分天下。如果說有一種題材既和國家民族歷史相系,又和傳播優勢相連,無論從數量和影響來說,抗戰劇當屬第一。從收視傳播影響效果來考察,抗戰劇占據顯著位置。我把它看做是近十年來中國電視劇最具特色的“國劇”標本。
二戰是一場幾乎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戰。70年來,很多相關國家都在以各種藝術形式表現這場戰爭,從戰場到民生,從軍人到百姓,從男人到女人,從老人到孩子。各種角度,五花八門,戰敗國不避諱,戰勝國更喜歡拿二戰說事兒。德國對于二戰的態度在二戰題材電影《莉莉瑪蓮》《潛水艇》里已有呈現,與之匹配的還有德國政治家向受害者的誠懇道歉。其作品數量不多,且多以與英美合資出品方式介入和回味歷史。日本對于二戰的“念念不忘”也一直體現在影視作品中。十年來,推出了電影《男人的大和號》《吾為君亡》《永遠的“零”》等戰爭電影,近期還在播放侵華戰爭背景的電視劇,已引起中國觀眾的熱議。但按數量來看,盟軍陣營里,對于二戰題材最為鐘情的當屬中、美,美國的電影和中國電視劇。
有什么樣的觀眾就有什么樣的電影和電視劇。美國人一直以二戰為榮,的確這場家門外的戰爭使美國成了世界霸主,英美異位,日不落帝國讓位于美利堅合眾國。二戰片成了美國戰爭電影的精神支柱和榮譽殿堂。而我們的二戰片具有特別的本土氣質,名為“抗戰片”,與法國的“抵抗片”相仿佛。抗戰題材曾是中國電影的一道強悍風景,老三戰特別是《地道戰》《地雷戰》曾經創造過洗印拷貝超高的紀錄。我們這一代觀眾是看著老三戰長大的,《平原游擊隊》里的李向陽、《小兵張嘎》里的嘎子,曾是我們心目中特別崇拜的接地氣的英雄。后來,這個血脈被電視劇繼承并得到了發揚光大。
十年來,抗戰風云從未退出過熒屏,戰火持續“蔓延”。今年這把火燒得尤其厲害。從央視開年面對《鋒刃》,到連月排播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怒放》《東北抗日聯軍》《太行山上》《東方戰場》《24道拐》,到各家衛視的抗戰劇,如《馬上天下》《秀才遇上兵》《英雄祭》《鐵在燒》《生死連》,可謂戰云密布,槍炮齊鳴,殺聲四起,霸氣四射。
觀察發現,抗戰劇的味道與時俱進。透視其變化軌跡不難看到,自70后、80后主創(特別是編劇、導演)開始進入“沙場”縱橫抗戰歲月,抗戰劇的色彩的確出現了鮮明的變化。時間讓我們與歷史漸行漸遠,與歷史的距離讓不同代的創作者幾乎下意識地選擇了不同的故事立場。抗戰劇開始出現了很飛揚的、穿越的甚至是雷人的劇作,戲劇感不斷被加強,當失去了一種控制和限度的時候,戲劇就邁向了游戲。由此,在不同年齡段的業者以及觀眾之間,產生了不同的化學反應。年邁者對于這種飛揚失度提出嚴肅質疑和批評,而年輕的受眾則喜歡和接受抗戰劇的新變化和新味道。我相信,10年后20年后,這種代差反饋還會繼續存在,認知和觀念沖突依然會出現。時間在推進,時間在淡化和稀釋一些東西,濃咖啡會變成一杯清茶。歷史的痛點也在模糊化,痛感在減輕。
抗戰劇數量繁榮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好劇寥寥,與數量呈反比的現狀也有目共睹。被收視數據推波助瀾的抗戰劇,有似脫韁野馬,在一片質疑和吐槽中高歌猛進。很明顯的變化是,從2005年推出的《亮劍》至今,抗戰劇的味道的確一直在變,變得越來越花哨,越來越失重,越來越強調技術含量,不大在意內涵開掘和深度立意了。過去我們特別愿意強調,我們是在“創作”,后來創作很少提了,這個概念被“制作”取代了。制作的自然首先是產品而不是作品,制作產品的目的就是銷售。商業氣質已然成為所有抗戰劇的第一風度。堅守人文敘事很困難,在產品流水線上從善如流成為正道。從時間的變化到環境的變化來看抗戰劇的變化,大致也就能理解目前抗戰劇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了。時間直奔未來,想倒車回到10年前20年前,怎么可能?面對現實,思考趨勢,探尋更好的路徑,是唯一現實的態度。從創作到制作,現在更多地扯到“運作”,這事兒變得越來越不單純了。
去年以來,我一直沉浸在上海抗戰歷史的史料堆中,摸索和思考上海抗戰劇的創作策劃思路。和許多上海朋友聊天,發現即便是上海人,很多人也分不清“一·二八”抗戰和“八一三”抗戰,一個是1932年,一個是1937年,中間有五年間隔。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等,大家都是了解的,但講述中就把“八一三”發生的故事講到了“一·二八”的背景里,記憶是模糊的,張冠李戴者不少。上海本地人尚且如此,外鄉人含糊也就不足為怪。所以,我和上海朋友合作發起抗戰姊妹篇的創作,一部叫《鐵血淞滬》寫“一·二八”抗戰歷史,一部叫《同一面戰旗》(又名《紀念日》)寫“八一三”抗戰。這部由我任藝術總監的《鐵血淞滬》已拍攝過半,以1932年“一·二八”抗戰歷史為背景,講述了一個裁縫世家卷入抗戰風云的故事。父親是這家的頂梁柱,作為上海灘小有名氣的旗袍大師,穩當經營著自己的生意。二兒二女,大兒子子承父業,專做洋服,為十里洋場的各路神仙精心服務,后被日本人拉下水,成了漢奸。大女兒是中國地下黨員,駐19路軍特派員。小兒子在戲班子混事兒,私下里是民間斧頭幫的頭號“鋤奸殺手”,小女是在校女生。以這個家庭故事為主線,以19路軍進駐上海抵御日軍為副線,講述“一·二八”抗戰的風云歷史。上海抗戰歷史頭緒繁雜,很容易陷入麻團說不清楚。故事的清晰度是我們特別強調的,突出上海抗戰的特點,突出上海普通人家應對危機時的猶疑和果決、忐忑和血性。敘事擇“武戲文唱”,有炮火硝煙,但重點放在民生故事。以民為主,以軍為輔,全民抗戰上海灘,希望在全體劇組成員共同努力下,拍攝出一部有特色、有特質、有追求、有品格的品質劇。在故事里與觀眾分享1932年的上海的空氣、風雨、歡笑、眼淚、決絕。
抗戰史無疑是我們內心充滿痛感和悲壯的往事。時間減弱了我們的疼痛,但不可泯滅的是記憶。不管用怎樣的方法講故事,對于歷史脈絡的清晰認知,對于那段歷史的價值評判等,都是需要堅守的。有戲不游戲,就是底線。
忘戰必危,抗戰劇是一劑良藥,提神醒腦,牢記歷史,不忘國恥,發憤圖強,激勵看客做一個稱職的勇敢的中國人。
商業氣質已然成為所有抗戰劇的第一風度。堅守人文敘事很困難,在產品流水線上從善如流成為正道。從時間的變化到環境的變化來看抗戰劇的變化,大致也就能理解目前抗戰劇不盡人意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