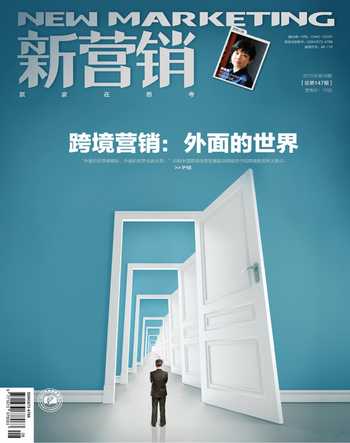“印”有之義
祝宏偉

一枚印章對于今天的我們,也許司空見慣。但說起印章文化,用博大精深來形容也不為過。據《說文》解釋:“印者,執政所持信也。”作為權力、信譽的象征,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它的功能早已不止作為執政的象征那么簡單,由于蘊含了豐富的人文信息,印從一個可資驗證的信物逐漸朝一個更具抽象意義的文化符號演變,幾乎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超級文化標志了。
印之魅
早期,印作為最權威的征信憑證,是有德者、有位者的法器。印不僅作為權力的象征,而且是行使權力的工具。《中庸》有云:“雖善無征,無征不信”,故“大德者必受命”,印信則是必配的法器。韓非子曰:“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老子則曰:“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毛澤東同志也曾指出,在歷史研究中要做到知人論世,就必須清楚在階級社會里人的思想上無不打上了階級和時代的烙印。誠然如此,但又豈止如此,它簡直可以無往不征,無遠弗屆。
當今,印對于我們每個人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在各方面都需要它。它的用處極廣,魅力極強。一旦離開它,真的寸步難行;一旦擁有它,就會能量大增。對于學生,錄取通知書、獎狀、畢業證上鮮紅的印章就是進步的階梯;對于工作人員,榮譽證、任命書、責任狀上鮮紅的印章就是工作的動力;對于適齡的男女,兩本結婚證到手,就成為合法的夫妻。君不見,大路上雖然車流滾滾,但如果沒有駕駛證就不能開車;銀行里雖然財源滾滾,但如果沒有印鑒則金融不能流動。社會的運作,正是通過這些有形的、無形的印信符契把每個人聯系在一起,通過這些形形色色的證書和印章規制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于是,有的人曾自嘲,每天不是在蓋章,就是在去蓋章的路上。
對于普羅大眾,印既高懸在我們的頭頂,又如影隨形地貼合在我們身邊,與我們須臾不分離。有的人把它銘記在心里,執掌在自己手中,有的人把它置之度外,宣揚“帝力與我何有”,有的人則被操縱在別人手中,成為別人的附庸。它的存在仿佛成為我們每個人命運攸關的物柄。
印之痕
印在斗轉千年的歷史變遷中,留下了一道光彩奪目的印痕。如果我們考察其源流變化,大約有四個階段演變特征,就會發現印章的本來面目和今天洋洋大觀的印文化大異其趣。
一是專屬性的擴大,從官方印信而普及成為民間信物。上古印璽通稱,但其專屬性自古至今都沒有改變。自秦以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用印信材質、形制及名稱均有別,天子、諸侯王獨以玉為材,以橐駝為鈕,稱為璽;列侯至二千石以黃金為質,以龜為鈕,名曰章;千石至四百石,皆以銅為質,鈕形不可僭越,曰印。印的專屬性主要是指官職而言,但發展到一定時期,就有了公私之分。
二是代表性(象征性)的擴大,從執政象征而發展至經濟信托。作為古代王侯之印,自然是金相玉質尊貴非凡,專供執政國家而用,唯有德者配之,唯有位者保之,凡人不可竊窺神器。戰國時期,蘇秦佩六國相印縱橫天下,一時顯赫無與倫比,也成為后世草根奮發向上的楷模。隨著印章從官方走向民間,在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中,以印封泥逐漸成為經濟信托責任的證明。其象征性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其材質的罕見。戰國時期出土的和氏璧,上演了一出“卞和無罪,懷璧其罪”的人生悲劇,并引出了藺相如“完璧歸趙”的歷史典故。
三是適用性的擴大,從沿用管制到文玩收藏。印璽作為權力的象征在管制上自然極其慎重,每逢政權更替需要轉交印璽外,歷代郡縣州府官員離職都要“封印”移交給后任。當印章逐漸成為個人私用的物件,特別是紙張的出現,一方朱印伴隨著翰墨書香,更加增添了書畫作品及文物的高雅情趣,印章文化大放光彩。無論印章的材質運用,還是印文的書體形式,都呈現出華彩繁茂、洋洋大觀的發展趨勢。印的獲得、轉移、遺失也產生了許多歷史故事。《三國演義》中就有兩則經典的與印有關的故事。一個是孫堅藏璽的故事。東漢末年政權瓦解,孫堅作為一方諸侯與袁紹、曹操等結盟起兵,在共同抵抗董卓時,無意中獲得了一塊傳國玉璽(即和氏璧),遂私心萌動,決定退出同盟,揮師江東,開辟帝業,于是拉開了三國鼎立的序幕。二是關羽掛印封金的故事。當淪陷在曹營的關羽打聽到劉備的消息,毅然推辭“漢壽亭侯”官印,謝絕曹操的美意,千里走單騎趕去投奔,其君臣兄弟情義令人感佩。
四是象征性的擴大,從官方權威到文化意象。印是權威的代表,從世俗的政權到宗教的世界,莫不如此。在佛教傳統中把佛門最基本的教義稱為“印定之義”,把幾條金科玉律奉為“法印”,有三法印、四法印、五法印之說;把以手指結成的各種形象,稱為“印契”以展示其法德。在神魔小說《封神演義》里,以印為法器的神仙妖魔都十分了得,元始天尊有“太極符印”,廣成子有以半座不周山煉成的“翻天印”,姜尚有“護臟符印”,就連通天教主也得早晚用符印護住“六魂幡”時,方能保障它的法器靈驗,印的法力端的厲害無比。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印總是與美好的事物連成一體,逐漸成為一個表達心理意象的詞匯。“印象畫派”是法國19世紀60年代展開的藝術運動,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畫風;由張藝謀執導的《印象劉三姐》大型現代歌舞劇表現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獨特人文風情;言情小說喜歡用 “心心相印”一詞表達男女二人兩情相悅、靈犀相通的美好情意;西湖美景“三潭印月”更是描述了中秋月圓之夜,水光瀲滟,山色空濛,三潭池水、三輪明月相互映照的曼妙意境;浩淼煙波之上,一名法號“佛印”的禪師與蘇軾、黃庭堅泛舟西湖,一起聯詩作對,其才華橫溢、妙語如珠的故事流傳至今。
印之光
當印章成為文化收藏,伴隨著翰墨書香增加了文物的價值,印與文化更加結緣了。由國家博物館珍藏的頂級書畫神品中,很多作品不僅蓋了作者本人的款識,還蓋上了歷代藏家、鑒賞家以及歷朝帝王的印章,使詩、書、畫、印連為一體,倍感高雅厚重。最著名的是,自詡文采風流古今第一的乾隆皇帝收藏鈐印之繁,罕有其匹者,《乾隆寶藪》記錄了乾隆印璽1000余方。而他在書畫上的鈐用與他的政治態度、文化修養、文人情趣是緊密相連的。
饒是如此,大多數印章在歷史的斗轉星移中,只有落得“爾曹身與名俱滅”的下場。但是,在浩如煙海的印章中,卻有一種印流傳下來,讓歷史也能耀出光華,透出鮮活,這就是聞名天下的徽州“紅方印”。
在上海國家煙草文化博物館以及黃山地區收藏家的陳列室中,陳列了不同款式的蓋上紅印章的煙草封皮,以及多枚制作于清代中晚期的印章。這些藏品對于研究中國煙草品牌發展、商標演進的學者來說,彌足珍貴。它們的存在,不僅揭示了明清時期煙草生產、制造、商業流通的歷史信息,而且還記錄了中國煙草品牌的萌芽──煙草商標出現的過程。
這些藏品不僅印證了安徽煙草的光輝歷史,對于安徽中煙黃山品牌的建設者們來說,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些藏品上的精美圖案、豐富的歷史人文信息,經過他們的二次創造,這些藏品的價值可以照亮黃山品牌的未來。一款從這些精華藏品中汲取創意靈感的設計──黃山(大紅方印)應運而生,“印韻”十足,妙趣橫生。投放市場后,黃山(大紅方印)立即引起轟動,出現了讓同行艷羨、至今擁蠆者不衰的“紅方印現象”,成為近年來煙草品牌營銷史上的一個經典案例。
印之韻
一方印何以能成為神品,印韻由何而生?
若考察其制作過程,一方印,因其材質珍貴,必須邀請非常之良工巧匠,方能治其印;一方印,因其鈐用者身份尊貴,必須具備能恰當地展現其才情、修養、抱負的文字方能堪其用。
若考察其流傳過程,一方印,除了品相固然不俗,還因用印者、治印者人品、藝品、文品兼優方能流傳于世。
只有當這些極其苛刻的條件疊加在一起,又經時間和良工這兩道造化之功的打磨,才能造就一塊印章的獨有神韻。由此觀之,“印”韻之生當有五大元素:“材、型、文、藝、人。”
若以材質而言,玉、金、銀、銅、石、牙、角、木等都有堅硬、堅貞的品質,以玉居首,其中包含的文化精義不可不察。許慎《說文》中道出“玉有五德”,所以“君子當溫潤如玉”。五德者,“潤澤以溫,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潔之方也。”由此可見一斑。
若以印文的形式而言,有篆書、隸書、楷書及其他書體,隨時代流變,風格各有千秋;依照刻寫效果有陰文章、陽文章,兩種章各有司職,或迎首,或壓腳,二者相輔相成,切忌不可亂用。
若以印文的內容而言,有名章、閑章之分。各種名章、閑章,已構成了印學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閑章尤甚。所謂“閑章”,其實不“閑”。到了近代,閑章的內容十分廣泛,且意趣盎然,書畫家或自擬詞句,或擷取格言、警句于閑章,以示對人生和藝術的感悟。
若以刻寫的工藝而言,很多篆刻名家大多是“少年功夫老始成”,以較高的天賦見多識廣,再加上經年不輟勞作、刻苦努力,才能有所成就。齊白石、趙之謙均視印如命,刻“印奴”二字以自命。篆刻大師吳昌碩至晚年方成一代宗師。在刻銅治印藝術方面,中國有閻氏一門克紹箕裘,綿延300多年,其中雖官爵顯赫而不失其藝者尤其難得,閻家代代名家輩出,均能與時俱進迭出新意,其家秉持的執著家風,非常符合李克強總理念茲在茲的“工匠精神”。
若以收藏者、使用者而言,除了帝王將相以外,古今文化大家所用之物都可以稱為文物。中國自古就有以使用者是否“德藝雙馨”來衡量文物價值的雙重標準,藝術規則和道德規則與文物價值息息相關。據說,當代偉人毛澤東也是一位喜歡印章的藏家,盡管他一生儉樸但所用的印章無不是當世名品,都是由當代仰慕其雄才大略者贈送,與世俗的權錢交易毫不相干。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記載的與夫君趙明誠一起收藏金石的經歷亦然。
印之義
在文化學里,印章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Clifve Bell,1881-1964),一種包含豐富信息的文化載體,歷經數千載而大放異彩。面對流傳下來的各種神品印章,我們不禁思考:一方印,在方寸之間如何有效地實現文化傳承和價值承載,其中究竟有何精義?
據筆者總結,其原因大約有四:一是材質貴,二是形式美,三是意義精,四是品格高。
如果對使用價值產生的原因來分析,盡管當今數控技術高度發達,無論什么材質都可以刻寫出同類形式的文字,并不能減少,反而只會增加大師級人工治印的價值。大師手工刻寫中所透出的書風個性,文字意義中所蘊含承載的涵義是無法復制的,仍然決定著它的價值屬性。此外,作者的藝品、文品、人品和風范尤其是難能可貴的。
如果對交換價值產生的原因來分析,好的作品具有與鑒賞者可供交流的心理密碼,它能使作者的心意和鑒賞者的心意在不同的時空展開交流,而印的價值彰顯關鍵在于作者與鑒賞者能夠“心心相印”。只不過人與物之間的主客交流互動往往需要在一個大的歷史時空中完成,人作為交換價值中最難得的因素,神品與藏者的際會需要特殊機緣,唯有識者乃能得之,唯有德者乃能保之。由此,可嘆一塊古代神品流傳下來歷經兵燹禍亂多少故事,能夠得以幸存下來何其艱難。這些在交換環節存在的歷史因素更增益其價值屬性。
從五彩斑斕的印文化中,我們不難得出:品牌價值的創造和傳遞其實也與印之刻治、流傳的道理相通。生產者與消費者必須心心相印,才能創造適銷的合格產品;在交易環節,一個偉大的作品必須放在一個較大的歷史時空中,完成作品與眾多有識者的互動,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方能化為永恒。
如果回到黃山(大紅方印)的話題,思考黃山品牌所倡導并力行的文化營銷之道,與消費者始終保持心意相通應當成為不變的追求,并且以這種恒定的心,持續下去,方能到達鑄造不朽品牌的理想境界。也許,這正是黃山品牌文化營銷需要闡發的“印”有之義吧。
黃山品牌正是這樣始終保持著與消費者心意相通的心,把品牌文化的力量穿透、溫暖到每個消費者的心中,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終有一天實現“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品牌夢想。